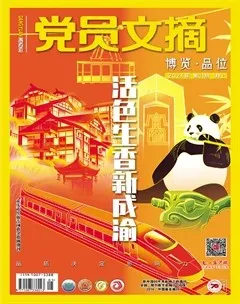蔡元培與北京大學:一段重塑中國教育歷史的光輝篇章
祁文斌
1917年1月4日,北京大學的校門口,所有校工佇立,準備迎接新校長的到來。
一位風度翩翩的學者從車上下來,竟然先脫帽鞠躬,向校工致意。
這一舉動引起不小的轟動,這位儒雅的學者正是蔡元培,被北大學子們尊稱為“永遠的校長”。
蔡元培的到來,書寫了北京大學的嶄新篇章。
當時的北京大學魚龍混雜、亂象叢生,決意教育興國的蔡元培從嚴肅校紀、整頓校風入手,對北京大學進行了一番大刀闊斧、脫胎換骨的變革。
而破除陳規陋習,聘請具備真才實學且富有革新觀念的人來校教學,成了蔡元培“千頭萬緒”中的當務之急。當時,北京大學空缺了一個關鍵職位——文科學長。與蔡元培早年相識、因主辦《新青年》而名噪一時的社會新銳陳獨秀進入了蔡元培的視線。
起初,陳獨秀很猶豫。因為《新青年》編輯部在上海,妻小又遠在安徽懷寧,自己若任教北大,自然不太方便,但是蔡元培求賢若渴。
蔡元培幾乎天天到西河沿的中西旅館探訪,那是當時陳獨秀來京辦事的臨時住處。有時去得很早,陳獨秀和別的旅客都還沒起床,蔡元培就叮囑茶房不要叫醒他們,只拿個凳子在門口坐著等。
陳獨秀最終被蔡元培的謙遜和誠懇深深打動,接受了蔡元培的邀請。蔡元培還建議陳獨秀將《新青年》編輯部也遷往北大,他說:“在北大,有一大批教授同仁可以給《新青年》寫稿,《新青年》的質量和知名度將大大提高,會更有影響!”
1917年1月11日,蔡元培在致教育部的報請函中,附上了一份陳獨秀的履歷:“……日本東京大學畢業,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安徽高等學校校長。”然而陳獨秀的這些“學歷”“任職”根本子虛烏有,完全是蔡元培為應付那些“重資歷,輕能力”的官僚所虛構的。
事實上,陳獨秀不僅沒有“學位頭銜”,甚至“從來沒有在大學教過書”。陳獨秀在1901年至1915年期間曾5次東渡日本,但每次逗留的時間都不長,也沒有接受過日本全日制普通大學的學歷教育。至于“任職”,陳獨秀是安徽公學的前身安徽旅湘公學遷回蕪湖的倡議人和推動者,但并沒有在該校任職。安徽高等學校是陳獨秀主持創辦的,但他也只任過教務長,沒有任過校長。
蔡元培的舉薦很快得到了認可。13日,教育部簽發部令:茲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15日,北京大學便張貼了布告,當天,陳獨秀上任。
“虛構”被聘者履歷,本不屬光明正大之舉,但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蔡元培為振興教育、選拔才俊,如此所為便是與人為善、成人之美。
陳獨秀到了北京大學以后,幫助蔡元培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使北京大學的面目煥然一新,新文化運動也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陳獨秀任文科學長后,向蔡元培竭力推薦《新青年》雜志投稿者、當時還在美國留學的胡適。蔡元培看了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詩三百篇言字解》等文章后,認為胡適舊學新學皆有造詣,決定聘請胡適任北京大學教授。胡適接到陳獨秀的通知后,很快回國接受聘任。
1918年,27歲的胡適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有反對派認為這是胡適不懂文言的“藏拙”之作。蔡元培以其國家宿儒、學界領袖的身份對此書大加贊許,并作序推薦。1919年2月,《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風行海內,面世3年之內再版7次,奠定了胡適在學術界的地位。
胡適也全力支持蔡元培的工作,共同推進北京大學的教育改革。
更令人感動的是,蔡元培聘請梁漱溟任北京大學教授時,梁漱溟只有24歲,學校有些學生的年紀都比他大。
1917年,梁漱溟報考北京大學沒有考上,論學歷他只是一名高中畢業生,但是梁漱溟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的文章引起了蔡元培的高度重視,他認為梁漱溟的功底深厚,前途無量,甚為惋惜,說:“梁漱溟想當學生沒有資格,就請他到北大來當教授吧!”蔡元培與當時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商議,決定聘請梁漱溟來校主持印度哲學講座。
梁漱溟對此卻感到十分惶恐,蔡元培問道:“那么你知道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嗎?”梁漱溟說不知道,蔡元培接著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橫豎彼此都差不多,還是來吧!你當是來合作研究,來學習好了。”最后,梁漱溟答應到北大任教。
于是,年紀輕輕的梁漱溟便登上了北京大學的講臺。在校期間,梁漱溟不僅很快勝任了教學工作,還寫出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重要學術著作,轟動了中外哲學界。
當陳獨秀、胡適、李大釗、魯迅、梁漱溟、馬寅初、李四光、馬敘倫、辜鴻銘等一大批新銳人物和舊派學者濟濟一堂,各得其所、云集北大時,彰顯出了蔡元培兼容并包、不拘一格用人思想的睿智、大度與氣派。
(摘自《文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