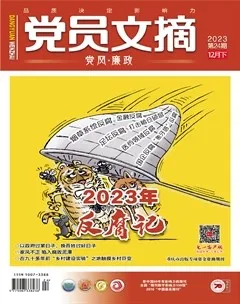防止滿意度調查“討滿意”
姜剛 周暢
當前,不少部門單位將滿意度調查作為衡量工作成效、評價工作作風的方式,收到良好效果。但少數基層部門單位在進行滿意度調查的過程中,卻出現打印“明白紙”,注明“滿意”“知道”等標準答案,回答“滿意”“安全”可得現金獎勵等怪相,導致滿意度調查“變了味”。
花式“討好評”,難獲“真滿意”
“我最近接到一個單位發來的短信,說如果接到滿意度調查電話,讓我為家鄉代言,還說回答‘非常滿意將激勵他們繼續前行……”中部地區某市的一位市民反映,自己時常收到此類“討好評”短信。“若干得好、有底氣,這些單位實在不必這樣變相拉票。類似不愿深入走訪,僅靠電話測評的做法,有時容易變相助長虛夸之風。”這位市民說。
曾經,不少江蘇南京市民都接到了一條短信。短信內容寫道:市委某部門將于近期開展電話調查,如您愿意參加,請回復“是”,成為調查候選人。
南京滿意度調查負責咨詢的工作人員表示:“您如果愿意參加,可能隨機抽取到您的電話。如果抽取到了,會有測評員在電話中對您進行一個問卷調查,主要是關于南京市民對公共服務、社會治安等工作的滿意度。”
南京市某區官方微信公眾號此后發文宣傳滿意度調查,其中提到,“‘滿意是您對某區最美的稱贊!”,“請不要使用‘說不清‘不了解‘還行‘還好等模糊語言回答!”盡管官方表示無誘導意圖,只是宣傳措辭不嚴謹,且相關調查并不只是“表面文章”,比如2019年他們收集到3萬多個樣本,形成了4份季度報告,最后還將整理出來的2000多個問題分類送給了各個職能部門進行整改,但依然引起熱議。
除發短信“討好評”外,有的地方擔心被調查群眾“亂說話”,干脆打印“明白紙”,提供標準答案。在大別山區某村,一村民家里有一張關于滿意度提升問卷調查的“明白紙”,里面列舉了11個問題,并在問題后附上了“滿意”“知道”等答案。村民質疑:“答案都有了,還讓我回答啥?”
花錢“求表揚”,也是滿意度虛夸、“注水”的體現,近年來在個別地方也發生過。據報道,有市民反映當地政法系統下發了一份滿意度調查通知,通知提到一定不要用“還行”“不錯”“一般”等模棱兩可的詞語,或“不知道”“沒參加過”等負面性評價;如回答“滿意”“安全”,憑錄音可得100元至300元獎勵。此后,當地6名領導干部因滿意度調查弄虛作假被問責。
“實名制”導向、設置“附加條件”的滿意度調查,也讓調查結果的準確性打了折扣。
華東地區一名市民反映,自己因工作原因與當地政府部門有業務往來,在年底時曾接到一個滿意度調查電話。這名市民向電話調查人員詢問自己的回答是匿名還是實名,得知是“實名記錄”后,只能回答了“滿意”。
不在工作成效上下功夫,卻在“數據滿意”上動腦筋,有的地方甚至出現“代替群眾填寫滿意度評價”現象。北方地區某市轄區一項工作被市有關部門通報指出存在“群眾滿意率低”問題。此后,該區相關干部在業務培訓會上,便示意他人代替群眾填寫滿意度評價,敷衍應付上級整改要求,弄虛作假,造成不良影響。
防止滿意度調查“走過場”
滿意度數據往往成為部門考核或個人考核的重要依據。有的部門單位和干部的政績觀有偏差,為提高滿意度數據,不惜弄虛作假。這不僅違背了大興調查研究的初衷,還把好政策的“經”給念歪了,最終跑偏了方向。
一名基層工作人員表示,滿意度調查在最后的考核占比中較高,如果滿意度不高,不僅會影響其所在部門最后的考核排名,結果還會被通報,所以大家都很重視數據填報這個環節。
然而,在滿意度調查中,如此“引導”“教導”,反映出個別單位存在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問題,讓被調查群眾容易產生只是“走個過場”的錯覺。
“不能總是套用同一種辦法。”有參與滿意度評價的工作人員表示,有的工作經常要跟群眾接觸,但由于其所在崗位的特殊性,接觸到的群眾很難給予其“好評”,若要提高滿意度,就只能另想辦法。
“滿意度電話調查的數據,有時產生的分差微乎其微。”一名基層干部說,“兩個地方某項工作的滿意度分別是96.1%和96.3%,就0.2%的差距,工作方式方法或服務態度能有多大區別?但在考核體系里換算出分值后,排名一下子就拉開了距離。而一旦這一項排名低了,其他工作干得再用心,也是白干。”
擠干滿意度里的“水分”
“讓滿意度調查見實效,必須要大興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對弄虛作假者嚴肅問責。”中部地區某市的一名干部說,只有收集到客觀真實的“民意”,并運用到實際工作中,才能推動相關問題的解決,真正回歸滿意度調查的本意。
在中國社會學會常務理事范和生看來,滿意度調查應當尋求更為科學、多元的評價標準,將群眾評價、專業機構評價、業內評價、上級部門評價等多種手段結合起來,找到更能科學反映部門工作的評價方式,避免盲目追求數字的怪相發生。
多名基層干部和群眾認為,應減少滿意度考核的“數據依賴”,期待更為科學合理的評價方式,真正激發工作活力。同時,各級部門單位要把功夫下在日常,把平時的工作干好、服務做優,讓工作成效經得起時間和群眾的檢驗,從根本上提高群眾滿意度。
(摘編自《半月談》《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