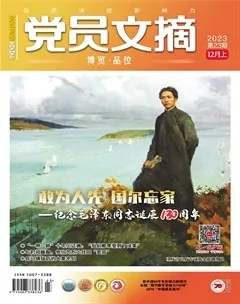今天,我們?yōu)槭裁慈绱诵枰苹?/h1>
2024-01-20 00:06:34
黨員文摘 2023年23期 關鍵詞:科學
“未來像盛夏的大雨,在我們還來不及撐開傘時,就已撲面而來。”《三體》作者劉慈欣曾如此形容科技高速發(fā)展給生活帶來的巨變。
若說能有什么比科學更先觸及未來,那一定是基于科學的奇思妙想。科幻,就是這樣一種產物。它因科學而生,卻又能以想象力為帆,游弋到更為遙遠的時間和空間。
早在100多年前,中國的知識分子便開始有了恢弘的科學幻想。我國最早倡導科幻小說的兩位作家是魯迅與梁啟超。那時,科幻小說被認為具有“開民智”的啟蒙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科幻文學再度興起。在“向科學進軍”的號角聲中,科幻承擔起科普教育的意義,成為“科普隊伍的一支輕騎”。此后,中國科幻幾經興衰,在今天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時代。
毋庸置疑的是,到了今天,科幻的意義仍在不斷延伸。那么,在當下語境之中,當我們談論科幻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一定會談論科學。作為科技進步的文化映射,科幻與科學始終有種奇妙的鏈接,它引人向往科學,探索科學。
一定會談論發(fā)展。當“科幻”一詞后面加了“產業(yè)”,這個詞變得很“值錢”。在中國,這個新興的產業(yè),過去一年的總營收已近千億元。
一定還會談論共識。在宇宙視角之下,科幻描摹的是全人類的命運與未來,其擁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核。科技與想象力是書寫科幻的語言,而這種語言沒有國界。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fā)談論科幻,我們都相信,科幻這束人類文明追夢之光,映照著科技、產業(yè)與未來。
由“智變”引發(fā)的質變
2019年科幻電影《流浪地球》上映后,互聯(lián)網社交平臺的熱搜中破天荒出現(xiàn)了一系列物理學名詞——“核聚變”“太陽氫閃”“洛希極限”……在電影的熱度之下,科學的冷知識似乎也熱了起來。許多媒體平臺紛紛為科研工作者開起科普專欄,以滿足受眾的求知欲。
這是科幻興盛時代所特有的現(xiàn)象——因文學作品所締造的精彩,大眾對科學知識生出向往。
科幻文學是科技時代的文學。克隆、AI、航天、登月……每當人類科技有突破,科幻也往往迎來興盛發(fā)展。但反向推演,科幻的繁榮,是否能夠作用于科學技術的向前?
不可否認的是,確實有許多科學幻想變成現(xiàn)實的真實故事——法國科幻作家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啟發(fā)了潛水艇的改進;“移動電話之父”馬丁·庫帕也承認自己在發(fā)明時,受到過科幻作品的啟示。
生活中,我們可能遇到過這樣的現(xiàn)象:一枚曲別針或一條細鐵絲,在沒有任何工具的情況下,無論使用多大的外力,都不能用手輕易把它拉斷;但如果先用手將它捋直,而后用更小的力來回彎折幾次,無需多時便能將其折斷。這就是所謂的金屬“疲勞”。據(jù)統(tǒng)計,在現(xiàn)代機器設備中,有80%~90%的零部件損壞,都是由金屬“疲勞”造成的。在此基礎上,也正是由于金屬“疲勞”導致的一個細小裂縫,引發(fā)了諸如輪船沉沒、飛機墜毀、橋梁倒塌等災難性事故。
電影《終結者2:審判日》中,反派天網系統(tǒng)將最先進的終結者T-1000送回現(xiàn)實,執(zhí)行刺殺任務。
作為液態(tài)金屬機器人,T-1000展示了一種特殊的能力:偽裝成人類的他,皮膚之下藏有一副銀白色的金屬身體。這不僅讓他可以像橡皮泥一樣隨意變形,還可以無懼爆炸、槍擊等外力造成的傷害。這種擁有“不死之身”的“自愈”能力,讓熒幕前的觀眾大呼過癮,更讓一眾科學家對“自愈”材料的研發(fā)產生了濃厚興趣。
2013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邁克爾·德姆科維奇發(fā)表了一項基于計算機模擬的新理論。他認為,在特定條件下,金屬應該能夠焊接封閉磨損造成的裂縫。這一理論,在桑迪亞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聯(lián)合運營的集成納米技術中心得到了證明。
前不久,該項目團隊的科研人員使用一種特殊電子顯微鏡技術,用來評估裂縫是如何在一塊納米級的鉑金中形成和擴散的。
實驗中,他們以每秒200次的速度反復拉動一片40納米厚的鉑箔,以觀察疲勞裂紋的產生和擴展。起初,裂紋出現(xiàn)在金屬片上并發(fā)生了擴展,但隨后他們意外地發(fā)現(xiàn),實驗進行了約40分鐘后,金屬重新融合在了一起。
近期,《自然》雜志的一篇公開報道顯示,研究表明,純金屬中的“疲勞”裂紋可以進行內在自愈合,稱得上材料界的“破鏡亦能重圓”!有業(yè)內人士指出,利用金屬的自我修復能力,可以帶動相關產業(yè)的發(fā)展,甚至可能引領新一輪的工程革命。
科幻是創(chuàng)新精神的源泉。此時此刻的種種奇思妙想和場景應用,未來或將成為促進新質生產力產生和發(fā)展的關鍵變量,進而不斷催生新興產業(yè)。而因熱愛與情懷驅動的創(chuàng)新探索,才能夠長久地推動科學進步。
科幻是一種理性的浪漫
“站在這顆藍色星球上,遠處是初升的太陽與璀璨的星辰。地平線形成一道弧線,陸地似止于此,而又無限延展。我們可以切出無數(shù)條地平線,但在同一時刻,每個人眼中,只有一條。地平線規(guī)定了視野的最遠處,讓我們不得不著眼于有限的世界中。因此,地平線在哪里,人的視覺認知就在哪里,人的見解與思想就在哪里。”在成都七中科學技術協(xié)會主辦的科技類雜志《未來夢》中,成都七中高三學生林靖杰寫下這段話。這位熱愛科幻的高中生能從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公交車談到全球能源危機,再到人工智能、區(qū)塊鏈等。他所談論的知識點,早已超出高中課本所涵蓋的知識領域。
“初中時好朋友送了我一本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小說里的世界觀很宏大,而且科幻還能用如此理性浪漫的手法折射出一些社會現(xiàn)實問題,這激發(fā)了我對未來的思考。”林靖杰認為,從那時起,一顆叫科幻的“種子”便在他心里生根發(fā)芽了。“初中畢業(yè)的暑假,我在新生夏令營的PPT上看到《未來夢》這本科幻雜志的封面。心想,怎么高中生也能辦雜志?”懷著好奇,林靖杰加入了成都七中科學技術協(xié)會,成為這本科幻雜志的一名編輯,希望能在青少年心里種下科幻的“種子”,將興趣變成志趣,早日實現(xiàn)他們的人生理想。
林靖杰認為,科幻是“理性的浪漫”,其實大多數(shù)科幻創(chuàng)作者都不是宇宙、物理、化學等方面的行業(yè)專家,但當一個天馬行空的幻想出現(xiàn)在他們腦海之后,創(chuàng)作者們總會不遺余力地搜集資料,去推理邏輯,想盡辦法證明它在未來或許是可能發(fā)生的。“這種帶著要證明某種東西去創(chuàng)作的信念,是非常可貴也非常浪漫的”。
像林靖杰這樣“看星星的人”還有很多。
2014年,電影《星際穿越》上映,片中以“黑洞”“蟲洞”“引力波”為線索的科幻世界觀,讓作為研究者的茍利軍大為震動和興奮。了解到該電影的科學顧問、物理學家基普·索恩還寫了一本同名科普書,介紹電影背后的科學故事,茍利軍連夜給這位后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寫了封郵件,熱切希望翻譯這本書。最終,這位專業(yè)級影迷的愿望成真了。40多歲的茍利軍說起這段經歷,眼中閃爍星光。
茍利軍回憶,他之所以會成為“看星星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少年時期讀到科幻雜志《飛碟探索》。而今天,科學家們想做的就是借助科幻熱,讓更多的人熱愛科學、向往科學。
“在全世界科技關聯(lián)度越來越高的今天,面對發(fā)展與未來,人類該怎么走,確實是一件越來越需要討論的事,尤其普通大眾層面應逐漸形成共識”,《科幻世界》雜志主編拉茲認為,在普通大眾層面,要推動共識的形成,科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要知道,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立足過去的,只有科幻是書寫未來的,人們需要這樣一種作品,消解對未知的焦慮,擁抱無限種可能”。
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我們比以往更加需要科幻,它是創(chuàng)新力,是生產力,也是向心力,它讓想象永無邊際,也讓未來更值得期待!
(摘自《工人日報》)
猜你喜歡
點擊科學中國科技教育(2020年2期)2020-12-07 05:55:01 走進科學閱讀(快樂英語高年級)(2020年9期)2020-01-08 02:20:52 走進科學閱讀(快樂英語高年級)(2020年10期)2020-01-08 02:20:31 點擊科學中國科技教育(2019年11期)2019-09-26 10:49:15 點擊科學中國科技教育(2019年10期)2019-09-26 10:48:13 點擊科學中國科技教育(2019年12期)2019-09-23 08:02:08 走進科學閱讀(快樂英語高年級)(2019年3期)2019-09-10 07:22:44 科學大爆炸小小藝術家(2019年6期)2019-06-24 17:39:44 科學今古傳奇·故事版(2016年15期)2016-09-07 06:57:32 科學怪咖科普童話·百科探秘(2016年7期)2016-05-14 10:24:41
“未來像盛夏的大雨,在我們還來不及撐開傘時,就已撲面而來。”《三體》作者劉慈欣曾如此形容科技高速發(fā)展給生活帶來的巨變。
若說能有什么比科學更先觸及未來,那一定是基于科學的奇思妙想。科幻,就是這樣一種產物。它因科學而生,卻又能以想象力為帆,游弋到更為遙遠的時間和空間。
早在100多年前,中國的知識分子便開始有了恢弘的科學幻想。我國最早倡導科幻小說的兩位作家是魯迅與梁啟超。那時,科幻小說被認為具有“開民智”的啟蒙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科幻文學再度興起。在“向科學進軍”的號角聲中,科幻承擔起科普教育的意義,成為“科普隊伍的一支輕騎”。此后,中國科幻幾經興衰,在今天迎來了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時代。
毋庸置疑的是,到了今天,科幻的意義仍在不斷延伸。那么,在當下語境之中,當我們談論科幻時,我們在談論什么?
一定會談論科學。作為科技進步的文化映射,科幻與科學始終有種奇妙的鏈接,它引人向往科學,探索科學。
一定會談論發(fā)展。當“科幻”一詞后面加了“產業(yè)”,這個詞變得很“值錢”。在中國,這個新興的產業(yè),過去一年的總營收已近千億元。
一定還會談論共識。在宇宙視角之下,科幻描摹的是全人類的命運與未來,其擁有著“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核。科技與想象力是書寫科幻的語言,而這種語言沒有國界。
無論從哪一個角度出發(fā)談論科幻,我們都相信,科幻這束人類文明追夢之光,映照著科技、產業(yè)與未來。
由“智變”引發(fā)的質變
2019年科幻電影《流浪地球》上映后,互聯(lián)網社交平臺的熱搜中破天荒出現(xiàn)了一系列物理學名詞——“核聚變”“太陽氫閃”“洛希極限”……在電影的熱度之下,科學的冷知識似乎也熱了起來。許多媒體平臺紛紛為科研工作者開起科普專欄,以滿足受眾的求知欲。
這是科幻興盛時代所特有的現(xiàn)象——因文學作品所締造的精彩,大眾對科學知識生出向往。
科幻文學是科技時代的文學。克隆、AI、航天、登月……每當人類科技有突破,科幻也往往迎來興盛發(fā)展。但反向推演,科幻的繁榮,是否能夠作用于科學技術的向前?
不可否認的是,確實有許多科學幻想變成現(xiàn)實的真實故事——法國科幻作家凡爾納的《海底兩萬里》,啟發(fā)了潛水艇的改進;“移動電話之父”馬丁·庫帕也承認自己在發(fā)明時,受到過科幻作品的啟示。
生活中,我們可能遇到過這樣的現(xiàn)象:一枚曲別針或一條細鐵絲,在沒有任何工具的情況下,無論使用多大的外力,都不能用手輕易把它拉斷;但如果先用手將它捋直,而后用更小的力來回彎折幾次,無需多時便能將其折斷。這就是所謂的金屬“疲勞”。據(jù)統(tǒng)計,在現(xiàn)代機器設備中,有80%~90%的零部件損壞,都是由金屬“疲勞”造成的。在此基礎上,也正是由于金屬“疲勞”導致的一個細小裂縫,引發(fā)了諸如輪船沉沒、飛機墜毀、橋梁倒塌等災難性事故。
電影《終結者2:審判日》中,反派天網系統(tǒng)將最先進的終結者T-1000送回現(xiàn)實,執(zhí)行刺殺任務。
作為液態(tài)金屬機器人,T-1000展示了一種特殊的能力:偽裝成人類的他,皮膚之下藏有一副銀白色的金屬身體。這不僅讓他可以像橡皮泥一樣隨意變形,還可以無懼爆炸、槍擊等外力造成的傷害。這種擁有“不死之身”的“自愈”能力,讓熒幕前的觀眾大呼過癮,更讓一眾科學家對“自愈”材料的研發(fā)產生了濃厚興趣。
2013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邁克爾·德姆科維奇發(fā)表了一項基于計算機模擬的新理論。他認為,在特定條件下,金屬應該能夠焊接封閉磨損造成的裂縫。這一理論,在桑迪亞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聯(lián)合運營的集成納米技術中心得到了證明。
前不久,該項目團隊的科研人員使用一種特殊電子顯微鏡技術,用來評估裂縫是如何在一塊納米級的鉑金中形成和擴散的。
實驗中,他們以每秒200次的速度反復拉動一片40納米厚的鉑箔,以觀察疲勞裂紋的產生和擴展。起初,裂紋出現(xiàn)在金屬片上并發(fā)生了擴展,但隨后他們意外地發(fā)現(xiàn),實驗進行了約40分鐘后,金屬重新融合在了一起。
近期,《自然》雜志的一篇公開報道顯示,研究表明,純金屬中的“疲勞”裂紋可以進行內在自愈合,稱得上材料界的“破鏡亦能重圓”!有業(yè)內人士指出,利用金屬的自我修復能力,可以帶動相關產業(yè)的發(fā)展,甚至可能引領新一輪的工程革命。
科幻是創(chuàng)新精神的源泉。此時此刻的種種奇思妙想和場景應用,未來或將成為促進新質生產力產生和發(fā)展的關鍵變量,進而不斷催生新興產業(yè)。而因熱愛與情懷驅動的創(chuàng)新探索,才能夠長久地推動科學進步。
科幻是一種理性的浪漫
“站在這顆藍色星球上,遠處是初升的太陽與璀璨的星辰。地平線形成一道弧線,陸地似止于此,而又無限延展。我們可以切出無數(shù)條地平線,但在同一時刻,每個人眼中,只有一條。地平線規(guī)定了視野的最遠處,讓我們不得不著眼于有限的世界中。因此,地平線在哪里,人的視覺認知就在哪里,人的見解與思想就在哪里。”在成都七中科學技術協(xié)會主辦的科技類雜志《未來夢》中,成都七中高三學生林靖杰寫下這段話。這位熱愛科幻的高中生能從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公交車談到全球能源危機,再到人工智能、區(qū)塊鏈等。他所談論的知識點,早已超出高中課本所涵蓋的知識領域。
“初中時好朋友送了我一本劉慈欣的科幻小說,小說里的世界觀很宏大,而且科幻還能用如此理性浪漫的手法折射出一些社會現(xiàn)實問題,這激發(fā)了我對未來的思考。”林靖杰認為,從那時起,一顆叫科幻的“種子”便在他心里生根發(fā)芽了。“初中畢業(yè)的暑假,我在新生夏令營的PPT上看到《未來夢》這本科幻雜志的封面。心想,怎么高中生也能辦雜志?”懷著好奇,林靖杰加入了成都七中科學技術協(xié)會,成為這本科幻雜志的一名編輯,希望能在青少年心里種下科幻的“種子”,將興趣變成志趣,早日實現(xiàn)他們的人生理想。
林靖杰認為,科幻是“理性的浪漫”,其實大多數(shù)科幻創(chuàng)作者都不是宇宙、物理、化學等方面的行業(yè)專家,但當一個天馬行空的幻想出現(xiàn)在他們腦海之后,創(chuàng)作者們總會不遺余力地搜集資料,去推理邏輯,想盡辦法證明它在未來或許是可能發(fā)生的。“這種帶著要證明某種東西去創(chuàng)作的信念,是非常可貴也非常浪漫的”。
像林靖杰這樣“看星星的人”還有很多。
2014年,電影《星際穿越》上映,片中以“黑洞”“蟲洞”“引力波”為線索的科幻世界觀,讓作為研究者的茍利軍大為震動和興奮。了解到該電影的科學顧問、物理學家基普·索恩還寫了一本同名科普書,介紹電影背后的科學故事,茍利軍連夜給這位后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寫了封郵件,熱切希望翻譯這本書。最終,這位專業(yè)級影迷的愿望成真了。40多歲的茍利軍說起這段經歷,眼中閃爍星光。
茍利軍回憶,他之所以會成為“看星星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少年時期讀到科幻雜志《飛碟探索》。而今天,科學家們想做的就是借助科幻熱,讓更多的人熱愛科學、向往科學。
“在全世界科技關聯(lián)度越來越高的今天,面對發(fā)展與未來,人類該怎么走,確實是一件越來越需要討論的事,尤其普通大眾層面應逐漸形成共識”,《科幻世界》雜志主編拉茲認為,在普通大眾層面,要推動共識的形成,科幻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要知道,幾乎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是立足過去的,只有科幻是書寫未來的,人們需要這樣一種作品,消解對未知的焦慮,擁抱無限種可能”。
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我們比以往更加需要科幻,它是創(chuàng)新力,是生產力,也是向心力,它讓想象永無邊際,也讓未來更值得期待!
(摘自《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