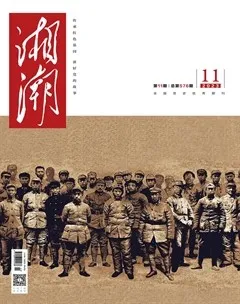調查研究: 毛澤東的謀事之道、成事之基
陳晉


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游學,本質上就是一種對社會的調查研究
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喜歡游學。他經常走出自己生活學習的地方外出游學,其中最著名的有兩次“游學”。一次是1917年同蕭子升,歷時一個月,漫游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縣,步行近千里,寫下不少筆記和心得。一次是1918年同蔡和森,繞洞庭湖轉了半圈,還將沿途的見聞、感想,寫成通訊寄給《湖南通俗教育報》。
社會是一本讀不盡的無字之書。青年毛澤東喜歡游學,就是把學習放在路上,或者說是在路上學習,俗稱“行萬里路,讀萬卷書”。
所謂游學,本質上就是社會調查。再深入一點,叫作調查研究。調查研究的對象是大地山川,民風世俗、社會情態、歷史風貌,這些是社會這本無字之書呈現給調查研究者的生動內容。有些時候,這些內容比讀有字之書來得興趣盎然,來得具體貼切,來得直入人心,來得醍醐灌頂。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游學,作為一種社會調查途徑,實際上是向人民、向實踐、向歷史、向自然學習的方式。
調查研究既然是一種學習方式,前提是放下身段做“小學生”
讀無字之書,應該有相應的學生姿態,不要弄成自己什么都懂的模樣去居高臨下地詢問和視察,更不要不懂裝懂地面對老百姓去指點江山和規劃未來。果真那樣,是學不到東西的;果真那樣,你打開閱讀的肯定不是無字之書,而是自己早已設計好的“主觀藍圖”;果真那樣,甚至都算不上是在調查研究。
關于讀無字之書,毛澤東有三條主張格外重要:拜人民為師,“甘當小學生”;“邁開你的雙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像孔夫子入太廟那樣,不懂的地方“每事問”;不做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確實是這樣做的。中央蘇區時期,他在興國做調查的時候,幾個農民態度疑懼,臉上沒有一點笑容,不愿意和毛澤東交往,更不愿多講。沒有學到東西的毛澤東就請這些農民吃飯,晚上又給他們被子蓋,這些農民才慢慢有點笑容,開始說話,最后放下戒備,參加討論,無話不談。結果是毛澤東學到了東西,獲得了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毛澤東1941年還感慨回憶:“這些干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采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
毛澤東的革命生涯起步于社會調查,他也正是在大量調查研究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共產黨道路探索的先行者、引領者和奠基人
1921年建黨以后,毛澤東真正成了浪跡天涯的游學者。如果說青年時代的游學多少帶有好奇,多少有些“有意為之”的話,那么,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他的游學便是“別無選擇”的工作和生活。真正的革命家幾乎都是四處奔走的游歷者。更何況,中國革命的流向,本來就是散落于城市、相聚于鄉村,然后又蔓延、匯合,朝城市滾滾而來。空間的轉換,一道道革命難題的涌現,怎能不讓革命家“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去叩問大地,叩問蒼生,叩問實際。
毛澤東在建黨伊始,最著名的調查研究,就是手持一把雨傘,到安源去發動工人運動。還有他1925年回故鄉韶山搞農民運動,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農村階級關系的緊張。從此,他把革命的重點轉向了農民。1926年在廣東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一個著眼點,依然是帶領學員深入韶關一帶去搞調查研究。大革命即將失敗前夕,他深入湖南農村做的農民運動調查,使他在黨內別具一格,脫穎而出,成為中國農民運動的“王”。在土地革命時期,他在井岡山和贛南閩西農村做的調查,不下15次,到延安時,還能找到11個調查報告。對丟失的調查報告,他終生牽掛。
正是在調查研究的路上,毛澤東被歷史選擇。毫無疑問,愿不愿意、能不能夠、善不善于搞社會調查,不是一件小事。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在黨內領導層脫穎而出,被領導團隊選擇為領導核心,固然有許多因素,但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他手里時時握著調查研究這把能夠挖出中國革命道路真實模樣的鋤頭,使他觀察和描述中國社會的能力,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的能力,高于眾人不少尺寸。
道路決定命運。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奮斗的一個重點,就是探索、選擇、實踐、拓展前進的道路。毛澤東的最大貢獻,是一生通過大量的社會調查,總是走在前面,成為中國共產黨道路探索和拓展的先行者、引領者和奠基人。
他領導開辟和拓展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與他無數次做農村社會調查有關。
他領導創造和實施了社會主義改造道路,與他1953年到武漢等地了解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現狀有關;與他1955年及時了解農村土地改革后的發展趨勢,進而把來自全國各地基層的新鮮材料,編選成《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還寫下一百多篇按語有關,他說自己這是在“周游列國”。
他領導探索和實踐了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與他集中花43天時間找國務院34個部委的負責人詳細調研有關,與他親自主持三個農村調查組深入農村生產大隊調研有關,更與他每年都有大約三分之一的時間走出北京,到各地工廠農村等基層社會調研有關。他曾這樣評價外出視察:我在北京住久了,就覺得腦子空了,一出北京,腦子里又有了東西。
從1958年開始,毛澤東還醞釀過一個更大規模的國情調查:騎馬沿黃河和長江流域深入考察,還要帶上各行各業的專家一起去。他說,自己要學明朝的徐霞客,“那個人沒有官氣,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長江的發源”“他就是走路,一輩子就是這么走遍了”。可惜,在1964年即將出發的時候,因為美國軍隊侵略越南北方,周邊形勢陡然緊張,沒能成行。直到1972年初他一次突然休克,蘇醒過來后還心心念念自己沒有實現騎馬考察黃河長江的愿望。
這就是永遠在路上的毛澤東。
讀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不可偏廢
調查研究強調讀無字之書,但毛澤東之所以行高于眾,不單單是因為他執著于讀無字之書,也在于他酷愛并善讀有字之書。毛澤東是黨內最喜歡讀這兩本“書”的典范。他善讀苦讀無字之書,開創了中國共產黨調查研究這一“可大可久”的謀事之道、成事之基;他善讀苦讀有字之書,去粗取精、出神入化,開拓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新道路。
讀懂社會與讀懂書本是不能分割的。讀書是學習,調查也是學習。只會讀書,并不意味著你會學習;只會調查,也不意味著你會學習。毛澤東一生追求的,是把讀無字之書和有字之書結合起來。比如,他說徐霞客正是因為跑遍長江流域搞調查,才發現金沙江是長江的發源,進而改變了“岷山導江”的傳統觀點。他還說,如果蒲松齡不在路邊設攤擺茶,請來往行人講鬼怪異事,就寫不出《聊齋志異》。
讀書是向前人的經驗學,向別人的經驗學;調查是向當地的群眾學,向眼前的實踐學。讀書可以思接千載,神游八荒,獲得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思想資源;調查則由問題導向,直面現實,獲取實踐的材料,去尋找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現實經驗。
讀書是為了向上成長,調查則可以向下扎根。向上成長,必須超越眼前,站在前人和別人的肩膀上,來總結經驗,這樣,你的站位就高出許多。向下扎根,就是你的思想、決策、行動要有泥土氣、煙火氣,要來自群眾和實踐,要解決問題。
強調讀有字之書,可以避免經驗主義。所謂經驗主義,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我們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實際工作中會遇到把什么事都看成“中心”,一會兒這個戰略,一會兒那個戰略。結果是,在實際操作中,往往相互打架,相互抵消,事情搞得一團糟。經驗主義不注重總結規律,缺少全局思維和長遠思維。
強調讀無字之書,可以防止教條主義。所謂教條主義,就是完全按照書本上的辦法去辦,按別人的和前人的經驗去辦。中國共產黨人還不成熟的時候,就習慣于把馬克思主義的具體論述教條化、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蘇聯革命經驗絕對化。教條主義者容易忽視乃至輕視中國國情和中國具體實際,在思想上和實踐上都有嚴重的依賴癥:理論指導上的依賴和解決問題的路徑依賴。
在某種程度上說,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在思想方法上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不懂辯證法,思維片面、單一、機械。教育家陶行知說過:“中國有三種呆子:書呆子、工呆子、錢呆子。書呆子是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錢呆子是賺死錢,死賺錢,賺錢死。”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都是陶行知說的“呆子”,一個是“工呆子”,一個是“書呆子”。要克服這兩種思維傾向,避免做“書呆子”和“工呆子”,辦法就是善于讀有字之書和無字之書,把這兩種看起來不相關的學習方式統一起來。歸根結底,就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
(作者系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國毛澤東詩詞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