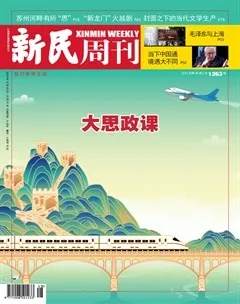封面之下:當代美國的文學生產
談炯程

美國社會學家克萊頓·柴爾德斯的《封面之下:一本小說的創作、生產與接受》為我們講述了一個典型的出版故事:圍繞著作家科尼莉亞·尼克森的長篇小說《賈勒茨維爾》在寫作、出版期間以及上架后所遭遇的種種,某種張力在封面之下被創造了出來。
《封面之下》所呈現的當代美國的文學生產流程,是高度細分,并且市場化的。相較中國,在美國的文學生產中,作家只負責創作,編輯只負責審讀稿件,作家與雜志社、出版社之間的對接,則交給專業的文學代理人。而文學代理人入職門檻比編輯低得多,這導致了文學代理人行業魚龍混雜,其中充滿了克萊頓·柴爾德斯所說的“掠食者”,他們專門撲向尚未被文學場域接納的新手,從這些渴望成功的人身上榨取油水。即使是專業的文學代理人,他們中的一部分,也只是為了賺取天價傭金而從事這一行業。這些人不熱愛閱讀,文學品味也無從談起。
然而,在流行文化與逐利的商業邏輯的雙重風蝕下,真正支撐起美國文學的生產的,卻并非古典經濟學中市場那“無形的手”,而是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美國國家藝術基金會(NEA)在這一領域持續不斷的資金投入。70年代時,NEA的“發現”津貼支持了無數貧窮但有才華的作家。同時也正是在NEA的引導下,2000年以來,創意寫作MFA項目在全美校園內的數量呈井噴式增長,最近20余年新增的MFA項目,超過自1936年愛荷華作家工作坊創立以來整個20世紀曾開設過的MFA項目的總和。因此,諸如科馬克·麥卡錫、科尼莉亞·尼克森之類美國當代作家的生平,比之他們20世紀上半葉的前輩,要平淡得多,他們幾乎不必夾在文學與生計之間過著雙重的人生,而是輾轉于一項又一項津貼,一個又一個教席之間。
這種現象,似乎也讓我們不合時宜地想到希臘詩人卡瓦菲斯寫于1896年的詩作《墻》,其中有這么幾行:“當他們在筑這些墻,我怎么會沒注意到!/但我沒聽見那些筑墻的人,一點聲音也沒有。/不知不覺地,他們把我與外面的世界隔絕了。”在克萊頓看來, MFA項目的真正目的,并非只是塑造下一代的作家。事實上,許多MFA項目畢業生,在經年累月學習后,除了背上高額學生貸款外一無所得。MFA項目最卓有成效的貢獻,是為美國大量的中層作家創造了穩定收入,并且為當代文學塑造出大量穩定且相對專業的讀者。一位中層作家,大可以透過其在MFA項目任教時的人脈網絡,獲得一批又一批固定讀者,而不必直面圖書市場上的殘酷搏殺,在那里,即使一本在藝術造詣上過硬的小說,都未必能獲得成功,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在初版時銷量不佳,戈爾丁的《蠅王》出版第一年的銷量甚至不足250本。經由MFA項目在全美的普及,當代美國文學已經有了一個內循環的機制,以支撐大量庸作的存在。
或許,免去日常生活苦役的美國作家,可以更多地轉向一種本質性的沉思,從MFA項目庇護下生成的文學礦脈中,會有人煉出質地堅實的合金,足以斬斷既有文學建制的話語慣性,就像費爾南多·德爾·帕索的《帝國軼聞》抑或大衛·福斯特·華萊士的《無盡的玩笑》,這個場域仍向未來的可能性敞開著。
《印度藝術》梳理了南亞次大陸從公元前300年至21世紀藝術發展的歷史,追溯了佛教、印度教、耆那教、伊斯蘭教、基督教贊助人和工匠如何創造出符合不同的宗教和意圖的豐富的藝術形式;石窟、神廟、雕塑、繪畫等又如何為不同時期的政權服務。通過探究藝術生產與贊助、個人創造力與統治意識形態間的互動,平衡印度教、佛教的影響和一直以來被低估的印度伊斯蘭藝術、殖民時期和現代藝術的成就,書中的每個時期都呈現出其獨特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