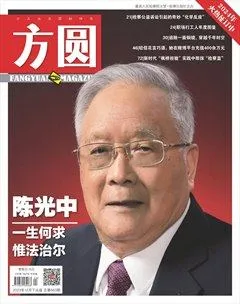職場打工人年度圖鑒
劉亞
清晨5點,天色未亮,寒風呼嘯,北京市通州區馬駒橋勞務市場已迎來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候。聚集在這里的務工人裹緊雷鋒帽、厚外套,焦急地等待來接他們務工的車輛。
深夜,大廠里剛加完班的打工人,終于能活動下因久坐而僵硬的腰椎和頸椎,準備從網約車軟件里打個車回家。
網約車上,后排打工人昏昏欲睡,前排司機只能嘆氣,“別人能睡自己可不行”——盡管已連續開了幾個小時車,但接單不能停,夜越深往往意味著越高的工作補貼。
網約車司機抵達目的地停車送客時,正好一位外賣騎手駕駛電動車從旁飛馳而過。司機驚得一身冷汗,外賣騎手卻習以為常——他必須準時送達,不然可能會被點餐的人差評,甚至被平臺扣補貼。
點了夜宵的36歲劉女士卻沒有沒胃口,因為在網絡招聘平臺投遞了簡歷,被一家公司負責人嘲諷:“36歲來碰瓷公司啊?”這讓劉女士心情非常低落,認為自己的人格尊嚴被傷害了。
…………
這一年,職場人一邊自嘲“脆皮”,一邊努力又頑強地工作著。從我近幾年采訪各類勞動者權益相關的案件來看,職場人面臨著加班關、薪酬關、年齡關、性別關,而隨著新業態勞動工種的出現,職場里的各類難關越發層出不窮。但關關難過關關過,從保障生命健康、工資薪酬到人格尊嚴,法治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實踐正在不斷深入推進。
馬駒橋務工人的日與夜
在北京,流傳著這么一句話:“落難必闖馬駒橋。”如果想深入了解真正的打工人,那么一定要闖一闖馬駒橋。2023年底,我探訪了這個北京最大、外地務工人員最多的勞務市場。
在馬駒橋勞務市場,聚集著大量有臨時工、日結工需求的務工人,沿街商鋪也多是勞務中介公司。沿著街道岔路往胡同深處走,便是務工人高度聚集的日租房和長租房。
無合同、無保險、超長“待機”是這里務工人的常態。有別于早年招零時工的方式,現在招工多數是在微信群進行。沿街勞務公司門口貼著各種招工群的二維碼,群里每天都會發布非常多的招聘信息。如果有打工意愿并符合招聘條件的,務工人便可接龍報名、登記信息。這一個個“接龍”便是工作的全部證明。這種情況下,勞動者合法權益保障著實令人擔憂。
在與周圍人的交談中我還得知,今年勞務市場對臨時工、日結工的需求不高,工資也由以往的一天二三百元跌到100多元,招工條件也變得苛刻,例如需要35歲以下的青壯年等。這也讓年近50歲的李某和魏某夫婦曾格外犯愁。
半年前,李某和魏某在山西老家“快手”平臺的直播中看到北京一些大型快遞公司招聘快遞裝卸和分揀員,被直播中的“快遞公司直聘、包吃包住、高薪、月結工資”等條件吸引,于是來北京打工。但到北京后的前3個月,他們每天工作時長達12小時,各自只拿到了2000多元的工資,與最初招聘者承諾的薪水相差甚遠。兩人多次討要工資未果,便撥打12345市長熱線向勞動監察大隊反映情況。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李某和魏某因不符合招聘條件,找不到工作。然而在北京每多待一天,就要多花一天40元錢的房租,即便早餐是開水沖麥片,午餐是10元錢的盒飯,晚餐在出租屋里做青菜煮面,對夫婦倆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李某和魏某的窘境隨著檢察機關的介入被打破。通州區檢察院民事檢察部收到了相關線索后,發現現有證據根本無法確認勞務關系和用工薪資。于是,通過與勞動監察大隊溝通調查,檢察官找到了公司的人事負責人,結合《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向其釋法說理,建議該公司先從內部用工打卡小程序上核實其身份信息及具體工作時長,結合同類型用工協議查清薪資數額;督促該公司清償李某和魏某的工資,后續再依法向相關外包公司或責任人追償等。
短短10天內,通過通州區檢察院與勞動監察大隊協同履職、共同推進,涉案公司向魏某、李某支付了工資尾款。當我在夫婦倆的出租屋里見到他們時,他們已收拾好行李準備離開北京了。“多虧了檢察院幫我們要回了工資,我們非常高興,也特別感謝他們。”夫婦倆說。
外賣騎手囿于“算法”
李某和魏某夫婦的經歷讓異鄉打工人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溫暖,但也反映出一個很突出的問題:直播間里應聘工作,這種以網約形式建立的勞動、勞務關系,誰才是真正的“東家”?
這讓我想起在2018年做過的一篇外賣騎手“東家”之爭的深度報道。當時,一名外賣騎手送餐時摔成腰椎粉碎性骨折,在需要雇主承擔部分醫療費時才發現自己的“東家”不是美團,而是一家外包公司。在采訪中我進一步發現,類似案件也集中出現在快遞、餐飲、網約車等勞動力密集型的服務行業。

2023年12月,寒潮來襲,外賣騎手堅守崗位,寒風雪地中進行配送。(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如今5年過去,“東家”的問題已不成問題,外賣騎手陷入了新的困局中。隨著城市里外賣騎手注冊人數幾近飽和,他們穿梭在街道、與時間賽跑,不知不覺已成為城市的一道風景,也帶來一定的安全隱患、治安糾紛。這些風險一旦發生,帶給騎手的傷害和損失往往更甚。此時騎手權益問題,除了與“東家”勞動關系認定難,更多是囿于“算法”,職業安全風險高、社會保障水平低等突出問題。
什么是算法?我與餐飲店里一些等餐的外賣騎手聊過這方面問題,他們并不清楚這個詞意味著什么,只知道這是他們薪酬的“晴雨表”:如果收到差評或投訴,他們會被罰款,甚至停號。就像多米諾骨牌一樣,為了提高收入,騎手只能盡可能接更多的單、更快送單。這可能導致的超長工作時間和違反交通規則不僅威脅騎手安全,也影響社會安全。
這些日益突出的問題也引發了社會公眾對平臺濫用算法的強烈質疑,要求加強算法監管。2022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出現的外賣騎手等靈活就業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突出問題立案并成立專案組。這是對外賣騎手權益保護的一次重大升級。
比如,江蘇分組重點調查某科技公司提供外賣騎手注冊個體工商戶服務是否停止,前期注冊成個體工商戶的外賣騎手是否進行注銷及刪除清理個人信息,相關勞動仲裁、裁判是否認定外賣騎手個體工商戶身份不符合實際,外賣平臺是否涉嫌借此逃避稅收等問題。
上海分組則依托電動自行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安全生產領域拓展外賣騎手勞動權益保障領域公益訴訟。針對電商平臺入駐商戶違法銷售電動自行車電池、充電電瓶修復器以及提供加裝、改裝、定制電池服務等違法情形,督促電商平臺和生產經營單位履行產品質量安全和公共安全社會責任。
如今,城市里每天風里雨里送餐的外賣騎手,不管是被“限制”的車速,還是頭上的各種頭盔,都是對他們自身的安全保障,也給城市交通安全帶來穩定,這里面有檢察機關付出的努力。
在進一步的新業態勞動者權益保障中,檢察機關也希望相關企業將外賣騎手權益保護的數據和舉措更新至2023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并如期公布。在最高檢專案支持下,通過企業自主行為更加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推動平臺經濟高質量健康發展。
“脆皮”打工人
距離通州區馬駒橋勞務市場50多公里開外的海淀區西二旗大廠,深夜11點依舊燈火通明。不少在大廠的打工人告訴我,因為久坐、坐姿不良等原因,他們多數患有頸椎、腰椎等各類毛病,年輕人也難逃此劫。他們自嘲“脆皮”,但仍然習慣性加班。
即便法律上早已明確“996”違法,這些問題依舊普遍存在于互聯網大廠等企業之中,侵害了勞動者休息權、健康權、報酬權等合法權益。2021年6月1日,最高檢對“996”侵害勞動者權益問題直接立案辦理,成立“996”專案組。
2022年兩會期間,我把這個問題帶給了有“打工人代言人”之稱的全國人大代表董明珠。在采訪中董明珠建議對“996”工作制開展公益訴訟,并表示:“有些崗位由于工作性質的原因適當延長工作時間,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企業置員工的身體、心理健康于不顧,這是絕對不可行的。”這條建議隨后在網上引發上千萬次討論,不少網友紛紛留言表示支持。

《方圓》2023年11月下刊推出的《36歲女子求職竟被嘲“來碰瓷”》一文,講述了36歲女子在求職中被公司嘲諷,為自己維權的故事。
這條被稱為“打工人之光”的建議同樣引起了最高檢關注。在采訪中我了解到,專案組在梳理相關法律法規、分析裁判文書,走訪行政機關、相關組織、企業,調取勞動監察執法和勞動爭議仲裁等資料后發現涉及“996”侵害勞動者權益的違法點,并形成詳盡的分析研判報告。
在專案組的指導下,專案分組主動與人社部門、當地工會等行政機關和組織進行深入溝通交流,在案件線索移送、溝通協調配合等方面達成一致意見。當然,檢察機關的工作沒有止步,接下來還將會同當地人社、總工會、婦聯、衛健等單位聯合發出倡議,倡導企業、社會、家庭及勞動者自身,增強健康工作意識,營造健康工作文化,完善健康工作保障。
保護職場女性的人格尊嚴
隨著法治的進步與完善,勞動者對自身權益保障的意識逐漸增強,特別是當女性遭遇職場歧視時,也會勇敢地選擇用法律武器維權。
2022年10月,36歲的劉女士為了求職,在網絡招聘平臺公開發布了個人求職簡歷,不料卻遭遇一家公司嘲諷:“人力資源也來做聯合合伙人?”“36歲來公司碰瓷啊?”在劉女士提出警告后,公司還進一步對劉女士進行職業貶低侮辱,并惡語貶低羞辱。劉女士說,她的人格尊嚴受到傷害,因此出現了精神迷茫、焦慮、抑郁和失眠。
劉女士將公司告上法庭。經歷近一年時間,該案終于塵埃落定:被告公司于判決生效后5日內通過在媒體刊登道歉聲明的形式向原告劉女士進行賠禮道歉,并賠償原告劉女士精神損害撫慰金1萬元。
審理該案的法官告訴我,勞動者依法享有平等就業和自主擇業的權利。公司在案涉招聘信息中針對劉女士的欺辱性言論,實質上是從精神層面對劉女士追求自主擇業的自由意志、通過勞動就業追求幸福生活和獨立人格發展的一種嚴重侵擾和扼制。公司行為已構成對劉女士自主擇業意志自由和人格發展、尊嚴所體現的一般人格權的嚴重侵害。
這起案件在保障職場女性合法權益有一定典型性,也是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完善和婦女維權意識增強的體現。這讓我想到近期的另一起案件——2023年11月,有不良網紅在網上冒充外賣騎手。她們穿著代表騎手的服裝黃色工服,下身穿著短裙,拍攝制作“外賣媛”等“擦邊”照片和視頻。外賣公司隨后對這4名為獲取流量而冒充騎手,長期進行虛假擺拍、損害騎手形象的網紅提起訴訟。
事實上,工服是職業的象征,體現勞動者的風采,不良網紅穿上騎手工服進行低俗露骨的擺拍與炒作,不但損害騎手們的形象,也是對廣大女性形象的損害,更可能導致女性就業空間的壓縮。
該案的進一步發展,公眾拭目以待。在我看來,一方面,勞動者在提供勞動獲取經濟利益的同時,理應獲得作為人所擁有的體面和尊嚴。而如何讓職場人更加體面、有尊嚴地工作,這是全社會需要考慮的問題。另一方面,檢察機關近年來把反性別歧視、加強職業保障、反人格貶損等問題作為婦女權益保護的重點工作來抓,將婦女就業權益保障從招工歧視向其他領域拓展。在“外賣媛”案中,除了外賣公司起訴,這種惡意擺拍的行為是否也傷害了廣大婦女的人格權益,檢察機關是否應有所作為?
跨國求職之困
回顧我采訪過的勞動者群體中,有一類打工人相對特殊,他們的“職場”堪比“戰場”,不在國內,而是在邊境線外的東南亞。近年來,境外犯罪組織通過網絡招聘等各種手段,定向誘騙國內求職人員出國從事針對國內的違法犯罪活動,影響社會安定和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引起各方高度重視。
在對這些人做調查時,我發現他們大多數是通過網絡招聘平臺應聘工作,在與“蛇頭”對接后偷渡到境外的。他們中有的人不僅面臨被毒打、關水牢、噴辣椒水、灌陳醋,甚至成為運毒品的“騾子”。那么,網絡招聘平臺究竟存在哪些問題,對跨境犯罪起到了哪些作用,又應該如何規范?
針對網絡招聘亂象,我還在幾個知名平臺進行了臥底調查。“月入過萬”“包吃包住”“報銷機票”,在網絡招聘平臺上經常能看到工作要求簡單、報酬豐厚的出境務工招聘信息。聯系對方后,他們會告訴求職者這份工作有多誘人,但不會告訴求職者,所謂的高薪工作就是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網絡賭博等各類犯罪的一環。
從招聘需求來看,犯罪分子在招聘時往往會設置文員、客服、銷售等專業技能要求不高的工種來吸引求職者,即便招聘崗位顯示招聘專業的人員,也往往不要求應聘者必須具備相應的專業知識。一些年輕人受經驗、資歷等因素影響,求職時也往往選擇對學歷、技能、職稱、工作能力要求不高的崗位,因而極易掉入犯罪分子挖掘的“陷阱”。從案件情況看,二三十歲的待業青年更易通過網絡招聘尋找工作而被騙。
從招聘公司來看,“大平臺”加上“大公司”容易成為掩蓋其犯罪事實的華麗“外衣”。犯罪分子設有公司、工作室,或借用其他公司名義進行招工,極易讓求職者誤認為是正常應聘參加工作。此外,我在調查時還發現,招聘方與后臺通過審核的公司不一致,招聘平臺模糊招聘方的情況確實存在。
為了保障求職者的合法權益,讓其不再掉入違法招聘的陷阱,檢察機關也提出相關建議,進一步加強網絡招聘監管力度,不僅要完善信息發布審核監管機制,還要加強對招聘信息的篩查、過濾、網上巡查,從源頭上防止虛假招聘信息通過網絡傳播。
在接下來的工作中,檢察機關堅持依法能動履職,以“我管”促“都管”,督促有關部門加強對網絡招聘的監管,共同防止此類案件反復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