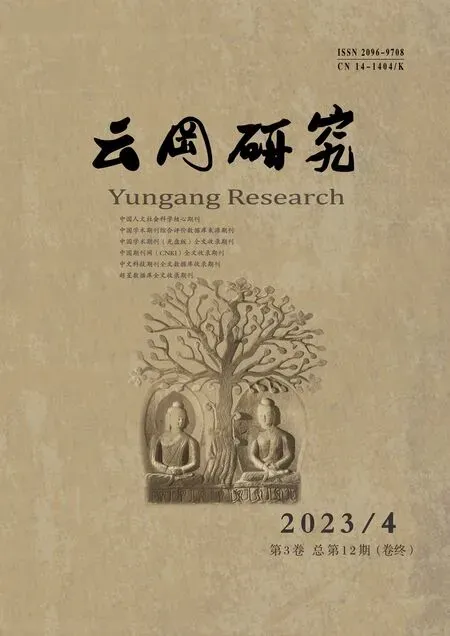云岡石窟大型洞窟的營造背景
黃 盼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010)
云岡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北,目前共有主要洞窟45座,附屬窟209座,[1][2]集中分布于武州山南麓的三個崖面上。大型洞窟為東部崖面的第1、2、3窟、中部崖面的第5-13 窟及西部崖面的第16-20 窟。北魏時期第3窟在開鑿洞窟的階段停止施工、第11窟中心柱未完成、第17窟地面及主尊腳部未完成。對于這些大型洞窟的營造背景,一般是根據洞窟形制及圖像等對洞窟的營造時間進行排序,并進一步通過文獻或圖像學對營造背景進行推測。現在的主流觀點一般將第16-20窟劃分為第一期,是《魏書》所載沙門統曇曜發愿由文成帝出資于和平年間(460-465年)營造,即曇曜五窟。第二期為第1、2、5-13窟,時間為孝文帝初期至太和十八年遷都洛陽(471-494年)。①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新發現的大同云岡石窟寺歷史材料的初步整理》,《北京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56年第1期,第71-84頁;宿白:《云岡石窟分期試論》,《考古學報》1978年第1期,第25-38頁;宿白:《〈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發現與研究——與日本長廣敏雄教授討論有關云岡石窟的某些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 年第2 期,第29-49 頁;宿白:《平城實力的集聚和“云岡模式”的形成與發展》,《中國石窟·云岡石窟》(一),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76-197頁。宿白結合《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記載,提出第7、8 窟為孝文帝所開,為遼代的護國寺,第9、10 窟為鉗耳慶時于太和八年至太和十三年營造,[3]此外從規模及造像題材推斷第5、6窟為孝文帝所開鑿的皇家工程。[4]但由于云岡石窟帶有紀年的材料較少,對于洞窟營造的具體年代,特別是第二期各窟仍有較多爭議。尤其是近年岡村秀典將第5、11、13窟提前,認為僅次于曇曜五窟營造,[5](P1-52)并通過圖像學分析判斷第5、13窟是獻文帝分別為文成帝及自己而造。[6](P100)基于以上探討可知云岡石窟的大型洞窟并非均為皇家工程,很可能有著不同的出資人,但并沒有一個可進行區分的明確標準。石窟的營造涉及不同人群,如出資人、指導僧侶、工匠等,其中工匠是施工者,而在圖像題材、洞窟形制的選擇和創造上,出資人、指導僧侶等才是關鍵,這些與開窟造像活動直接相關的人物往往會以供養人圖像的形式出現在洞窟之中。云岡石窟中保存有數量眾多的供養人圖像,雖然大部分未保存下銘文,但通過這些圖像可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云岡石窟大型洞窟的營造背景。本文將以供養人圖像為著眼點,通過供養人圖像與石窟的關系,對云岡石窟大型洞窟的出資人及營造背景進行探討。
一、云岡石窟供養人圖像及其含義
云岡石窟的大型洞窟主要營造于遷都洛陽之前,作為本文的前提,需要明確北魏平城時期云岡石窟供養人圖像的特征及含義。云岡石窟的供養人形象一致,身著胡服或漢服,或立或跪,既可附屬于單獨小龕,亦可附屬于整個洞窟。洞窟的供養人圖像一般以列像的形式布置于下部空間,單獨小龕一般也將供養人置于佛龕下部,偶爾也會雕刻于龕楣兩側、龕柱前方等位置。下文通過帶有銘文的龕像進一步考察供養人圖像的含義。
云岡石窟第20 窟右脅佛頭光正上方有一尖拱龕,龕上方為僅露出頭部或上半身的供養天人,龕左側雕刻有長條形榜題、一供養天人的上半身、一跪姿男性供養人像(圖1-1)。供養人前方刻銘尚可辨識出“佛弟子蓋□。為七世父母。所生父母□□”,[7]長條形榜題刻銘“□□□及知識造多寶佛二區”,[8](P5)可知該像是世俗信者為父母所造。雖然該龕保存的不完整,但從壁面布局來看,相對一側并沒有再容納供養人圖像的空間,這個身著胡服的跪姿供養人圖像表現的應是造像主本人。

圖1 北魏平城時期的供養人圖像
云岡石窟第11 窟明窗太和十九年(495 年)常山太守妻周氏為亡夫、亡子、亡女所造之像(圖1-2),下部銘區左側為二僧侶二胡服男性,右側為二僧侶二胡服女性,均朝向主尊。供養人旁雕刻出人名,可知左側由二比丘先導后為亡夫、亡子,右側由二比丘尼先導后為周氏及亡女,表現了一個小家庭。
進一步將人數增加至20 人左右,并且男女分列的圖像在云岡也較為常見,但均沒有銘文。作為參考,可以舉出鄴城遺址出土的劉伯陽造像。太和十九年“劉伯陽為居眷男女大小敬造釋迦牟尼石像一區”(圖1-3),造像正反共雕刻18 人,除一人未刻姓名外,分別是劉伯陽的亡父、母、自己、姐、妻,及七兒、五女,表現了以造像主為中心一個大家族的三代人。其中父母位于正面、自己與一兒在左側面、姐與妻在右側面均朝向正面主尊。像背分四層,最上層為一坐佛,坐佛兩側的供養人與第二層的供養人除未刻銘一人外均為女兒,朝向該坐佛。下二層供養人為六兒,朝向正面主尊,為左側面男性列的延續。
人數進一步增加,如云岡石窟第11 窟太和七年(483年)邑義54人“為國興福”所造龕像(圖1-4、1-5),表現出數量眾多的供養人圖像。男女分列四層,均朝向主尊,其中左側男性殘存16 人,①銘文為54人,現殘存世俗形象52人,僧侶6人,所以54人內應不包含僧侶形象,目前左下角殘損部分可容納2人,男性原本很可能為18人。右側女性36人,2倍于男性,最上層隊首各一僧侶形象,其中一人殘留邑師的榜題,下層四位僧侶位于隊首,形象較大,占據二層空間,其中三人殘留邑師的榜題。
此外,還有僅有僧侶形象的造像。如云岡石窟第17 窟明窗太和十三年(489 年)“比丘尼惠定,身遇重患,發愿造釋迦多寶彌勒三區”,共雕刻8位僧侶形象的供養人。
通過以上實例,特別關注人數、性別及身份的話,可以看出平城時期云岡石窟的供養人圖像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供養人均朝向主尊排列;
第二,男女同時出現時,一般男性在左側,女性在右側,即以左為尊。此外的身份差僅表現在圖像大小及距離主尊的遠近;
第三,圖像中登場的人物均與造像活動相關,如造像主、回向對象及僧侶等;
第四,同時出現多人之時,特別是超過20人的情況下,與邑義等集團造像相關的可能性很高。20 人以下以個人造像為主。
二、云岡石窟供養人圖像與洞窟的位置關系
前文已明確供養人圖像的含義,接下來對云岡石窟大型洞窟的供養人圖像進行具體分析。按照供養人圖像與洞窟的相對位置關系,可將大型洞窟分為二類:
A類:洞窟整體沒有對應的供養人圖像。
B類:洞窟整體有對應的供養人圖像。
(一)A類洞窟
洞窟整體沒有對應的供養人圖像,具體為第5、13、16-20 窟。七座洞窟均為大像窟,主尊巨像占據窟內的主要空間,為洞窟的主體工程。伴隨洞窟及大像的營造,同步在壁面雕刻佛龕。[9]除第17 窟風化、第20 窟坍塌不明外,窟頂平面均略呈橢圓形,邊緣布置三角形垂飾,表明窟頂為主尊的天蓋。
第16-20 窟位于西部崖面的東部。其中第18窟、第19 窟主窟及東脅窟、第20 窟一次性完成,而第16、17、19窟西脅窟開窟后主體工程的施工曾一度中斷。五窟中洞窟整體沒有對應的供養人圖像,但周壁與開窟工程同步施工的小龕卻常見帶有供養人的情況。第20 窟周壁大部分坍塌,但北壁左上角主尊背光外側坐佛像下方有單膝跪地禮拜的供養人像。右脅佛頭光正上方的二佛并坐龕旁有一世俗供養人像(圖1-1),從銘文可知這些小龕具有單獨的出資人。第19 窟周壁大部分被千佛小龕填滿,但其中部分帶有供養人像,姿態與第20 窟相同(圖2)。第18 窟上層的大型佛龕基本上帶有供養人圖像(圖3)。第17、16 窟周壁與開窟工程同步的佛龕大部分帶有供養人(圖4、5)。第16 窟周壁大龕中,東壁大龕的供養人像在后期被削掉雕刻成千佛小龕,目前尚可看到足部,西壁對應大龕下部同樣是追刻的千佛小龕,有可能原始也雕刻有供養人像,南壁明窗與門口之間的中央龕由于崩落下方是否帶有供養人像不明。這些龕的供養人圖像一般人數較少,不超過20 人,且多為男女分列,可能均為個人造像,個人性質較強。大部分僅表現形象不帶銘文,甚至不設銘區,與龍門石窟古陽洞等在千佛龕旁僅題刻人名的做法差距很大。

圖3 第18窟東西北壁(紅框為帶獨立供養人龕,YunKang V.12 Fig.53加筆)

圖4 第17窟東西南壁(紅框為帶獨立供養人龕,YunKang V.12 Fig.43-45加筆)

圖5 第16窟東西南壁(紅框為帶獨立供養人龕、虛線為推測,YunKang V.11 Fig.43加筆)
第5、13窟分別位于中部崖面的兩端。與腰壁完全不表現供養人圖像的第16-20 窟不同,第5、13 窟的腰壁出現了供養人圖像。第13 窟西壁風化嚴重,東壁保存較好,可以看出以蓮瓣紋帶為界,上部分五層排列小龕群,各龕基本均帶有獨立的供養人像,龕下大部分都設有單獨的銘區(圖6-1)。其中上數第三層的三龕下出現了人數眾多的供養人圖像,中央銘區的左右兩側共35 位男性胡服供養人,由4 位僧侶先導,是典型的由男性組成的造像集團(圖6-2)。洞窟下部為供養天人像及尺寸較大的身著胡服的男性供養人列像。天人像均朝向主尊,但供養人朝向窟門。從朝向來看,供養人像應為門口上方7尊大型立佛的出資人,從人數和性別可知亦為一個男性造像集團(圖6-3、6-4)。

圖6 第13窟(紅框為帶獨立供養人龕)
第5 窟周壁由蓮瓣紋帶大致劃分為6 層,其間滿布小龕。設計、制作的完整性均不及B 類洞窟,但除晚期追刻的小龕外,大部分龕未單獨表現供養人圖像。壁面規律布局的小龕表明出資人為一個集團的可能性。并且規律布局的小龕群侵蝕了主尊脅佛的背光,表明周壁佛龕與洞窟主體是兩個不同的工程(圖7-1)。窟內下層風化嚴重,西壁最下層從南直至脅佛的南側殘留著不能明確辨認是供養人或是供養天的立像痕跡(圖7-2、7-5)。此外,主尊背后的隧道內出現了供養人形象。隧道內西側風化,東側保存較好,北壁及東壁可見中國式著衣的供養人列像,合掌朝向左側,上方為同樣朝向的飛天(圖7-3、7-4、7-5),參考同樣設置隧道的第9、10 窟,隧道西部的供養人列很可能朝向右側。①(日)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雲岡石窟》卷2、Pl.58A,應為隧道東壁的供養人像。這些供養人很可能與周壁小龕群的營造相關。

圖7 第5窟
7 座大像窟均以洞窟的開鑿、巨像的營造為主體工程,同時又在周壁營造了具有獨立出資人的小型佛龕。從周壁小龕的排列及供養人的位置來看,第18-20 窟周壁小龕排列不規律,尚具有涼州早期石窟如炳靈寺第169 窟利用天然洞窟進行造像的特征。第13、16、17 窟周壁小龕的布局較為規律,小龕一般附有獨立的供養人圖像,并且第5、13 窟開始在洞窟的下部空間布置供養人圖像。第5 窟小龕分布較為規律但各龕單獨不設供養人圖像,供養人統一雕刻于洞窟的下部空間。此外,西部五窟中的佛龕個人性質較強,第5、13 窟開始出現集團造像。
(二)B類洞窟
洞窟統一營造,整體有對應的供養人圖像,具體為第1、2 窟及第6-10 窟,均為佛殿窟或中心柱窟。洞窟統一設計,多為對應的雙窟,一次性完成施工,單獨小龕無對應的供養人圖像。供養人統一布置于洞窟下部空間,且數量眾多。窟內題材豐富,供養人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第12窟目前腰壁完全被泥覆蓋,暫不做探討。
第7、8 窟為一組雙窟,兩座佛殿窟東西并列,外壁之間設碑,以文字的形式宣揚開窟造像的功德。二窟均有前后二室,前室設通道將二窟相連。下部空間風化較為嚴重,第8窟前室東西南壁下層可看到分兩層排列的身著胡服的供養人像,第7窟主室內西壁腰壁可見較大型的供養人列像,所有供養人均朝向北壁主尊(圖8)。

圖8 第7、8窟
第9、10窟亦為一組雙窟,均為前后二室,前室設通道相連,主尊后設隧道。前室下部嚴重風化,腰壁的本生、因緣故事圖條帶下方可見供養人的痕跡,但細節不可辨認。第9 窟主室內腰壁殘留的形象尚可清晰辨識出頭光,可見并非供養人圖像。主尊大像后的隧道內北壁至兩側壁排列著身著胡服的供養人列像,中央三人,左側為男性、右側為女性,分別由僧侶先導,由兩側繞向主尊方向。供養人上部的飛天列亦朝向同樣方向(圖9)。

圖9 第9、10窟
第6 窟平面接近正方形,中心設方柱,腰壁之上的周壁及中心柱均分為兩層,上層為立佛,下層為佛傳龕,北壁僅開一大龕。東西南三壁腰壁可辨認出供養人的痕跡,其中東壁保存最好。東壁腰壁上層為佛傳故事條帶,下層為排列于廊下的供養人列像。可辨認回廊每間容納四人,大部分為高髻的女性形象,發髻向上幾乎靠近闌額,手持長徑蓮花,花莖從右肩處向斜后方伸出。東壁靠南壁第一間末尾一人不見發髻,可能為僧侶形象(圖10)。北壁大龕下部完全風化,但龕下緣高度低于周壁布置供養人圖像的位置,所以布置同樣形態供養人圖像的可能性較低。

圖10 第6窟
第1、2 窟為二座并列的中心柱窟,窟內布局近似,周壁僅布置一層佛龕。兩側壁分別開四大龕,南壁二大龕,北壁為一大型楣拱龕。東西南壁佛龕之下以忍冬紋為分割線,布置故事圖條帶及供養人列像。風化嚴重,僅第1 窟東壁北端可辨6 位身著漢服的男性供養人形象,南向排列。供養人的痕跡向南一直延續至南起第2龕北側,更南部殘留晚期追刻龕的痕跡,供養人列可能被追刻龕打破。西壁完全風化,朝向不明。第一窟北壁大龕下方尚存朝向中央胡跪的供養天列像(圖11)。
B 類洞窟供養人均雕刻于洞窟下部空間。第7、8 窟與第9、10 窟的供養人均朝向主室北壁主尊。雖然第9、10窟出現隧道,但供養人并未表現繞像禮拜,從功能上看,隧道進一步增加了雕刻供養人的空間。第1、2 窟與第6 窟為中心柱窟,供養人圖像保存較差,但第1窟北壁尚存以北壁主尊為中心布局的供養天像,第6 窟北壁亦未出現與周壁相同的供養人圖像,并且云岡石窟基本沒有表現為右繞的供養人圖像,所以周壁的供養人很可能是從兩側繞向中心塔柱的正面。從另一個方面顯示出與北壁主尊相比,中心柱窟的禮拜中心為塔柱。從位置來看,一般會將男性布置于左側,則東壁(左壁)為女性供養人圖像的第6窟很可能是由女性主導的集團出資營造。
三、云岡石窟大型洞窟的營造背景
(一)A類洞窟
A 類洞窟為第5、13、16-20窟。《魏書·釋老志》載“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于一世”,[10](P3037)繼太武帝滅佛,文成帝即位佛教復興,新上任的沙門統曇曜于和平年初(460 年)在武州塞斬山開窟,營造了五尊大佛。常盤大定與關野貞首先將第16-20 窟比定為曇曜五窟。[11](P2-7)塚本善隆進一步提出五窟是為道武帝至文成帝在內的五帝而造。目前除對五窟具體對應的帝王尚有爭議外,已基本成為學界的共識。
曇曜發愿營造五窟為見諸史料的記載,而五窟分別對應五帝則是基于文成帝“興光元年(454年)秋,敕有司于五級大寺內,為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立像五,各長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萬斤”[10](P3037-3038)的推論。值得注意的是,帝王鑄造釋迦立像的傳統,在獻文帝時期仍在延續。根據《魏書·釋老志》,皇興元年(467 年)“其歲,高祖誕載。于時起永寧寺,構七級佛圖,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為天下第一。又于天宮寺,造釋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10](P3037-3038)中部的兩座大像窟在設計上與曇曜五窟一脈相承,如窟頂略呈橢圓形,周邊雕刻出三角形垂飾。大像依舊占據窟內主要空間,周壁為開放的造龕像空間等,均顯示出設計上的一貫性,二窟是對曇曜五窟的延續,應是由帝王出資的帝王窟,數量上正對應遷都前的二帝,即獻文帝及孝文帝。從選址來看,西部第20窟以西巖層脆弱,第13窟選擇了中部丘陵的西部,更接近曇曜五窟。而第5窟主尊著衣為漢式,反映出明顯的時間差。則第13 窟應是獻文帝的帝王窟,第5 窟為孝文帝的帝王窟。先行研究往往將帝王的行幸與工程的結束相關聯,但與佛像的開眼供養相比,帝王參與奠基儀式的記載更為常見,如《魏書·高祖紀上》載孝文帝于太和三年(479 年)八月“幸方山,起思遠佛寺”,[10](P147)或據《魏書·釋老志》營造洛陽永寧寺時“靈太后親率百僚,表基立剎”。[10](P3043)《魏書》中獻文帝唯一一次行幸云岡石窟是皇興元年,[10](P128)即位僅2年,并于同年鑄造釋迦立像,其行幸云岡很有可能與新帝王窟(第13窟)的“奠基”有關。作為孝文帝的帝王窟第5窟漢式主尊的選擇也與孝文帝漢化政策一脈相承。曇曜為第16-20 窟的發起人,文成帝為最初的出資人。值得注意的是五窟中的東二窟并未在文成帝時期完成,皇帝的變更自然會導致出資人的變更。岡村秀典指出第13、17 窟主尊背光結構相同,[5](P81)而第5、16窟主尊著衣均為漢式,則第17窟與第16窟的繼續施工很可能分別與獻文帝及孝文帝有關,而獻文帝的“暴崩”,導致第17窟并未最終完成。
A類洞窟為皇家工程,均無附屬于主體工程的供養人圖像。太和五年(481年)“二圣”在定州造塔“以官財雇工”,[12]《周書》載“時靈太后臨朝,減食祿官十分之一,造永寧佛寺”,[13](P658)則皇家工程并不會出現數量眾多的出資人。此外,基于往往會提及的道人統法果之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我非拜天子,乃是禮佛耳”,[10](P3031)在北魏皇帝即如來的思想下,帝王窟的出資人亦是洞窟內禮拜的對象,基于這一矛盾,亦不會將帝王形象作為供養人表現。
(二)B類洞窟
B類洞窟為東部的第1、2窟及中部的第6-10窟,均屬于云岡二期。表現出眾多的供養人形象,則這些洞窟并非由帝王出資,而是集資營造。佐藤智水通過對北朝造像銘的系統研究指出北朝造像中為親人或亡者造像的數量最多,而其中集團造像更多的反映出皇帝崇拜、鎮護國家的思想,[14]可見這些集資洞窟具有較強的政治性。
B 類洞窟中最早營造的是第7、8 窟為學界的共識,近年彭明浩觀察到第7、8 窟窟前平臺左右分別被第6、9、10 窟的斬山范圍打破,進一步明確第7、8窟的營造早于第6、9、10 窟。[15](P144)此外,云岡石窟的大型洞窟中僅第13 窟與第7、8 窟在交腳菩薩像的腳下雕刻出蓮花,可以看出三窟的關系較為密切。第13 窟很可能是皇興元年(467 年)開始營造的獻文帝的帝王窟,則第7、8 窟這一政治性較強的集資洞窟很可能營造于這一時間之后。延興元年(471 年)獻文帝讓位孝文帝,而自己作為太上皇依然參與朝政,作為形式特殊的雙窟,很可能正是在這一背景之下創出。
曇曜五窟的早期尖拱龕拱端使用了無腳龍形,第7、8窟僅使用有腳龍形,晚于其的第9、10、6窟除有腳龍形外出現了鳳鳥形和無角獸形。拱端的無角獸形又見于太和七年、十三年等小龕,太和五年開始營造的永固陵使用了鳳鳥形。此外,岡村秀典又根據唐草紋的發展變化提出第9、10窟的營造緊接著永固陵。[5](P1-52)所以除第7、8窟外的各窟很可能均營造于太和年間。據《魏書》等史料記載,孝文帝于太和四年(480年)八月首次行幸武州山石窟寺,其后太和六年(482年)三月、七年(483年)五月、八年(484年)七月連續行幸。太和七年八月邑義信士信女等54人“為國興福”[8](P3)在第11窟內造龕像,太和八年鉗耳慶時“為國祈福”[3]造石窟,均是在帝王行幸之后動工的政治性造像活動。太和年間各窟營造的開始,很可能集中于孝文帝頻頻行幸云岡石窟的太和四年至太和八年。
(三)時間關系
通過上文的分析,可將云岡石窟主要大型洞窟的營造按照帝位的更迭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文成帝和平年(460-465年)間。營造了皇家洞窟第16-20 窟,其中第16、17 窟未完成,同時個人出資在皇家洞窟中出資營造了部分小龕。
第二階段:獻文帝行幸云岡石窟的皇興元年(467 年)至獻文帝崩時(476 年)。營造皇家洞窟第13 窟,開啟對中部崖面的利用,并重啟第17 窟的營造。眾人集資開鑿第7、8窟,個人及團體在皇家洞窟中營造小龕。
第三階段:孝文帝首次行幸云岡的太和四年(480年)至太和十八年(494年)遷都洛陽。營造了皇家洞窟第5 窟,重啟第16 窟的營造,眾人集資營造了第1、2、6、9、10 窟,個人及集團在皇家洞窟中繼續開龕造像。
云岡石窟的營造始于皇家洞窟,而集資型大型洞窟突然出現于第二階段。這種大型集洞窟的營造需要足夠的工匠。北魏初從各地將工匠遷移至首都平城附近,這些工匠具有獨立編戶,職業世襲,被國家直接控制。[16](P50-52)所以在第一階段可集中工力營造巨型皇家洞窟,個人營造的不過是一些附屬于石窟的小龕。而延興二年(472 年)“詔工商雜伎,盡聽赴農”,[10](P137)對工匠的管控開始放松,太和五年“二圣”在定州造塔已是“雇工”。在這一背景之下,更多自由的工匠可被雇傭進行大型洞窟的營造。此外,從供養人圖像的布局來看,第一階段皇家洞窟中個人出資營造小龕的供養人并不能直觀出現在觀者的視線中,而從第二階段開始,以第7、8窟為首的大型集資洞窟的供養人均位于洞窟下部明顯的位置,是對個人參與開窟造像行為的彰顯。供養人圖像布局的這種外向性格反應出集資開窟造像事業在此時是充分獲得國家肯定的行為。第二階段發生的工匠解放及國家的鼓勵,直接導致第三階段集資洞窟的大量出現。
結語
佛教東漸,在北魏太武帝時期遭受重大打擊。文成帝復法之后,沙門統曇曜佛教復興的政策之一即是營造巨大石窟及象征帝王的巨大佛像。曇曜的事業得到帝王的直接贊助,這就決定了云岡石窟的特殊地位,除具有一般寺院的修行、祈福等功能之外,帶有較強的政治性。帝王的行幸引發開窟造像的熱潮,眾人集資在帝王窟附近營造了大型石窟。
云岡石窟的營造始于皇家洞窟,以國家的鼓勵及延興二年發生的工匠解放為背景,大型集資洞窟出現。皇家石窟為帝王窟,其設計帶有連貫性,均以等同帝王的巨像為營造的主要目的。帝王窟之外的洞窟則更為自由,更多的體現出宗教上的功能性。可進入修行、禮拜的佛殿窟及中心柱窟的營造,擴展了石窟作為寺院的功能。遷都之后,由于政治中心的轉移,營造的多為個人或小家庭祈愿的中小型窟龕。在銘文較少的情況下,供養人圖像是理解石窟營造背景的重要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