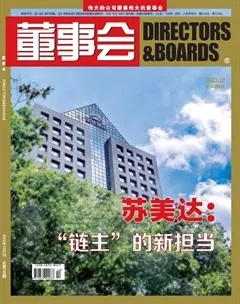科技成果低轉化率之謎
許惠文
科技成果轉化率低這一問題的本質是什么?卡在轉化環節的諸多問題的根源是什么?從企業視角看,至少存在九大問題。打通其間的諸多難點,則是一個系統工程
中國工程院院士、重慶大學教授潘復生,在2023智博會騰訊先進制造高峰論壇上指出: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最高只有30%,只有發達國家的一半,高校的科研成果產業化只有10%。稍早前,廣西審計廳披露某高校獲得科研經費1.79億元,實施科研項目702個,僅有5個項目成果實現市場轉化。
實際上,國內高校等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一直不高,不同企業的科研投入和科技成果轉化率也參差不齊。企業需要科技成果助力核心競爭力提升,而高校等科研機構也希望科研成果能產生社會經濟效益,以提升自身的收益與影響力,看起來一拍即合的雙方,即便在各地政府科技成果轉化相關機構的推動下,多年來仍無法解決科技成果與轉化應用之間“兩張皮”或者說“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科技成果轉化率為什么低,原因究竟在哪?沒有把科研成果到產業界轉化的鏈條打通。從企業視角看,至少存在九大問題。
企業自身研發與科技成果轉化:
不敢投、不會投,不真用,不會用
學者吳壽仁在《創新知識基礎》一書中提出科技成果轉化的“魔川—死谷—達爾文海”理論模型,以描述科技成果轉化所經歷的困難:技術創新成果從走出實驗室,到技術熟化、產品落地,中間往往要經歷從研究到開發的“魔川”、從小試到中試的“死谷”、從中試到產業化的“達爾文海”等一系列攻堅克難的過程(見圖1)。
其中的“達爾文海”,意指在從基礎研究、發明到應用研究的創新和新的商業模式之中,存在巨大的死亡風險的鴻溝(見圖2)。
商場如戰場,企業家形容創業和發展如同“九死一生”,技術研究成果從研究人員的概念提出到成功的商業化何嘗不也是“九死一生”?目前看,企業在自身研發與科技成果轉化投入上存在“不敢投、不會投,不真用,不會用”三大問題。
問題1:企業自身研發“不敢投、不會投”
雖經近20年的發展,知識產權保護仍然面臨著諸多問題。“山寨技術”依舊大行其道,很多中小企業不敢研發投入,也不敢進行技術成果引進。
企業經常談的創新,實際上分三個層面:理論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很多企業熱衷于直接關聯經營成果的產品外觀、銷售模式等創新,少部分企業喜歡做管理者比較熟悉的管理制度創新,至于投入更高、風險更大的技術創新,很多企業因為不具有技術研發經驗,敢于嘗試者寥寥。所以,不敢投入、不知道如何投入在企業界是一種普遍現象,大多數中小民營企業沒有錢投入真正的科研。
校企合作看上去很多,但是大多數高校與科研院所實驗室沒有太多的縱向經費,更多采用跟公司合作、做橫向課題的方式。這樣一來科技成果轉化率看似很高,但一般屬于純應用領域,理論上的創新價值不高。這樣的項目難以吸引高校等科研機構中真正優秀的科研人員的合作,也難以給企業帶來更大的科技成果轉化的收益。
企業和院校聯合從事真正的科研離不開大的投入。比如華為研究中心和外部研究機構進行某云相關的研究項目合作,每年僅支付幾十位研究人員的工資就高達2000多萬人民幣。整個項目預估要做4~5年,最終可能的可轉化的成果籠統來說類似于開發一個全新的算法,讓華為云快幾秒。為此華為就要多花上億元,如此量級的投入顯然讓眾多企業望而卻步。
民營企業中目光短淺的做不大,能做大的絕不會忽略科研這一塊,有些民營企業家也具有較好的戰略眼光。比如廣東某公司老板擁有兩家工廠,全公司加一起人數不到200人,但兩家工廠都跟大學合作,以專門的課題小組做產品研發,收效不錯。
問題2:企業對技術成果引進和轉化“不真用”
引入技術成果究竟為了啥?有些民營企業只是為了宣傳,為了混“高新”等各種認證,為了“拿”各種政府補貼,為了給領導評職稱用,或者為避稅所用,引入的技術專利沒有實際應用價值,企業賬面上研發經費投入的實際水分極大。甚至長久以來存在著一條“產業鏈”,一些行走在政府、事業單位和企業間的掮客,專門“幫助”企業騙取政府補貼。
有些國有企業看起來也投入了大量的研發經費,但科研并不是真正為了出成果。在某些國企的經營目標中,行政管理比商業管理更受重視,導致有的國企創新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戴帽子”、做政績,而不是真正為企業發展投入資金自研或者引入科技成果,這些科技成果轉化的效果當然也就不盡如人意。
問題3:企業對技術成果引進和轉化“不會用”
一般而言,企業內部的部門機構設置更多圍繞市場端、消費端進行建設,從企業家本人到企業研發管理人員往往沒有足夠的時間和資源投入對業內最新科研成果的關注上。大多數企業還是在競爭中向標桿企業學習,看競爭對手用了什么技術、開發了什么產品,自身對原創技術和技術引進的重視度和投入不足。即便有些規上企業進行了一些技術投入,也不能很好地識別出哪些技術成果可以為企業所用,要么高價購買了無用落后的技術,要么不會對買來的技術做二次開發和使用,例如單純地購買專利技術而未能與技術的開發者進行深度合作。
當企業邁過了對自身研發敢投入、會投入的“青春歲月”,隨著企業在競爭中逐步進步,要想成為國內領先、行業領先、世界領先,企業就要匯聚高校等科研機構更多的知識、能力源,就會從最初的購買技術專利階段,逐步走向自研與購買引進相結合,和科研機構聯合研發,在異地設立企業技術能力中心(研究院)的新階段。
企業看外部科研成果:
“不了解、不信任、不匹配”
除了上述問題,企業看高校等科研機構的成果,還存在著“不了解、不信任、不匹配”三大問題。
問題4:企業對科技成果的產生時間、類別和可能收益不了解
數據顯示,大量低價值科技成果嚴重拉低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項目的平均合同金額(見表1)。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數量少,但質量比高校高;從科研院所平均轉化項目數小于2項可知(見表2),許多科研院所還沒實現科技成果轉化項目零的突破。2022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突破3萬億元,然而大量的科研項目躺在科研機構沒有發揮應有的價值,這是巨大的浪費。
企業對科技成果產生的時間和類別關注并不密切,在高校等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轉化數量和金額都有限的情況下,數量巨大的企業,研發主要依賴自身力量,沒有很好地利用高校等科研機構的研究成果。這里深層次的原因還包括:企業本身對研發投入少、很少主動引導高校等科研機構的技術研發方向,以及高校等科研院所不了解、不愿意了解企業的需求,產出的成果立足于學校評價體系和需要等。
問題5:企業對某些科技成果的質量不信任
高校等科研機構的科技成果質量為何讓企業存疑?
某些高校等科研機構的科研成果產出質量管理確實存在問題。比如較為普遍存在的“重立項,輕研究”問題,職務晉升靠的是課題立項,拼的是如何拿到經費、出論文,而不是看科研成果轉換效果。每年高校、省市獲批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很多,但某些學者宣傳的“帽子”往往是其獲得多少國家資助,而不是取得什么實際科研和轉化成果。
甚至有的科研院所存在“自產自銷”的體內循環式的潛規則操作。比如為了評職稱,做自身都知道無有效成果產出、更不可能有科技成果轉化的選題。申請到科研經費后,拼湊出論文、著作、專利等科研成果通過審核,然后找關聯的公司簽訂專利轉化合同,再返還專利購買費用,科技成果轉化成了“如轉”(好像轉化了,實際上沒有任何轉化)。其結果是,相關研究者賺取獎金和名譽,所在機構賺取“成果”,被轉移成果的公司還能申請稅收減免和創新補貼,皆大歡喜的背后,虧了國家和納稅人的利益。
為了獲得相關經費,獲得個人、學校機構等評定成果指標,某些高校等科研機構還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現象。很多科研成果產出需要經歷很長的投入產出周期,或者很多科研干脆就沒有成果,而只有經驗教訓,但是為了平衡各研究院系、科室的“利益關系”,在不科學的“科研評價”體系的引導下,高校等科研機構走向了凡是研究都要求有成果產出、成果轉化這條異化的“歧路”,導致科研研發投入多而散,不考慮學科特點和產出特點,最終的科研成果數量多而質量不高,甚至產出許多永遠走不出實驗室和紙面論文的“偽劣成果”,這當然無法為講究實效和產出的企業所認可。
問題6:很多有價值的科研成果短期內無法轉化為“新生產力”
籠統地說科研人員的成果轉化率低也許并不合適。科研人員粗略可按文科、工科和理科分類,理科、工科等不同細分學科也要在科技成果轉化率評價指標方面設置不同的權重。比如,基礎理論研究本身產出成果慢,不是瞄準短期內產生科研成果而設的,但一旦產出成果則影響巨大。
2004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學者Wilczek在他關于電子分裂的文章中寫道:“正如少部分敢于冒險的創業者可以獲得巨大的成功,也只有少數瘋狂的智力冒險最終會發展成突破性技術。無論哪種情況,成功都是罕見的,失敗才是大多數。盡管如此,基礎研究可能帶來的巨額的回報仍然使得對它大量的投資物有所值。”
當然,一般企業無法承受這樣長期的投入,即便有的企業“財大氣粗”、具有良好研發投入慣例和體系,也無法全額支持這樣的基礎研究。所以,談科技成果轉化首先要將成果作區分,一般分為科學和技術兩大類,我們所談的成果轉化主要是指技術成果轉化。
現在的問題主要是,應用創新類的項目不能有效轉化。甚至還存在一類“耍賴”的“應用基礎研究”,既不夠基礎和理論,也不夠有用和現實,浪費了國家的科研經費。例如,有的大企業和學校等科研機構合作,但有的科研院所的合作動機是為“撈名”,企業出資出力后發現,專利下來后,企業因排名在后導致科研成果無法有效應用。很多小企業非常樂意合作,但很多科研院所又看不上,不大愿意安排高水平的學者投入聯合研究。所以,對不同類型、不同規模的企業而言,談科技成果轉化,也要分層、分類、分企業發展階段來進行資源投入與資源合作。
企業和高校等科研機構之間:
彼此定位不同,相互“霧里看花”
從研究到成果轉化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實驗室創新階段、技術的商品化階段、技術的產業化階段。企業不知道科研院所的創新方向,科研院所不知道企業的需求,成為制約科研成果轉讓整個過程的“兩張皮”難題。問題核心出在兩大流動上: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如何向企業流動,企業的需求如何向科研院所流動。
問題7:科研院所定位導致科研成果和需求之間存在巨大鴻溝
大部分高校等科研機構的定位是人才培養、基礎研究、知識創造,科研應用本身就不排前面。這種定位下的各種研究,從一開始就不是瞄準科技成果轉化而來的,如何實現成果轉化?
科技成果轉化是有高回報,但也存在高風險。科研人員是理性的,追求的是期望值即收益×實現概率,因此需要被合理激勵。理性的科研人員比較之后發現,現有科研評價體系下,寫論文收益更高,類似實現企業中“打糧食”的績效指標——成果可見,容易突破,收益相對可控;而科技成果轉化類似企業中“土壤肥力”的績效指標,長期才可能顯現出成果。實際上,如果沒有科學合理的評價機制,即便在企業中,“土壤肥力”指標也往往不受待見。
越頂尖的高校越重視基礎理論研究。一流高校等科研機構本身就應該注重理論研究,沒有理論上的突破,學科的后續發展無從談起。普通高校或者頂尖高校的應用學科,定位還是要多往企業需求端走,多支持科研成果的應用創新。要做到這些,關鍵取決于高校等科研機構的評價體系要科學,不同學校、不同學科有著不一樣的科技成果轉化的要求和定位,這就要求分層、分級、分類施策,不搞一刀切。
真正的科研大概率是失敗,出成果是個小概率事件。同時,錢沒用在該用的地方固然有負面影響,但不是決定因素。所以,所謂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問題,要理性看待。
問題8:企業獨立研發所需全部技術幾乎不可能
企業瞄準的是商業價值創造和商業變現能力,投入研發也主要是應用研發,靠近客戶端的產品研發,越靠近基礎研究端投入越少。
所謂領先一步成先烈,領先半步真領先。由于投入技術研發風險高,絕大多數企業更依賴于模仿,購買小額的、成熟的技術,或通過挖走相關企業的核心人員以低成本獲得技術。即便是科技型行業、有理想抱負的企業家,所需要的科研成果也很難直接來自高校等科研機構,因為轉化時間可能過長。這些企業往往需要通過金融資本市場解決融資問題,進而開展大規模的國內外技術引進或者自建研發團隊;這些企業一般位居行業頭部,屬于獨角獸類型,已然實現了“以我為主”的技術投入和研發成果轉化。
不妨打個比方,人類的知識體系可以看作一個“餅”,科研人員是把這個“餅”往外擴大,但絕大多數情況下會出現下列幾種情況:
1.這個研究并沒有實際價值,或者說基于人類目前的認知,沒有用,但也許未來有用。
2.實驗失敗,做不下去了,始終無法得到預期效果,但好處是,可以發論文告訴大家這條路走不通。
3.通過大量的試錯和調整,實驗獲得成功,并轉化成商業成果,但這個過程需要大量資金、時間還有運氣。
所以,讓絕大多數商業公司直接做科研很難,試錯成本太高,但是商業公司會在自己的領域去做嘗試。科研出成果本來就是一件小概率的事情,需要有關方面做大量“無用之用”的投入。
問題9:企業和高校等科研機構彼此存在的“溫差”尚待消除
為了消除企業和高校等科研機構彼此之間存在的“溫差”,促進其有效對接,打通“從有科研成果到科技成果轉化成功”這條路,至少有三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一,要真實的成果,有價值的成果。可以是“無用之用”,也可以是“有用之用”,但不能是“偽成果”。要區分科學成果和技術成果,有些研究可以市場為導向,追求科技成果轉化率,有些則不能。對待科研工作不能走兩個極端——唯文章論或者唯成果論,比如唯成果論導致科研只能出成果,為了出成果而做各種“排列組合”,生產出科研工作者自己都認為不能轉化應用的“成果”。
第二,確定是否需要轉化,客觀上能否轉化。國家目前的政策導向鼓勵高校等科研機構研究,而不唯成果和轉化;對科研工作的評價,除了看成果也可以看失敗總結,失敗總結也是成果,真正的科研就是需要在無限方向進行無數試錯。基礎學科一旦厚積薄發,就具有劃時代意義,國內仍然缺乏這方面的立項。
第三,在前兩個問題化解的基礎上,再考慮如何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包括對轉化成什么、如何衡量轉化后的結果進行考慮。比如基礎研究容忍失敗,轉化成經驗總結也是很好的“成果”。像華為在與大學合作時并不要求一定要有可以應用的成果產出,如果研究失敗了,只需要告知為什么失敗即可,以便華為總結經驗,調整研究投入的方向。對企業和高校之間的關系,任正非的主張是:企業與高校的合作要松耦合,不能強耦合。高校的目的是為理想而奮斗,為好奇而奮斗;企業是現實主義的,有商業“銅臭”的。強耦合互相制約,影響各自的進步……必須解耦,以松散的方式合作。
在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征程中,如何打通高校等科研機構和企業在科技成果轉化上的“最后一公里”?
最根本的還是要靠需求方即企業方,企業知道需求,是市場導向的功利性組織,是直接受益的最大一方,理所應當主動打通技術轉化的堵點與卡點。從改進動作來說,企業也是最有動力、行動最迅速的一方。其中,企業家本人要成為擁有技術洞察力的引領者,企業內部要有具備技術專業、經驗和商業能力的內外部研發管理者,企業還要建立起內部研發與外部技術成果轉化的高效互動機制。
而從更大視角看,打通“最后一公里”的諸多難點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頂層擘畫,統籌施策。
作者系中天鈞策咨詢公司創始合伙人、博士、專家咨詢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