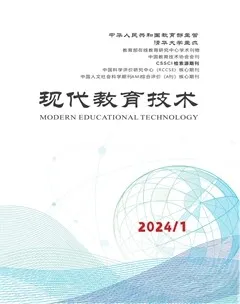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研究*
劉 妍 李夢興 舒 杭
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研究*
劉 妍1李夢興1舒 杭2[通訊作者]
(1.上海交通大學 教育學院,上海 200240;2.江南大學 “互聯網+教育”研究基地,江蘇無錫 214122)
數字技術的強勢推動,對教師的教學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即教師應具備數字化教學能力。在此背景下,厘清數字化教學能力的內涵并對教師的數字化教學能力進行診斷,成為破除技術應用淺、轉化效果弱等現實困境的關鍵。基于此,文章采用問卷調查和訪談的方法,對教師的數字化教學應用現狀和教師在開展數字技術融合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了分析,并對這些問題出現的主要原因進行了探討。在此基礎上,本研究依托場景交互理論和能力遷移假設,設計了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模型。此模型以技術儲備為“原點”,是一個包含數字化教學、技術應用、教師專業發展的三維模型。在此模型的指導下,本研究提出了包含實驗實施、數據挖掘、診斷分析、案例萃取四個環節的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實施路徑,以期為教師數字化能力診斷提供模型參考,并助力教師數字素養提升,實現高質量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數字化教學能力;交互場景;數字素養;能力診斷
引言
2022年2月,《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點》明確提出“實施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1];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把“推進教育數字化”作為重要戰略部署[2]。而“強國必先強教,強教必先強師”,教師是教育高質量發展的第一資源,新時代基礎教育教師是數字化戰略得以落地的關鍵動力[3]。同年11月,教育部發布《教師數字素養》行業標準[4],明確了教師數字素養指標。2023年2月,世界數字教育大會首次提出“提升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5],實現人機協同教學,更好地創新教育教學模式和測評方式,助推教學質量提升。當前,數字技術已具有互聯互通、即時高效、動態共享的特征,能快速匯聚資源、打破時空限制,支持形成跨時空、跨地域、跨區域的泛在學習形態,并支持呈現多元、立體、虛實結合的學習空間。以數字技術為抓手開展人機協同教學,是未來教育發展的新形態[6],這對教師的教學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元宇宙、數字人、基于AIGC的百“模”大戰,裹挾著一波波新技術、新概念呼嘯而來。智能互聯黑板、虛擬現實技術等多樣態、泛在化的教學與研修應用迭代更新,促進了教學環境的數字化轉型[7]。各類智能應用如雨后春筍般產生,不盡相同的使用邏輯給教師增添了過高的學習成本。在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流程再造中,教師的能力無法自動生成[8]。因此,即使掌握了其中一種技術,但如果教師難以靈活地進行跨平臺應用,就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重新學習。目前,數字技術仍停留在幫助教師組織傳統教學活動的層面,教師仍需在教室內面對多個學生開展教學活動[9],而無法實現“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無邊界教學。2022年,全國各級各類專任教師較上年增加35.98萬人,各級各類學校已基本具備信息化教學環境。但數字化基礎設施的完善與教師在課程教學中對ICT應用的不足形成鮮明對比,多媒體設備的淺層應用讓課堂的生成性空間大打折扣。研究發現,教師在現階段仍存在因缺乏信息素養而導致的課程設計難、學習評價難、課堂監管難等問題[10],更遑論高階的數字能力[11]。面對如此嚴峻的數字化教學應用問題,有效構建滿足教師素養和角色轉變的數字化教學能力體系與長周期、成長型的診斷路徑才是解決之道。
一 研究現狀
1 數字化教學能力內涵延伸
早在1999年,黃俊聯等[12]就提出了“數字化教學”的概念,相關概念還有數字化教學技能、數字教學環境等。隨著數字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在歷經多媒體技術、人工智能、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的發展后,教師能力內涵拓展至更豐富的維度。傳統教師能力包括教學能力、反思能力、溝通能力、終身學習能力等。當整合技術的學科教學知識(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TPACK)被提出后,信息技術整合學科教學能力受到重視,信息技術能力被納入教師能力體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發布的《教師ICT能力框架(第3版)》繼續細化ICT能力框架,將ICT能力分為知識獲取能力、知識深化能力和知識創造能力三類[13]。歐盟發布《提升教師信息甄別能力與數字素養指南》,指出要培養教師批判性地使用數字技術的能力,讓教育工作者具備一定的數字素養[14]。我國教育部發布《教師數字素養》教育行業標準[15],明確了數字時代教師應具備的素養框架,強調要促進數字技術與教育教學的深度融合,以數字化資源共建共享提升教師的數字素養,最終讓數字素養支撐教師的數字化教學,形成數字教育新生態。數字素養不只是知識與技能,更是在特定情境中利用和調動數字資源(包括技術和態度)以滿足復雜需要的能力。教育數字化轉型是借助數字技術,推動教學理念、目標、手段、方法、設施、評價的系統變革。教師作為第一資源,其能力需求已不再是技術工具的簡單應用。數字化教學能力是數字素養的本體構件[16],是指應用數字技術支持教學活動設計、實施與評價等教學核心活動的能力,其內涵延伸涉及以下五個方面:①具備數字化意識、態度和技術技能;②將適切的數字應用與教學深度融合,如將豐富教學環境的技術創新應用于學科教學或跨學科教學設計;③將數據作為驅動教育創新和變革的動力,如運用數據分析結果來診斷教學設計的有效性;④利用交互式教學場景協同教學,體現人人協同和人機協同,探索數字化場景教學,構建教師教學新范式;⑤具備數據安全保護意識和倫理規范。應用數字技術創新教學實踐是一個融通的動態過程,在此過程中可能出現多元的學科知識認知、活動組織、技術應用路徑和數字技術應用場景。診斷數字化教學能力應遵循其延伸內涵和動態特征,通過融入場景、環境、資源、平臺等多種因素,探索有價值的指標以刻畫這一高階能力。
2 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測評研究
傳統教師教學能力基于教學設計、教學實施、教學評價、課程開發、教學創新等維度展開,借助問卷、訪談和課堂觀察形式考察評價[17]。隨著技術在教育教學領域的深度融合,對教師信息化能力、數字能力等的要求逐漸被提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教師ICT能力框架》、美國國際教育技術協會的《面向教師的教育技術標準》、歐盟的《歐盟教育工作者數字勝任力框架》相繼指出,教師需要具備應用數字技術進行教學的能力[18][19][20]。我國教育部也先后提出《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標準(試行)》[21]、《教師數字素養》行業標準[22],要求教師具備技術融合教學的新能力。為測評教師的數字化教學能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實施的教師教學國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TALIS)項目針對技術理解、準備、應用展開了能力測量[23]。在我國,張哲等[24]基于TPACK模型,提出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評價模型,開發了包含基于信息化教學基礎能力、信息化教學整合應用能力、信息化教學情境應用能力三個維度的評價指標;魏非等[25]依據教育部頒布的《中小學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測評指南》,從微能力出發構建了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測評模型,以量表形式客觀地測量了教師應用信息技術進行教學的能力;陳娬等[26]結合相關文件的要求,從理念與態度、知識與技能、應用三維度開發了信息技術融入教學能力測評量表,繪制了信息時代欠發達地區教師的數字教學能力畫像。此外,楊濱[27]以新媒體、新技術為依托,構建了“互聯網+”新媒體環境下教師教學能力指數型趨同發展培養模型(Teaching Ability Exponential Converged Development,TAECD),以教師教學能力趨同發展評價量規對教師教學的細化能力進行量化或質性評測。
綜合上述分析,雖然教學過程的多模態、客觀性數據留痕已經引起關注[28],但現有研究尚未深入探討利用多模態數據進行長周期、跟蹤式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和反饋。未來研究需要重視不同階段教師的專業發展差異、評價內容差異和評價證據的科學性,挖掘教師教學特征,精準定位教師教學的不足,以有針對性地提升教師的數字化教學能力。
3 基于交互場景的測評研究
學習過程是從知識習得走向知識體系建構的過程,教學過程是學習目標實現和師生互動的過程,而課堂場景是創造和增加價值的第一現場。20世紀70年代以前,對教與學的研究大多依賴于專家課堂觀察筆記對課堂教學行為進行分析。隨著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者對數據的認知不斷提升,同時得益于視頻錄制技術的迅猛發展,基于視頻的課堂分析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隨后,課堂話語分析、課堂互動分析、微觀互動民族志等課堂分析方法陸續出現,深刻地影響了教育研究的方法論、技術與范式。隨著智能技術在教育領域應用的深入,Bao[29]提出可以利用多模態傳感設備對個體不同場景匯總的信息進行采集,實現對個體位置、活動、意圖、行為、交互的數據記錄與行為推斷,從而實現對個體特征、群體特征的細致畫像和對教育場景的精準感知。近幾年來,國內多個地方開展了基于課堂的質量評價研究[30],積累了一定的實踐場景經驗和理論研究成果。即使研究開始關注教師的教學能力指標,但作為分析指標的互動場景尚未出現在診斷體系中,更難以借助及時、動態的獲取方式進行個性化分析和反饋。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基于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內涵解讀和場景評價現狀,調研中小學一線教師在數字化教學過程中面臨的現實困境,剖析其根源,試圖構建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模型,以助力教師專業能力的提升。
二 研究設計
為厘清現階段中小學一線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現狀和專業能力發展特征,從而為教師“能力診斷-反饋機制”提供策略支持,本研究通過抽樣調查的形式,針對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及其應用開展了問卷調查與訪談。
1 研究工具
參考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量表[31]、TPACK理論框架[32],結合文件《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標準(試行)》[33],本研究編制了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問卷。問卷設有數字化教學能力、基于場景的智能技術應用兩個一級維度,其中數字化教學能力維度含有數字技術的儲備、教學設計與實施、教學反思3個二級維度,共8道題;基于場景的智能技術應用只含場景應用1個二級維度,共2道題,如表1所示。所有問題均以多選題的形式展開,按頻數與頻率方式計分。

表1 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問卷的維度設計
與此同時,本研究從數字技術應用鴻溝和能力需求兩個維度,設計了兩個開放性訪談問題:①一線教師在開展數字技術融合教育教學的過程中存在哪些問題?②智能技術在應用于教學的過程中要求教師應具備哪些能力?
2 研究對象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以上海市中小學的一線教師為研究對象,從2023年9月至11月,通過隨機抽樣方式進行調查,共發放問卷295份,回收有效問卷264份,有效率達89.5%。問卷題項經過多次調整后,可靠性Cronbach’s α值為0.85,KMO值為0.834,球形檢驗的顯著性無限接近0,說明問卷已具有較好的信效度。問卷數據統計結果顯示,入職時間少于5年的教師占比31%,5~10年教齡的教師占比22%;女性、男性教師的占比分別為54%、46%;教師所教學科涵蓋信息技術、化學、物理、數學、語文、科學、道法等。本研究采用的數據分析工具是“微詞云”在線生成平臺(網址:https://fenci.weiciyun.com/)和SPSS 20.0軟件。
同時,綜合考慮教齡、性別、所教學科等因素,本研究選取10名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市中小學一線教師進行訪談(如語文學科教壇新秀、數學學科帶頭人、科學學科二級教師、信息科技學科高級教師等),共獲得訪談音頻時長200余分鐘,經整理后轉化為訪談文本2萬余字。之后,本研究采用NVIVO 14軟件對訪談文本進行了編碼分析。
三 研究分析
1 數據分析與問題歸因
(1)問卷數據分析
問卷數據分析結果表明,當前教師的數字化教學能力整體偏低,且不同教師之間的差異性顯著,主要表現為:①數字技術儲備方面,59.4%的教師表示需要半年及以上的時間去完成與技術的磨合,有5%的教師表示這種磨合需要2年以上。這說明教師與技術的磨合需要較長的周期,同時從側面說明數字技術與教學的融合需要經歷長周期、滲透式的探索過程,也說明數字技術的飛速發展并未能帶動教師數字素養的提升。②教學設計與實施方面,89.34%的教師會在課堂教學環節使用技術工具,78.69%的教師會在備課環節使用,這說明教師對于技術支持的教學設計與實施具有較高的認可度。但是,課后復習、作業評估、學情診斷環節的占比均不足50%(分別是31.97%、42%、42.62%),這反映出教師的數字化教學能力并未在教學全流程中得到提升。③教學反思方面,有73.2%的教師表示會選擇通過錄音、視頻的回放幫助自己復盤教學過程,而只有不到35%的教師會利用平臺數據和分析工具來理解學習的過程,這說明教師的數字化教學反思能力比較薄弱。④場景應用方面,超過88%的教師表示在教學過程中選擇的是傳統多媒體工具(如投影儀),78.36%的教師表示使用了互動教學工具(如電子白板),而只有36%的教師選擇了智能工具(如平板)和沉浸式工具(如VR、AR)。這說明傳統信息技術與環境仍占主導,而數字技術與場景應用被忽視。也正因如此,才會有近乎半數(44.3%)的教師表示數字技術沒有達成既定的教學目標。
(2)訪談文本分析
通過對教師訪談文本的分析,本研究歸納出教師在開展數字技術融合教學過程中存在的三個主要問題:①外部誘因差異,教師不會用技術。結合對訪談文本中高頻關鍵詞的分析,可知技術、學生、教學資源、時間、規范等是教師不會用技術的主要外部誘因。有教師表示:“經常會遇到學生個體差異、學習習慣、網絡和硬件不穩定、資源不足、班級氛圍和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而影響技術應用。如何讓數字化技術更加匹配教學目標,是融合過程中我遇到的重點問題。”②教學功底不牢,教師不敢用技術。有教師表示:“采用什么技術、如何使用技術,往往因策略和理論方面的短板造成應用鴻溝和壁壘”,且“數字化技術如何賦能傳統教學策略和教學方式,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答”。③教學場景復雜,教師不善用技術。有教師表示:“隨著數字技術應用的場景越來越多,無論是課堂管理還是教學實施效果,都很難通過深度應用數字技術來達成提質增效。”如果教學效果與投入負相關,長此以往便會打擊教師教學的自信心,從而降低深度學習的意愿。
從教師的角度出發,要想充分實現數字技術與教學的深度融合以提升教師的數字化教學水平,就需要教師自身具備一定的能力。對訪談問題②的相關訪談文本進行關鍵詞統計,得到教師數字化教學的能力要求,如表2所示。表2顯示,訪談中被提及最多的關鍵詞是“基本教學技能”,之后從高到低依次是教學設計能力、協同教學能力、數據診斷能力、教學反思能力、教學決策能力(頻次均>100)。毋庸置疑,基本教學技能是教師應當具備的首要能力,也是教師專業發展的基礎。而教學設計、協同教學、數據診斷、教學反思、教學決策都是開展數字化教學實踐對教師的能力要求。正如受訪教師所言:“教育數字化轉型、人工智能教育等發展的大趨勢,要求我們一線教師從培養學生高階能力和綜合素養的角度去設計課堂教學活動”“作為新手教師,我覺得我更加需要提升教學反思能力。與有經驗的老教師相比,我很難抓準課堂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而且面對教學過程中的一些突發情況,有時候會覺得很慌亂無助”“系統中的那些數據,我看不太懂,也不知道怎么將這些數據用到教學之中”“基于教學過程中的實時數據評價,非常考驗教師的決策能力和教學診斷能力”。此外,還有教師表示缺乏教學自主創新的意識和能力,如不能借助數字技術創新教學模式。

表2 教師數字化教學的能力要求
2 問題歸因
根據上述問卷數據分析和訪談文本分析結果可知,目前提升教師專業能力發展并不切實有效,影響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因素也紛繁復雜,其原因主要在于:
①傳統測評難以應對時代訴求。對教師不敢用和不善用的問題進行分析,可以發現傳統教師能力測評難以為教師提供實質性指導。例如,評價指標方面,目前的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框架已不能滿足智能時代對教師角色轉變與素養提升的需求。評價策略沒有考慮教師不同專業發展階段的差別,具體表現為教學育人、技術應用等均是單維測評,而缺乏全面、多發展階段的系統診斷路徑,對教師智能教育素養的內涵研究也相對較少[34]。同時,教學質量因素探究和教師能力評價內容多為研究者的個人自由探索,且教師發展的多階段、多層次可能會造成評價缺乏針對性的問題;相關研究尚未融入動態和長周期數據支撐的數字教學能力畫像依據,能力評價的精準性也難以判斷。此外,還出現了以靜態測評為主和精準診斷滯后的現象。目前評測目的是遴選評價,忽略診斷提升,在實踐中往往存在“測評難”“溯因難”的問題,在教師專業發展個性化指導方面也存在不足。針對上述問題,采用長周期、跨場域、多模態數據的采集與融合技術,能使對教學全過程的行為追蹤與能力發展溯因成為可能[35];而借助人工智能技術的采集和數據分析手段,可以全方位收集過程數據,在保障數據倫理安全的前提下有的放矢,篩選有價值的數據與關鍵指標建立映射關系,進行高價值、長周期、動態的數據分析,提高教師能力測評的精準度。
②數字素養提升不足帶來應用壁壘。盡管教師的數字化意識與基本技能已經初步具備,但其數字化應用、數字化教學能力和數字素養方面的明顯不足(如缺乏技術規范化使用、數字技能與教學的深度融合不夠等),帶來了數據決策不夠科學、教學改進經驗不夠豐富等問題。如何借助智能技術實現“資源找人”?如何滿足學生的個性化需求,實現智慧地教?[36]這些問題也阻礙教師進一步提升數字化教學能力。本研究發現,差異化的智能應用產品與功能體驗導致教師上手難、不能用同一套邏輯體系組織海量的數字資源。教師對數字技術應用的淺認知、低接受、應用刻板和缺乏創新等問題,都是數字素養不足帶來的教育教學應用壁壘。因此,破解教師面臨的教學困難和技術應用鴻溝等難題,提升教師的數字素養,對于提升教學質量至關重要。
③場景數據缺失難以驗證效果。數字化教學實施融入了場景、物理環境、資源、平臺等因素,其數據具有多元復雜性。這一方面對教師的教學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方面當前場景數據的缺失和忽視,導致其應用效果難以被驗證。而采用無感知的情景化測評方式,能夠提升素養測評的精準度[37]。本研究發現,教師素養和能力數據采集大多來源于評課觀察、教學考核的結果數據,對于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指標的診斷與干預還遠遠不夠,容易帶來研訓內容不匹配、教學資源推薦不精準等問題。另外,傳統的問卷、訪談等方法難以獲得客觀、全面的教學數據。借助人工智能技術不僅能解決上述問題,還能實現規模化的診斷效果,并據此提供超越教師經驗定式的智能分析決策服務。同時,應用數據智能技術還能幫助教師理解日常現象背后的教學規律、發現自身教學問題,從而實現精準教學和專業能力提升。
盡管數字技術應用鴻溝客觀存在、面臨的現實困境重重,但通過對訪談文本的情感挖掘,本研究發現教師對數字技術使用依然保持積極、樂觀的心態,并不會因現實困境而降低對課堂教學的熱情。教學的本質是互動過程,而能力診斷是實現教師專業發展的驅動力。為回應“測評難”“溯因難”“不精準”等問題,本研究試圖構建基于交互場景的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模型,并在此基礎上結合長周期、伴隨式的多模態數據分析,提出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實施路徑,以解決場景數據缺失、數字素養不足等問題。由此,實現“動態診視”和“科學判斷”的結合,協助教師發現教學問題和數字化教學能力方面的不足,引導教師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從而有針對性地提升教師的數字化教學能力,促進高質量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四 診斷模型設計與實施
1 診斷模型設計
場景交互理論是場景理論應用于交互設計的指導性理論,將師生交互作為刻畫能力模型的核心[38]。而能力遷移假設關注情境的相似性,通過相似的情境來理解在一種技術教育應用情境中獲得的知識和能力對另一種技術教學應用情境的影響[39]。本研究依托場景交互理論和能力遷移假設,結合上文分析,設計了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模型
如圖1所示,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模型是一個以技術儲備為“原點”構建的三維模型:①從數字化教學維度來看,借鑒數字素養中的數字化教學指標,貫穿教學設計、教學實施、教學評價、教學反思四個環節;②從技術應用維度來看,涵蓋理解技術、解決問題、設計活動、創新應用四個關鍵步驟;③從教師專業發展維度來看,包含新手教師、經驗型教師、成熟型教師、專家型教師四個發展階段。這四個發展階段的劃分來源于教師“職業成熟”階段理論[40],此理論認為教師的專業發展是一個連續的、動態成長與靜態成熟相結合的過程,與之匹配的是教師在數字化環境中與技術的融合程度。
數字化教學、技術應用與教師專業發展共同發力,刻畫出一條三維立體的診斷路徑。在開展數字化教學的過程中,教師可能會在意識、認知、經驗習慣、能力四個方面發生遷移。另外,長周期地采集伴隨式的行為數據、言語數據、定位數據等多模態數據,提供從單一場景到多場景的動態建模、診斷與反饋,生成教師周期型的專業發展報告,也有助于教師專業能力的進階式發展。最終,新手教師將實現從經驗型教師到成熟型教師再到專家型教師的轉變——這是一個逐層遞進的連續發展過程,對不同專業發展階段的教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①經驗型教師需具備教學基本技能,能夠關注知識維度、學生需求和綜合素養提升,在教法、技術基礎應用等方面已積累了豐富經驗;②成熟型教師需能熟練、靈活地應用數字技術,并結合教學目標、教學情境和學生需求,有針對性地運用教學基本技能;③專家型教師需能利用技術創新協同教學,并能結合過程數據診斷教學,根據反饋結果進行調整、實現能力提升。各發展階段的教師專業能力既交叉重疊,也螺旋上升,但專業發展的基準要求存在差異,因此對教師專業能力的評價不能按照統一的標準開展。應用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模型時,需注意不同教師專業發展階段的不同基準要求,宜采用增值評價方法和最優匹配策略,對不同專業發展階段的教師先進行專業定位后再實施診斷反饋。
2 實施路徑
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提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專業發展歷程來看,其涉及職前、職后兩個階段。關注實踐場景的能力表現,不僅有助于快速、有針對性地找到問題癥結,也能突破以往標準化測驗、自評反思方式的限制,形成真正有效的能力診斷路徑。真實教育場景的復雜性使教學能力診斷與高質量課堂特征測評存在難度,故開展場景驅動的評價是能力診斷實施的關鍵。挖掘不同場景下的多源異構數據,實現對完整教育場景的精準刻畫和教學生態的完整表征,才能更客觀地探明教師在動態發展中的優勢與不足,實現高質量的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基于此,本研究綜合考慮教師專業發展的階段性、迭代交叉性和成長動態過程,采用增值評價方法和最優匹配策略,依托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模型,提出包含實驗實施、數據挖掘、診斷分析、案例萃取四個環節的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實施路徑(如圖2所示),以期為教師提供適合自身專業發展和能力提升的反饋策略。

圖2 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實施路徑
環節①:實施多場景下的數字化教學社會實驗。數字化教學社會實驗采用國際通用的社會實驗方法,遵循“控制-對照-比較”的科學研究邏輯,根據教學實際需要,選取典型教育社會實驗進行對比研究。實驗設計需要考慮將對應場景特征分別引入診斷模型,以常態化課堂、智慧教室、虛擬教學環境、在線智慧教育平臺為典型的互動場景,聚焦教學、評價、教研、作業等業務流程設計數字化教學活動并展開研究,實現應用示范。在數字化教學社會實驗的實施過程中,需重點關注教師數字化教學設計、實施和評價的能力。通過對比不同類型教師的能力差異和變化,挖掘互動場景驅動的數字化教學實踐效果數據;同時,需注重發揮數據驅動教與學診斷的優勢,將互動場景、業務功能、智能應用、數據采集進行串聯,以應對當前的數字技術應用鴻溝,解決專業定位教學不夠精準的問題。因此,借助高清攝錄設備、自主學習環境、物聯網、在線學習管理系統、虛擬教學實驗平臺、可穿戴設備等多傳感設備采集不同場景內的數據,方能支持后續能力診斷的開展。
環節②:挖掘不同場景下的多模態數據。在多場景下的數字化教學社會實驗形成的典型應用示范中抓取教師能力提升的相關數據,同時結合多模態人機交互數據來有效還原真實的教學過程,將是能力測評的重要方向。而對學習場景信息的數據化表征,是未來智能教育領域研究的重點。通過對構成教育場景的人、機、物、環境等要素的智能感知與精準測評,從數據感知層面對學習場景進行全方位的測量分析,有利于實現對教育規律的深層次挖掘。在實現業務需求(如智能輔導、沉浸學習等)的過程中,典型數字化教學場景(如常態化課堂、智慧教室等)可能會出現一些具有價值的教育線索,如教學場景信息、教學過程信息、教學行為信息、教學資源信息、教學活動信息等。這些信息與師生的行為、認知、情感等方面狀態和表現密切相關,影響著教與學的過程,其數據化表征成為課堂整體的場景變量。例如,師生互動過程中的言語、非言語數據關涉教與學的進度,人機交互數據反映教與學的行為,環境數據影響教學活動開展的節奏與氛圍,生理數據體現師生的精神與情感狀態等,這些數據均可借助點陣紙筆、電子書包等采集工具進行捕獲。這些數據呈現出分布位置的分散性、形態呈現的多模態等特征,能用于多維度地數字化呈現真實的教學過程,因此挖掘場景內的多模態數據是未來需要攻克的技術難題。從技術實現的角度來說,應考慮如何對這些數據進行識別與整合,并實現其與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科學映射,如用常態化課堂中師生互動的言語行為和非言語行為表征“課堂教學情緒”,用智慧教室中課堂狀態數據表征“課堂教學氛圍”,用虛擬環境中的生理數據表征“行為表現狀態”,用在線平臺內的痕跡數據表征“認知發展過程”等。
環節③:開展場景數據驅動的能力診斷分析。完成多模態數據采集后,需先進行粗數據提取,即運用算法對采集后經預處理的數據進行數據相關屬性提取和模型驗證。例如,采用BRAT、CDVA、Labelme進行圖像語義、文本數據分割數據標注,為溯源過程提供更加豐富的背景信息。之后,開展結構化表征數據分析。一般來說,多模態學習分析涉及算法訓練、特征提取、特征選擇、解釋與反饋五個步驟。具體而言,在識別與揭示隱藏模式時,采用LSTMS、BERT、貝葉斯網絡等算法模型對數據進行識別、分類與預測,并獲得相應的數據特征,以解決數據之間的長期依賴問題。在此基礎上,可以采用基于深度學習的半監督學習算法,對場景特征數據、行為數據、言語數據、教師數據等進行多維度分析,解釋數據和模態之間的隱藏關系。同時,在歸因和關聯分析時,借助聚類、回歸、分類等機器學習方法,挖掘不同類型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關鍵特征與行為偏好,從而為教師提升數字化教學能力提供更有針對性、指導性的依據。
環節④:通過教學迭代萃取典型示范案例。經過上述三個環節,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方案將基本成型,之后可以通過持續迭代、反復驗證、深度反思,不斷優化能力診斷方案,并將其應用于不同場景的教學實踐,形成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提升行動方案,以實現長周期教師能力診斷與跨場景遷移應用。更進一步,可以采取教學迭代萃取方法,挖掘隱藏于實踐行為背后的策略、路徑與機制,進而總結提煉出可復制、可推廣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提升的典型示范案例,以幫助教師將數字技術真正融入教學過程,在生成面向未來教師發展需求的數字化教學應用示范的同時,喚醒其內在驅動力。
五 結語
從信息素養到數字素養、從信息技術整合教學到數字化深度融合、從簡單應用到創新生成,在此轉型過程中強化教師利用數字技術活化和變革教學的意識、能力、責任,是助推教師專業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本研究對上海市中小學一線教學教師進行了問卷調查和開放性訪談,發現現階段中小學一線教師存在技術磨合周期長、技術使用差異化、反思能力較薄弱、場景應用被忽視等問題和不會用、不敢用、不善用技術的心理困擾,出現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傳統測評難以應對時代訴求、數字素養提升不足帶來應用壁壘、場景數據缺失難以驗證效果。結合上述研究分析,本研究依托場景交互理論和能力遷移假設,設計了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能力診斷模型,并以此為指導提出了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實施路徑。為進一步實現基于交互場景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精準診斷,本研究認為需關注互動場景測評視角的教師能力診斷,同時要認識到:教師專業能力提升是一個動態、融通的發展過程,需要客觀的、過程性、伴隨式數據驅動教學能力精準測評。在實施具體的能力診斷時,可結合多種數字場景應用與業務功能構建高價值的數據指標,以精準映射教師不同專業能力發展階段的核心能力。在此基礎上,可利用多場景下的數字化教學社會實驗和多模態數據分析,進行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多維度、跨場域測評,借助長周期的動態數據形成“教中診斷,診斷后迭代”的反饋機制,從而為教師提升數字化教學能力提供更有針對性和持續性的反饋建議。
數字素養與技能作為未來生活、工作的重要能力和素質集合,直接影響教育質量及其效果。探索提升教師數字素養和教學能力的渠道,堅持“為提升而測”的原則,有利于形成教師發展的新機制、新場景和新模式。后續研究將結合數字技術的具體教學應用情境完善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診斷,借助國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務平臺、中國教師研修網等在線教學資源深化教育數字化理念,強化數字技術賦能。同時,后續研究將關注數字技術應用標準、有價值的數據指標,建立滿足教師能力長足發展的診斷指標,支持教師開展數字化創新應用和實踐,并搭建數字化互動分析系統,開展規模化的教學數據治理和常態化反饋,為“如何智慧地教”提供典型示范。
[1]教育部.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點[OL].
[2]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OL].
[3]祝智庭,胡姣.教育數字化轉型:面向未來的教育“轉基因”工程[J].開放教育研究,2022,(5):12-19.
[4][15][22]教育部.教育部關于發布《教師數字素養》教育行業標準的通知[OL].
[5]懷進鵬.數字變革與教育未來——在世界數字教育大會上的主旨演講[OL].
[6]楊宗凱.構建開放共享的全球數字教育生態[OL].
[7]楊曉哲,任友群.教育人工智能的下一步——應用場景與推進策略[J].中國電化教育2021,(1):89-95.
[8]楊俊鋒,秦子涵.學校數字化轉型的方向與重點[N].中國教育報,2023-1-9(9).
[9]袁振國.教育數字化轉型:轉什么,怎么轉[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3,(3):1-11.
[10]張輝蓉,朱予橦,念創,等.重大疫情下中小學網絡教學:機遇、挑戰與應對[J].課程·教材·教法,2023,(5):58-63.
[11]田小紅,季益龍,周躍良.教師能力結構再造: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關鍵支撐[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3,(3):91-100.
[12]黃俊聯,采振祥,徐明.數字化技術在教學改革中的作用[J].電化教育研究,1999,(3):92-94.
[13][18]UNESCO. UNESCO ICT competency framework for teachers[OL].
[14]European Commission. Guidelines for teachers: Tackling disinformation and promoting digital literacy[OL].
[16]閆廣芬,劉麗.教師數字素養及其培育路徑研究——基于歐盟七個教師數字素養框架的比較分析[J].比較教育研究,2022,(3):10-18.
[17]黃友初.教師專業素養:內涵、構成要素與提升路徑[J].教育科學,2019,(3):27-34.
[19]劉志波,許惠芳.面向教師的美國國家教育技術標準(2008版)[J].現代教育技術,2008,(9):128.
[20]European Commission. DigComp 2.1: The digital competence framework for citizens with eight proficiency levelsand examples of use[R]. Luxembourg: Publications Off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7:12-20.
[21][33]教育部.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印發《中小學教師信息技術應用能力標準(試行)》的通知[OL].
[23]OECD. TALIS 2018 results (Volume I) teachers and school leaders as lifelong learners[OL].
[24]張哲,陳曉慧,王以寧.基于TPACK模型的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評價研究[J].現代遠距離教育,2017,(6):66-73.
[25]魏非,宮玲玲,章玉霞,等.基于微能力的教師信息化教學能力測評模型[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2021,(6):94-102.
[26]陳娬,盧曉中.教師能勝任信息時代的教學嗎?——來自欠發達地區的調查[J].開放教育研究,2020,(5):71-77.
[27]楊濱.教師教學能力指數型趨同發展培養模型構建研究——“互聯網+”新媒體環境下教師專業發展研究[J].電化教育研究,2020,(6):105-112.
[28]Starcic A I. Human learning and learning analytic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2019,(6): 2974-2976.
[29]Bao X. Enabling context-awareness in mobile systems via multi-modal sensing[D]. Durham: Duke University, 2013:3-81.
[30]胡航,李雅馨,郎啟娥,等.深度學習的發生過程、設計模型與機理闡釋[J].中國遠程教育,2020,(1):54-61、77.
[31]高婷婷,郭炯.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研究綜述[J].現代教育技術,2019,(1):11-17.
[32]Koehler M, Mishra P. What is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TPACK)?[J]. Journal of Education, 2013,(3):13-19.
[34]郭炯,郝建江.智能時代的教師角色定位及素養框架[J].中國電化教育,2021,(6):121-127.
[35]Bozkurt A, Karadeniz A, Baneres D, et 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ref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landscape: A review of AI studies in half a century[J]. Sustainability, 2021,(2):800.
[36]郝建江,郭炯.技術演進驅動教師素養發展的過程、路徑及內容分析[J].現代教育技術,2022,(7):22-30.
[37]胡小勇,李婉怡,周妍妮.教師數字素養培養研究:國際政策、焦點問題與發展策略[J].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3,(4):47-56.
[38]姜海洋,梅云,顧憲松.場景化交互設計理論的分析與研究[J].包裝工程,2019,(18):269-275.
[39]姚梅林.當代遷移研究的趨向[J].心理發展與教育,2000,(3):55-58.
[40]李寶峰,譚貞.教師專業發展導論[M].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2:51-70.
Research on the Diagnosis of Teachers’ Digital Teaching Competence Based on Interactive Scenarios
LIU Yan1LI Meng-Xing1SHU Hang2[Corresponding Author]
The strong promo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teaching ability, that is, teachers should have digital teaching competence. Under this context, clarifying th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competence and diagnosing the digital teaching competence of teachers have become the key to break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shallo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weak transformation effect.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adopted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ers’ digital teaching application and the main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teachers’ carrying out digital technology-integrated teaching, and discussed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se problems. Accordingly, relying on the scenario interaction theory and the competence migration assumption, the paper designed the diagnostic model of teachers’ digital teaching competence based on interactive scenarios. This model took the technology reserve as the “origin”, which was a three-dimensional model that included digital teach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model, this study proposed an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 diagnosis of teachers’ digital teaching competence based on interactive scenarios, which included experimental implementation, data mining, diagnostic analysis, and case extra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a model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of teachers’ digital competence, help teachers improve their digital literacy, and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digital teaching competence; interactive scenarios; digital literacy; competence diagnosis

G40-057
A
1009—8097(2024)01—0084—12
10.3969/j.issn.1009-8097.2024.01.009
本文為2023年度全國教育科學規劃國家一般項目“教師數字化教學能力的伴隨式數據診斷與跨場域提升研究”(項目編號:BCA23028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劉妍,助理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為跨學科教育研究與實踐、教師數字能力、學習科學與技術設計、學習者能力診斷測評,郵箱為flyliuyan0707@sjtu.edu.cn。
2023年9月27日
編輯:小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