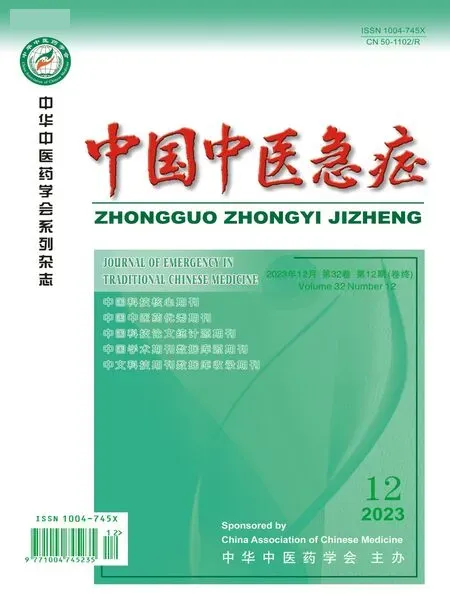從六經辨證的虛實兩端治療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的思考
高 林 張楷晨 陳虹旭 李 霄
(1.四川省樂山市中醫醫院,四川 樂山 614099;2.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四川 成都 610032)
膿毒癥(Sepsis)是宿主對感染反應失調所致危及生命的器官功能障礙[1]。據統計每年在急診和ICU 病房患者中,膿毒癥的患病率約為30%,是重要的死亡原因[2]。西醫對膿毒癥的發病機制已有較為清晰的認識[3],機體促炎和抗炎的失衡是膿毒癥發生、發展的重要基礎。胃腸道功能障礙是膿毒癥常見并發癥,即是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的早期體現,又是加重MODS的驅動器[4]。因此干預和治療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是治療膿毒癥的關鍵,目前西醫的治療手段主要是對癥、調節胃腸功能及抗感染治療[5],但治療效果欠佳。
中醫在胃腸功能障礙的治療上有其特有的優勢,其治療效果已得到學界的廣泛認可,為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的治療提供新的思路。為此筆者認為明確膿毒癥胃腸道障礙的中醫發病機制是治療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的關鍵。筆者從《傷寒論》六經辨證的角度對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進行論述。因本文重點討論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而太陽病為熱病初期,病位淺而病情較輕;少陽病為半表半里證,病情仍輕,未及膿毒癥病情之危重;厥陰病病機復雜,更側重膿毒癥患者進入慢性危重病狀態,故均不在本文討論范圍內。
1 中醫對膿毒癥胃腸道功能障礙的認識
中醫學中無“膿毒癥”這樣的名詞和概念,但在中醫藥諸多典籍均有描述與其相關類似的病癥。例如中醫經典《黃帝內經》中[6]的《素問·刺法論》中描述的“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評熱論》描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其與膿毒癥的發病機制有諸多相似之處。醫圣張仲景的著作《傷寒論》,所述的六經傳變規律與膿毒癥的發生、發展過程極為相似。現代醫學認為膿毒癥早期表現為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SIRS),晚期則表現為免疫抑制狀態,這正與《傷寒論》六經傳變過程中“三陽證”向“三陰證”的發展過程極為相似[7]。
熱性病的初期大概都是發生在太陽病,所以開始有“傷寒一日,太陽受之”,而熱性病有一定的傳變規律,常在病4、5 天的時候出現“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于脅下”,而由表傳半表半里而發生少陽病;有時也常直接傳里而發生陽明病。少陽病也有由于治療不當或不及時使邪更陷于里,而發生陽明病。正邪進一步交爭,正氣更虛,邪氣進一步深入,由“三陽病”轉入“三陰病”[20],而太陰病為三陰之首[13],首先受之。
“膿毒癥胃腸道功能障礙”根據時振聲老師的六經辨證理論[8],早期的胃腸道功能障礙與六經傳變階段的“陽明病”的特點具有一致性,“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充分體現“陽明病”胃腸病變的本質,常由太陽病失治、誤治所致,邪熱傳內入里,燥邪直犯陽明,陽明里熱與燥屎互結成陽明腑實證,出現的癥狀有大汗、申時發熱、舌苔黃、口干舌燥、燥屎內結、腹滿疼痛等癥狀,這與膿毒癥胃腸道功能障礙的早期分級不謀而合,中醫治療以通腑瀉熱為主[9]。
若陽明實證治療不及時,“三陽病”向“三陰病”發展,胃腸道功能障礙進一步加重,逐步進入六經傳變階段的“太陰病”,進一步表現為“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等一系列胃腸功能障礙進一步惡化的表現[10]。太陰病為三陰之首,與陽明病同為里證,陽明病表現為實證、熱證,太陰病則表現為虛證、寒證,中醫治療以“溫”為治療大法,且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發展到太陰病階段,除單純表現為“脾胃虛寒”的太陰病外,多合并有“邪熱未盡、腑氣不通”的陽明證候,類似于太陰病中“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的病機改變。脾為后天之本,腎為先天之本,脾之健運,化生精微,要借助于腎陽的推動,故有“脾陽根于腎陽”之說。脾腎在生理上相互資助、相互促進,在病理上亦相互影響,互為因果[22]。如脾虛濕勝,脾陽虧虛,日久則由脾及腎,損傷腎陽而成少陰病,少陰病又以陽虛寒化之虛寒證為辨證要點,胃腸功能障礙進一步加重表現為一派虛寒之象。目前西醫對膿毒癥胃腸道功能治療效果欠佳且治療手段有限,而從《傷寒論》“陽明病、太陰病”方向入手論治有望在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的治療中取得突破。
2 從陽明病論治膿毒癥胃腸道功能障礙
根據膿毒癥疾病特點,可將膿毒癥病程按六經辨證[11]的規律分為三陽病及三陰病兩大類,三陽病中太陽主表、少陽主半表半里、陽明主里,三陽病邪盛正易盛,治療應當以祛邪為主。膿毒癥胃腸道功能障礙的早期隸屬三陽病中的陽明病,該階段正邪斗爭劇烈,邪熱由表入里,燥熱之邪直犯陽明或與有形之燥屎互結而成“陽明腑實證”。“陽明之為病,胃家實也”此為《傷寒論》所記載,又有《靈樞經·本輸》[12]記載“大腸小腸皆屬于胃”,中醫所述的腸胃均屬六腑范疇,該階段患者主要臨床表現為“燥屎內結,腑氣不通”,應當給予瀉熱通便,使邪毒從下而降。初期表現為“有熱無積之無形實邪”,治以清理瀉熱為目的,典型代表方劑有白虎湯;而陽明腑實證主要表現為“燥屎內結”,也是我們討論的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的主要病機,治以通腑瀉熱為主,典型方劑為三承氣湯,而其中尤以大承氣湯使用最廣、最為人所知。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早期按照六經傳變規律當屬陽明病,此期治療相對較易,及時干預,可遏制膿毒癥進程,避免向三陰病發展,阻斷MODS 的進一步發生,改善患者預后。
3 從太陰病、少陰病論治膿毒癥胃腸道功能障礙
太陰病為三陰之首[13],患者出現“服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等更嚴重胃腸道癥狀。與陽明病相同之處在于均為里[14],都出現一系列胃腸道反應的癥狀,但不同之處在于陽明病證邪盛正強,邪正交爭劇烈,需攻下瀉熱,而到了太陰病階段病機主要以正氣虛為主,是虛證、寒證的開始階段,治療若完全按陽明病證的治療方式,會很快出現“若下之,必胸下結硬”等變證。若在太陰階段治療方式恰當,陽氣逐漸恢復,且疾病向愈,此時應給予溫中補虛加以治療,經典方劑如理中湯、附子理中湯[15]。但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發展至太陰病階段,其病機往往也更加復雜,除存在脾胃虛寒的純虛證,往往還存在陽明病未盡的“腹滿痛、大便難”的臨床表現,正如太陰病中“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的病機改變,其治療也應在強有力扶正溫陽的基礎上通腑瀉下,扶正同時兼顧瀉下祛邪。太陰病是胃腸道功能障礙進一步發展的中醫病癥,其治療正如《傷寒論》[16]中所言“有胃氣則生,無胃氣則死”,故應在強有力扶正溫陽“保胃氣”的基礎上通腑瀉下。
太陰虛寒易傳少陰,而成脾腎陽虛證,患者出現“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飲水自救”,其胃腸功能障礙多表現為下利,而與單純太陰病腹瀉不同,太陰病下利“自利不渴”,少陰病表現為“自利而渴”,為下焦陽衰氣化不利,不能蒸化津液,津液不能上承于口,癥見口渴,而其胃腸功能障礙表現為消化吸收功能的嚴重受損,癥見下利清谷、完谷不化。治療當從溫腎健脾止瀉,方多用附子理中湯[21],而少陰病胃腸功能障礙也不均為腹瀉,也有“少陰三急下證”如“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干者,急下之”“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干燥者,急下之”,“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而方均選大承氣湯,后世多認為“少陰三急下證”是瀉陽明之邪,而保少陰之陰。“少陰三急下證”應為少陰陽明并病。
4 典型病例分析
4.1 病例1 患某,女性,72 歲,因“右脅肋帶狀皰疹4 d”于2 月入院,既往有高血壓、糖尿病史20 余年、糖尿病腎病,形體肥胖、體質量指數(BMI)33.29 kg/m2。治療過程中患者出現咳嗽、發熱、最高體溫39.0 ℃,給予抗感染等治療病情進一步惡化,住院第7 天體溫仍持續波動在39.0 ℃,嗜睡,呼吸困難(呼吸頻率30 次/min 左右),氧飽和度下降(面罩吸氧89%),請ICU 會診后轉ICU 治療,完善胸部CT 提示右下肺肺炎,入ICU 后小便量少,序貫器官功能衰竭評估快速(qSOFA)評分2 分,序貫器官功能衰竭評估(SOFA)評分較基礎SOFA 評分增加2 分。入院診斷:重癥肺炎,膿毒癥Ⅰ型呼吸衰竭;2 型糖尿病,糖尿病腎病(CKD4 期),糖尿病血管病變,糖尿病周圍神經病變;帶狀皰癥等。急性生理慢性健康評分(APACHEⅡ評分)17 分,治療上給予升級抗生素為美羅培南,積極容量復蘇,間斷無創呼吸機及高流量呼吸支持。經積極呼吸支持及抗感染,患者呼吸困難及氧飽和度較前改善,白細胞、C 反應蛋白及降鈣素原均呈下降趨勢,但患者仍高熱,下午體溫最高39.0 ℃以上,仍嗜睡,不思飲食,自訴腹脹,近5 d 未解大便,急性胃腸道功能障礙分級Ⅱ級。中醫四診:體型肥胖,嗜睡,腹脹不思飲食,訴口干但不思飲水,舌紅胖大,苔黃厚干,脈洪數。參照《中醫內科學》診斷標準及六經辨證理論[17],結合患者病史及四診,考慮患者為陽明腑實證。故治療上予大承氣湯原方:生大黃30 g(后下),芒硝30 g(沖服),厚樸20 g,枳實20 g。每劑煎取300 mL;第1 天予患者100 mL 口服,每日3 次;150 mL 灌腸,每日2次,經治療患者仍未解大便,仍發熱、嗜睡、腹脹;考慮患者病重藥輕所致,第2 天原方及煎法不變,改為100 mL 口服,每4 小時1 次;150 mL 灌腸,每6 小時1 次。當日夜間患者解大便3 次,第1 次解硬結大便數枚,后兩次解稀便約1 000 mL,停止服用大承氣湯。解大便后患者精神較前明顯好轉,訴全身輕松,飲食正常,腹脹消失,未再發熱,舌苔較前變薄,黃色消退;在大便通后第3 天患者諸癥改善,轉專科繼續治療。
按:本案患者初期僅西藥治療,雖感染指標有所下降、呼吸困難有所緩解,但仍有胃腸道功能障礙癥狀、嗜睡、體溫持續不退,經大承氣湯通腑泄熱,大便通后諸癥很快改善。中醫學的一個重要理論認為“肺與大腸相互表里”,與現代醫學胃腸功能障礙是多器官功能障礙的始動環節有共通之處,故患者在大便通暢、胃腸功能改善后呼吸衰竭、發熱、嗜睡等情況也得到迅速改善。
4.2 病例2 患某,男性,74 歲,因“右下肢疼痛伴潰瘍5 個月余,加重2 個月”入院,高血壓、糖尿病病史10 余年,于我院行右下肢動脈造影+球囊擴張術及右足潰瘍清創術,住院第27 天,患者突發呼吸困難、氧飽和度下降。請ICU 會診后轉ICU 治療,完善胸部CT 提示雙肺多發感染灶,入院后患者血壓下降,予深靜脈置管后去甲腎上腺素維持血壓[去甲腎上腺素最大用量0.5 μg/(kg·h)],經無創呼吸機呼吸支持氧飽和度仍不能維持、呼吸急促,予氣管插管有創機械通氣(最高吸氧濃度80%),APACHEⅡ評分21 分。入院診斷:1)重癥肺炎:MODS[感染性休克、急性腎損傷、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ARDS)]急性心力衰竭。2)慢性雙下肢動脈粥樣硬化閉塞癥伴壞疽等。治療上予美羅培南加復方磺胺甲唑片加強抗感染,積極容量復蘇,經治療患者循環較前穩定、氧飽和較前改善,但患者入科3 d 未解大便,腹脹、腸鳴音不能聞及,胃潴留,復查CT 提示:結直腸管腔明顯擴張,其內可見大量糞石影,考慮患者胃腸功能障礙、麻痹性腸梗阻。中醫四診:神差,嗜睡,腹部膨隆,腹壁張力增高,胃潴留,舌淡苔白,脈沉數。參照《中醫內科學》診斷標準及六經辨證理論[18-19],該患者診斷為太陰虛寒證,但目前患者還表現出大便不通的“邪熱未盡、腑氣不通”的證候,且合并有“大實痛”的腹壁張力增高的太陰經脈氣血失和、氣滯血瘀,故結合太陰病“以其臟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及“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的治療原則,使用“攻補兼施,溫陽通腑化瘀”。方藥:生大黃30 g,細辛9 g,白附片30 g,芒硝15 g,枳實15 g,厚樸15 g,丹參30 g,當歸15 g。50 mL 鼻飼,每4 小時1 次;150 mL 灌腸,每6 小時1 次。經以上治療2 d 患者大便通暢、腹脹及胃潴留好轉,停用溫腸通腑法,繼續在西醫治療基礎上予溫陽健脾等中醫藥治療。繼續治療1 周余,患者成功脫機拔管,轉專科繼續治療。本案患者在太陰病基礎上,合并有陽明余邪未盡的復雜證候,故治療上扶正溫陽、通腑瀉下化瘀。
5 結 語
膿毒癥胃腸道功能障礙既是MODS 的早期體現,又是加重MODS 的驅動器,單純西醫治療手段有限且效果欠佳。根據中醫學理論,從“陽明病、太陰病、少陰病”論治膿毒癥胃腸功能障礙有望在膿毒癥胃腸道功能障礙的治療上取得突破,避免膿毒癥誘導的更嚴重的并發癥,為中西醫結合治療膿毒血癥另辟新徑,臨床上值得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