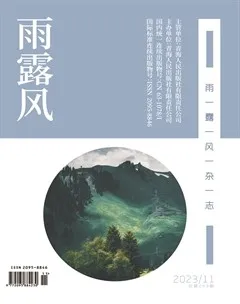漢語同形字來源及類型分析
于慧潁


漢字在發(fā)展的過程中會隨著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以及不同人們的需要而不斷進行音形義的調(diào)整,從而產(chǎn)生了許多古今相異的用字現(xiàn)象。同形字是從漢字發(fā)展的早期就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一種文字現(xiàn)象,即用一個字形來代表兩個及兩個以上的漢字。同時,隨著漢字形體的不斷發(fā)展變化,在通假字、繁簡字等其他的用字現(xiàn)象中也逐漸出現(xiàn)與之類似的同形字。
一、同形字的定義
關于同形字最早的記錄,可以追溯到顏師古為《漢書·武帝紀》做注時,在“怵于邪說”中發(fā)現(xiàn)的模糊的同形現(xiàn)象,再到鄭樵在《六書略》中提出的“雙音并義不為假借”的觀點,再到朱駿聲在《說文通訓定聲》中提出的“別義”概念,都表明同形字現(xiàn)象早就已經(jīng)為古代的文字學家所發(fā)現(xiàn),只是還沒有形成統(tǒng)一的定論。直到近代,王力先生在《字的音形義》中明確指出存在著意義不同、字形卻偶然相同的現(xiàn)象,并用疑問代詞“哪”和語氣詞“哪”“咳嗽”的“咳”和“咳呦”的“咳”舉例,來說明同形字雖字形相同,但在字音和字義上沒有聯(lián)系的觀點。
由于漢字的造字過程漫長而又復雜,能夠表示具體事物和抽象事物的字形又非常有限,所以就不可避免地會出現(xiàn)表示不同意義的兩個或幾個字的字形相近或者完全相同的情況。文字學家裘錫圭先生在其著作《文字學概要》中談道同形字是與異體字正好相反的概念:異體字是外形不同,實際上只能起一個字的作用;同形字的外形雖然相同,實際上卻是不同的字。
目前學界對于同形字的定義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同形字即沒有引申或假借關系,為記錄不同的詞而造出的字形偶然相同的字,而且同形的兩個或多個字的字音與字義之間沒有必然的聯(lián)系。如“鎬”這個字就是一個典型的狹義同形字,在上古時期,“鎬”字音讀hao,本義溫器,又假借為周朝的都城“鎬京”,但是在現(xiàn)代漢語中,“鎬”讀音gao,表示一種掘土工具,因此,讀音為hao,本義為溫器以及假借義為周朝都城的“鎬”字與讀音為gao,本義為掘土工具的“鎬”字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字,只是在造字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字形偶然相同的情況。
裘錫圭認為廣義同形字包括所有表示不同的詞的相同字形,因為從甲骨文時期到漢字發(fā)展的晚期,都存在一形多用的現(xiàn)象。如果說那些由于異時異地的原因偶然出現(xiàn)的同形現(xiàn)象是狹義的同形字,那這些由于字的數(shù)量有限而有意識地用一個字形表示多種意義的象形字,與由于借用讀音而出現(xiàn)的一字兩用的通假字,以及由于字形變化而形成的繁簡同形字,也都可以看作同形字,而且這些同形的字可能在字音或者字義上有著某種聯(lián)系。
因此我們認為,同形字不應該僅僅包括那些字形偶然相同、字音字義之間沒有必然聯(lián)系的字,只要表示不同意義的幾個字具有相同的字形,無論它們的字音以及字義之間有無聯(lián)系,都可以看作同形字。由于文字系統(tǒng)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發(fā)展變化的,因此我們不能將字形相同但音義之間可能存在某種聯(lián)系的字從同形字中剔除出去,要全面考慮其音形義之間可能存在的關系。
二、同形字的來源
根據(jù)索緒爾語言學的基本理論,每個符號都是一體兩面的,一面為“音響-形象”,一面為“概念”,“音響-形象”是“能指”,“概念”是所指。文字屬于符號的一種,所以文字符號也是“能指”與“所指”的集合體。漢字屬于意音文字,是音、形、義的統(tǒng)一體,其中“能指”由聲音(字音)和形象(字形)構(gòu)成,“所指”則是符號所對應的概念,即字義。經(jīng)過“能指和所指”理論的分析,我們得出同形字大致有三個主要來源:早期象形字的同形字、通假字中的同形字以及繁簡字中的同形字。
在早期象形字中,由于所造字的數(shù)量有限,所以同形字的概率比較大,隨著象形表意字的大范圍使用,人們逐漸開始意識到這種一形多用的現(xiàn)象會導致字意表達不明確,難以區(qū)分不同的字,進而造成文字系統(tǒng)使用和理解的混亂。于是人們開始采用多種方法來區(qū)分同形字,如用同音的符號將那些難以表意的詞語分化出來,或?qū)⒈硪夥柡捅硪舴柦Y(jié)合起來,構(gòu)成既表音又表意的形聲字,來盡量避免一形多用字的出現(xiàn)。然而隨著漢字的不斷發(fā)展,異時異地的人們在造字的時候總是會無法避免地出現(xiàn)同形字。
(一)來源于早期象形字中的同形字
在早期的象形漢字中,由于人們所造字的數(shù)量有限,所以常常出現(xiàn)用一個字形來表示多個字的現(xiàn)象,例如甲骨文表“月”字和“夕”字,甲骨文表示“大”字和“夫”字,甲骨文表“片”字與“析”字等等。由此可見,在早期漢字中,這種一形多用的現(xiàn)象是非常普遍的。
在象形造字之初,每個漢字由字形與字音所構(gòu)成的“能指”都是對應一個“所指”,表征單個特定概念的。但是在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發(fā)展后,造出來的漢字的數(shù)量無法滿足人們?nèi)粘=涣鞯男枰行┬枰磉_的意義沒有所對應的字,所以這時人們就將“能指”中的形象標準(字形)放寬,用現(xiàn)有的“能指”來表示一個新的“所指”,如此,一個“能指”就擁有了兩個或多個不同的“所指”,由此就產(chǎn)生新的對應關系,這種對應關系就包括我們所說的同形字。
例如字形為的象形字,既是“月”字,表示客觀存在的物體“月亮”,同時“夕”字也用這個字形來表示抽象的時間概念“夜晚”,由此字的“能指”就與所指“月亮”義和所指“夜晚”義同時擁有了對應關系,在這種情況下就形成了同形字。在這種同形字中,能指中的字形是一致的,字音是沒有關系的,而兩個所指之間雖然意義不同,但是依舊是有聯(lián)系的:月亮只出現(xiàn)在夜晚,二者所表示的意義有著邏輯上的關系。再比如字,既表示“片”字,本義為被劈開一分為二的木片,又表示“析”字,本義為用斧頭劈開木頭的動作。二者的字音相差甚遠,意義雖然不同,但是也可以看出兩個字的本義是有著動作-受事的語義關系的,在這個語義關系下,用這個字形作為能指,
與動作義和受事義的兩個所指分別組成對應關系,就形成了字音無關、字義相關的同形字。由此可見,正是因為身為所指的兩個意義有著邏輯上的語義關系,才會在漢字發(fā)展早期所造字的數(shù)量并不充足的情況下,用相同的字形來表示相關的意義,也正由于意義相關,人們在認知和理解時也不會出現(xiàn)很大的偏差。
(二)來源于通假字中的同形字
通假是古人用字的一種變通現(xiàn)象,即放著本字不用而臨時借用音同或音近的他字來替代,是“本有其字”的“依聲托事”。與許慎“六書說”中“本無其字,依聲托事”的假借并不相同,二者本質(zhì)的區(qū)別就是有無本字,通假是有本字的借用,假借是沒有本字的借用。
清代文字學家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提出:“假借之始,始于本無其字。及其后也,既有其字矣,而多為假借。又其后也,且至后代之訛字,亦得自冒于假借。博縱古今,有此三變。”由此可知,段玉裁將古今所出現(xiàn)的假借現(xiàn)象分為三種:一是本無其字的假借,二是本有其字的假借,三是因訛字而出現(xiàn)的假借。現(xiàn)在學界普遍認可的通假字概念,就是段玉裁所分的本有其字的假借和因訛字而出現(xiàn)的假借。
通假所借用的字,其字形是已經(jīng)在文字系統(tǒng)中存在的,字音是與本字相同或相近的,其通假義并非借來的意義,而是指這個字被臨時借用作與之音同、音近的別的字后所代表的意義。所以是否可以在已知通假的前提條件下,將借字與本字看作是字形相同,字音之間有聯(lián)系,字義不同的同形現(xiàn)象呢?在《論語》中,“康子饋藥,拜而受之。”中的“饋”字為贈送義,“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中的“歸”字,字音為gui,本義為女子出嫁,引申義為歸還,放在文中都無法解釋,利用讀音條件,推斷“歸”字是臨時被借用來代替“饋”字,表贈送義的。雖然漢字系統(tǒng)中的“歸”字并沒有“饋”字的字音與字義,但在“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這句特定的通假語境下,“歸”就擁有了“贈送”的通假義,就可以將字音為gui,字義為歸還的“歸”字與字音為kui,字義為贈送的“歸”字看作同形字。
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中提到,在通假中有一種特殊的類型,叫作形借,即不管一個字原來的音義,只借用它的字形的一種現(xiàn)象。形借與正常的通假不同,一般的通假都是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來表示,但形借卻是無關音義,只借字形的情況。例如“隻”字,《說文解字》中釋義為“從又持隹”,表示“獲得”義,后來有了新的釋義,將“從又持隹”與“二隹曰雙”相對,用來記錄表量詞的“只”義,在這個借用的過程中,僅僅借用了“隻”的字形來記錄量詞,與其原本的音義沒有任何關系。因此,在形借中,一個字原來所代表的意義跟借它的形的那個字的意義之間沒有本義與假借義的關系,也沒有本義與引申義的關系,對于這個字形來說,不需要特定的通假環(huán)境來作條件,在語言系統(tǒng)中,它們都可以看作本義,這也是通假字中存在的另一種同形現(xiàn)象。
在面對一些比較抽象的概念和事物,無法用具體的象形形狀來表示其意義時,人們就會從字音的方面放寬標準,將“能指”中的字音與新的“所指”相結(jié)合,從而在原有的“能指、所指”的配套關系之外形成新的對應關系,這就是我們常說的“假借”。到了漢字發(fā)展的后期,隨著形聲字的出現(xiàn),人們已經(jīng)創(chuàng)造出足夠數(shù)量的漢字去表達意義,但是由于避諱、訛字、書寫習慣等文字規(guī)范化方面的原因,“假借”的現(xiàn)象并沒有隨著漢字數(shù)量的增加而消失,人們反而有時會故意利用兩個“能指”中字音的相同或相近的關系,突破字形的限制,在具體的語言環(huán)境中,賦予其中一個字新的“所指”,使這個字在“能指”相同的情況下,表示不同的“所指”。除了上文的“歸”和“饋”,“匪”字的本義是一種竹器,但在《詩經(jīng)》“我心匪石,不可轉(zhuǎn)也”中,“匪”字就借用了“非”的否定義,這樣就可以將本義為竹器的“匪”字與通假義為否定的“匪”字看作同形字,但是這種同形如果脫離了通假的語言環(huán)境,二者的同形關系就消失了。而通假中的形借則無論字音相同或相異,僅借用其字形來與新的“所指”建立對應關系,這個“所指”也可以看作是與“能指”雙向?qū)年P系。例如上文提到的,借表示“獲得”義的“隻”的字形,來表示與“雙”相對應的“只”義,我們也可以將“隻”字看作是為了表“只”義而專門借用的字形,這樣“隻”字的所指既可以與表示“獲得”義的能指相對應,又可以與表示“只”義的所指相對應。
由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得知,在通假字中,有兩種情況都可以看作同形現(xiàn)象。一種是在通假的語境條件下,借字可以與音同或音近的本字看作同形,但是一旦脫離了通假的語言環(huán)境,兩者之間的同形關系就會消失;二是在無關字音字義只借用字形的形借中,不需要特定的語言環(huán)境,就可以將借字與本字看作同形字。
(三)來源于繁簡字中的同形字
繁簡字是繁體字和簡體字的合稱,所謂繁體和簡體,是就同一個字在構(gòu)形表象上的繁復與簡單相對而言的,構(gòu)件或筆畫多的是繁體,構(gòu)件或筆畫少的是簡體。漢字字形的趨繁與趨簡并不是單向發(fā)展的,而是人們在漢字的使用過程中根據(jù)社會用字自然選擇的結(jié)果,所以繁體和簡體并不存在絕對的時間上的先后關系。
字形在進行繁簡變化后,有可能會出現(xiàn)與某個已經(jīng)存在的字的字形相同的現(xiàn)象。例如“體”字在宋代剛出現(xiàn)時,本是從“人”“本”聲的形聲字,音義與“笨”字相同,表粗苯、粗魯義,《廣韻·混韻》:“體,粗貌,又劣也。”而表示身體義的“體”字在宋代之后簡化為“體”,是從“人”從“本”的會意字;“廣”字,在《說文解字注》中的釋義為“廠者,山石之厓巖。因之爲屋,是曰廣”,即依山而建的房子叫作廣,而繁體“廣”字在《説文·廣部》中釋義為“廣,殿之大屋也”,其在字形簡化后與本義為依山而建的房屋的“廣”字相同;再如“價”字,在《說文解字注》中釋義為:“從人介聲,善也。”是本義為“善”義的形聲字,而后世簡化為“價”字的“價”字卻是本義為“價值”,“從人賈,賈亦聲”的會意兼形聲字。以上這些字都可以看作是古人在偶然的情況下,對字形進行改造時形成的同形字。
到了近代,國家開始推行漢字簡化政策后,也出現(xiàn)了大量某字簡化后的字形與古字中某個字的字形完全一樣的同形現(xiàn)象。例如繁體表“聆聽”義的“聽”字,簡化后為“聽”,但在古書中早已存在“聽”字,在《說文解字》中釋義為“笑皃,從口斤聲,宜引切”,即音讀yǐn,表“笑貌”義;繁體表“適合”義的“適”,今簡化為“適”,而“適”在《說文解字》中釋義為“疾也,古活切”,音為kuò,表“迅疾”義;繁體表“建造”義的“築”,簡化后字形為“筑”,而“筑”字在古代音為zhú,是一種樂器的名稱,還有如表“勝利”義的“勝”的簡化字與“高處不勝寒”中表“禁得住”義的“勝”同形;表“不好”義的“壞”的簡化字與“隙大而墻壞”的“壞”同形等。
繁簡字的同形現(xiàn)象可以看作是在繁體字簡化過程中,簡化后的“能指”的字形恰好與某個古字的“能指”中的字形相同,但是在簡化的過程中,被簡化的字之所以與某個古字字形相同,并非完全出于偶然,與能指中的字音擁有一定的關系。例如“聽”字上古音為疑母文部,“聽”字上古音為透母耕部,文耕旁轉(zhuǎn),故讀音相近,所以是能指相關,所指不同的同形字。這類同形字大多數(shù)不在同時同地出現(xiàn),只需要在閱讀古書時進行區(qū)分。就像我們現(xiàn)在使用簡化字“聽”時,使用的是其在簡化前“聽”字所對應的“聽話”義,而不是古“聽”所代表的“笑貌”義,但是在閱讀古書時碰到“無是公聽然而笑”這類情況,要注意使用古“聽”字的音義。
至此,我們可以總結(jié)出,同形字三個來源的本質(zhì)都是突破了“能指”中的字形范圍,來與其他“所指”的意義相結(jié)合從而產(chǎn)生新的對應關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早期象形文字中人們有意識創(chuàng)造的同形字,不僅字形相同,兩個字的字義可能也是相互關聯(lián)的。通假中的一部分同形現(xiàn)象是利用“能指”中字音的相同或相近關系來選擇需要突破的字形,在特定的語言環(huán)境中讓一個所指代表兩個能指,但是脫離了具體的通假環(huán)境,同形關系就不成立。在形借中,僅僅借用能指的字形來與新的所指形成新的對應關系,與字音字義皆無關,是狹義的同形字。繁簡字中的同形現(xiàn)象大多是由于繁體字在簡化后的字形與某個早已存在的古字字形相同,簡化時以能指中字音的相同相近為條件,形成能指相同、所指不同的同形字。
三、同形字類型的劃分
關于同形字的分類,裘錫圭最早在《文字學概要》中根據(jù)同形字在結(jié)構(gòu)或形體上的特點,將同形字分為四類:文字結(jié)構(gòu)性質(zhì)不同的同形字、同為表意字的同形字、同為形聲字的同形字以及由于字形變化而造成的同形字。
文字結(jié)構(gòu)不同的同形字是指在不同時期,用不同的造字方法造出來的具有相同外形的字,例如“價”字、“聽”字。同為表意字的同形字是指擁有相同字形的兩個表意字分別表示不同的意義,例如早期象形字中的字。同為形聲字的同形字是指擁有相同字形的兩個形聲字分別表示不同的意義,這類同形字與其他性質(zhì)的同形字最大的區(qū)別就在于:其他性質(zhì)的同形字,彼此之間的讀音是毫無聯(lián)系的,而同為形聲字的同形字,彼此之間的讀音一定是相同或相近的。在由于字形變化而造成的同形字中,造成字形變化的原因有很多,字體的演變、字形的繁簡變化以及避諱、訛字等,只要是由于字形的變化而同形的字,都可以歸到這一類,最典型的就是在漢字簡化的過程中,繁體字簡化后與某個古簡體字的字形相同,如上文的“聽” “廣”等。
但是在這種分類方法中,一個同形字是無法絕對地歸入某一類中的,這違背了分類的唯一性原則。繁簡字中字形簡化前后造字方法不同的,既可以看作文字結(jié)構(gòu)性質(zhì)不同的同形字,也可以和繁簡字中的其他同形字一樣,屬于由于字形變化而造成的同形字。比如“體”字,剛開始的“體”字是從“人”“本”聲的形聲字,音義與“笨”同,到了宋之后,表“身體的部分”義的“體”字簡化為“體”,簡化后的“體”是從“人”從“本”的會意字;再如“聽”字,古字“聽”是從“口”“斤”聲的形聲字,表“笑貌”義,近代將繁體“聽”簡化為“聽”,簡化后的“聽”是從“口”從“耳”的會意字;通假字中大部分的同形字可以歸為同為形聲字的同形字,例如“琟”字就是同形形聲字,表示似玉之石的名稱時,是從玉隹聲的形聲字;表示某種鳥的名稱時,是從隹玉聲的形聲字,但是通假字中的形借卻屬于同為表意字的同形字;還有一種特殊的字形簡化的同形字:兩個不同的形聲字的簡化字是同形的形聲字,例如“獲”和“穫”都簡化為“獲”,“鐘”和“鍾”都簡化為“鐘”等等,我們既可以將這類字歸入由于字形變化而造成的同形字,同時也可以看作同為形聲字的同形字……像這樣同屬于多個分類的同形字,在使用時會產(chǎn)生理解上的混淆。
為了避免上面的弊端,基于能指和所指理論對同形字來源的分析,我們可以根據(jù)同形的字之間的音形義關系,對同形字進行分類,分為以下三類。一是字音字義無關的同形字;二是字音無關,字義相關的同形字;三是字音相關,字義無關的同形字。
首先,由于狹義同形字是在偶然的情況下出現(xiàn)的字形相同的現(xiàn)象,與音義無關,通假中的形借現(xiàn)象也是僅僅借用字形來表示不同的字,也與字音字義無關,因此我們可以將狹義的同形字與通假中的形借一起歸為字音無關、字義無關的同形字。
其次,早期象形字中的同形字出現(xiàn)的條件是字義之間相互關聯(lián),因此我們可以將早期象形字中出現(xiàn)的同形字歸為字音無關、字義相關的同形字。
最后,由于繁簡字中的同形字之間在字音上存在某種關聯(lián),一般的通假字是以字音相同或相近作為通假的條件,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兩類歸為字音相關、字義無關的同形字。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一般情況下的通假字只有在通假的語境中才可成立,如果脫離了特定的通假環(huán)境,就不能看作同形字,因為在漢字系統(tǒng)中通假字的字形和與通假義之間并沒有建立起穩(wěn)定的能指與所指關系。
采用通過音形義之間的關系對不同來源的同形字進行分類,對同形字的研究和發(fā)展將會有促進作用。這種分類方法一是更加簡潔明確,二是根據(jù)音形義的關系分類不僅適合狹義的同形字,范圍更加寬泛的廣義同形字也能夠進行有效的分類整合,能夠更加清楚明了地看出各類同形字的特征。另外能夠為以后對同形字之間音形義可能存在的相關關系的研究做出合理假設,進而提出字音與字義源流探究的新思路。
四、結(jié)語
由上述分析可知,漢字是一種結(jié)構(gòu)復雜且歷史悠久的文字,同形字是古代漢語系統(tǒng)中非常重要的文字現(xiàn)象,對漢字的發(fā)展研究有著重要的意義。我們不可以在分析時將其音形義的關系完全地割裂開來,很多同形字之間都或多或少地在字音和字義上有所關聯(lián)。同形字對古籍文獻的閱讀、文獻校勘、語文教學、漢字源流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還需要文字學家們在此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