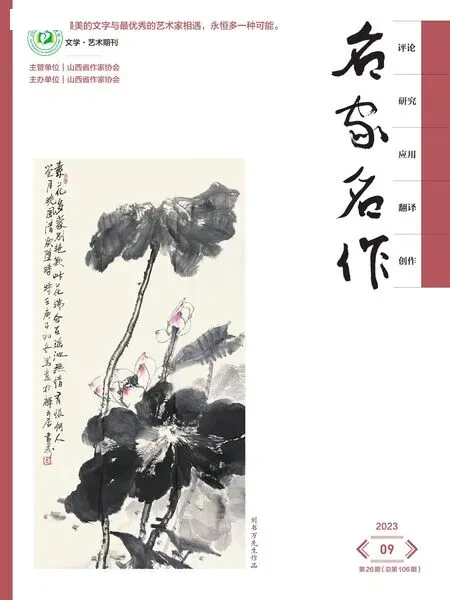審美焦慮:美學領域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虛無悖論
陳思行
過去,人們通常認為審美主體的評價反映了審美客體的內在品質。然而,隨著文化發展的現代化和多元化趨勢的加強,使人們發現藝術和美學領域的審美評價是非常主觀和有限的。審美主體在欣賞藝術時不僅是在評價藝術品本身的價值,更多是在評價自身的審美水平和品位,這樣就會產生一種焦慮:審美主體無法確定自己的評價是否正確,也無法確定別人的評價是否正確。審美焦慮也表現為對于審美品位的困擾和不自信,這種困擾和焦慮往往導致人們無法真正欣賞和享受藝術,從而使藝術無法被完整地理解和傳達。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重新反思審美主體評價的真實性和客觀性,特別是關于言語描述與審美客體真正審美價值之間的關系。審美主體憑借自身的審美價值觀去評價藝術品,在評價的同時產生對審美客體的認識,但是這種認識又會集中于審美主體自身的感受,從而導致審美客體在美學價值上存在虛無。審美主體作為審美客體的價值賦予者,其審美過程的主觀性反而剝奪了審美客體一定的價值,然而不經受審視同樣會導致審美客體無法擁有主觀價值。審美主體既希望對審美客體進行客觀的評價,又無法避免主觀性的介入,二者產生的矛盾關系正是審美中的虛無悖論(Paradox of the criterion)。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虛無悖論使審美評價不可避免地主觀化,從而成為審美焦慮的來源之一。
一、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概念與關系
審美主體特指審美活動中的主體,是在審美活動中與審美客體構成對象性關系的一方,審美主體是審美活動的發出者、承擔者,在審美活動中起著積極的主導作用。審美主體是在社會實踐特別是審美實踐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審美能力的人。審美主體是與審美客體相對的美學范疇。
而審美客體與審美對象都是源于對西語“aesthetic object”的翻譯而產生的現代漢語詞匯。故在現行的美學理論中,審美客體與審美對象是兩個沒有區別的、可以相互替換的同義概念。即它們的所指都是在審美活動中審美主體與之發生關系的事物,但在本文的探討中,審美客體的概念需要更加明確地確定下來。在20 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中,朱光潛先生曾提出著名的“物甲”和“物乙”說,以說明審美活動中所涉及的真正對象是“物的形象”(物乙), 而不是“物” 本身(物甲)。他說:“物甲是自然物,物乙是自然物的客觀條件加上人的主觀條件的影響而產生的,所以已經不是純自然物,而是夾雜著人的主觀成分的物。換句話說,已經是社會的物了。美感的對象不是自然物而是作為物的形象的社會的物。”而本文的審美客體指的是“物的本身”(物甲),并且關注的正是基于審美主體的評價而產生的“物的本身”(物甲)與“物的形象”(物乙)之間的偏差,以及這種偏差帶來的審美價值的虛無。
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關系作為審美評價的核心,在不同的學派得到了不同的解釋和分析。在實證主義美學中,審美價值是獨立于審美主體的。實證主義認為藝術品的價值只與藝術品本身有關,并且可以被觀眾以非主觀的方式接受和理解,也就是可以被世界的經驗證實。實證主義一味地強調工具理性,否定了藝術作品的超越與批判維度。
而符號學美學認為,藝術品本身沒有確定的內涵和意義,藝術的價值意義是觀眾與藝術品的互動過程中共同構建的。也就是說,藝術品的意義和價值不單單依賴于藝術品本身,同樣需要觀眾的參與和理解。符號學肯定了主體與符號客體之間的意向性關系。
相對而言,存在主義美學更注重觀眾的主體性和個人經驗。存在主義觀點認為,藝術作品不是一種認知或傳達消息的工具,而是一種情感和意識的表達方式,審美主體對于藝術作品的反映是藝術品價值的一部分。作家的意識活動和美感產生的一致性在創作過程中主要是通過主體和客體的關系表現出來,并且存在主義者所竭力反對的正是那種把藝術創作看成一種無中生有、 空對空的主觀臆造的觀點, 他們只是充分肯定了作家的主觀能動性在文學創作中的主導地位。
從實證主義到存在主義,審美主體評價的主觀性呈現出越來越重要的態勢。但不管采用哪種學說,審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都是一個普遍問題。準確來說,是審美價值的始源性問題,即審美價值是源于審美主體的主觀性還是審美客體的客觀性。但是何為主觀價值、客觀價值,非常難以回答。除此以外,審美主體做出的評價是針對“物的形象”(物乙)這一存在于主觀想象中的“物”,這種偏離造成了審美客體和主體之間永遠無法完全重合的問題,也就是虛無悖論。
二、虛無悖論在審美過程中的應用
著名的哲學思想實驗:假設一切都不存在,“不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描述狀態的概念,如果“不存在”這個概念存在了,一切就不可能不存在。這個思想實驗被稱為虛無悖論。在哲學和邏輯學領域,虛無悖論是指在某種邏輯系統中,如果某個主張A 引申而來的B,又會單方面影響到A 的可證明性或者真值,那么就會出現A 和B互相沖突加以證明和證偽,最終導致該邏輯系統內部矛盾、混亂和無法完全確定的問題。
在審美邏輯中,審美客體的審美價值是需要被評價或者證明的A,而審美主體的判斷則是基于A 生發的B。審美主體品位的個體差異和主觀性會影響其對審美客體的價值評定,倘若沒有評價,審美客體將不具備審美價值。因此審美客體的審美價值(A)與審美主體的判斷(B)呈現出一定的沖突和矛盾,即審美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虛無悖論。并且在審美客體被凝視的過程中,審美主體的評價不一定能夠充分表達出其本身的審美體驗,在表達的偏差下,審美客體的審美價值還受到主體表達能力的限制,使審美客體的價值處于更“虛無”的狀態,難以達到審美客體的美的真實。
(一)審美主體:意義的偏離
審美焦慮作為社會心理狀態,指的是對于自己的審美觀念、審美表現、審美能力的不確定、擔憂和壓力。在當今社會,很多人對自身的外表和審美能力產生了焦慮感,難以接受自己不符合主流審美觀念的一面——多元的文化使“正確的審美”成為比以往更加難以回答的問題,審美主體在形成判斷時會受到諸多觀點的影響,因此審美客體的價值構成時也產生了更大的偏差。
審美主體造成審美客體價值偏差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從審美主體的判斷構成上來說,在審美主體形成觀點時,自身意見與主流觀點相互糅雜,其他觀點的影響會使主體偏離最初的審美感受。當主體在權衡如何做出最終評價的時候會產生審美焦慮,因為他不能夠明確應當聽從內心還是跟隨大眾;另一方面,固有的語言和概念可能與審美主體的審美感受相去甚遠,當主體試圖用語言準確地表達他們的審美意見時,他們會受到語言系統的局限,遇到概念混亂、邏輯矛盾等問題。
當審美主體試圖理解和表達藝術作品的審美特征和價值時,但同時也意識到自己的理解和表達容易被限制和扭曲,虛無悖論中因審美主體的主觀性而生成的矛盾也就浮現出來。審美中的虛無悖論通常會導致審美主體感到困惑和不安,因為他們意識到無論他們如何努力,他們最終仍然無法徹底理解或表達藝術作品的完整性和復雜性。
(二)審美客體:價值的消解
當談到審美客體的價值時,客觀價值和主觀價值是兩個重要的方面。客觀審美價值指的是客體可以被測量、比較和評估的美學價值,如美術中標準的臉是“三庭五眼”,視覺藝術中黃金比例是0.618:1 等。從樸素的生活經驗上觀察,通過這種衡量客觀價值的方法,不同人的客觀價值評價往往會趨于一致。相對而言,審美的主觀價值是指個體對審美客體的個人主觀感受。這種價值不僅在不同個體間存在差異,并且每個個體自己的價值感受也是隨時間變化的。客觀價值和主觀價值這兩個方面的價值互為關聯,它們經常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共同決定了一個審美客體的真正價值。
審美主體憑借自身的審美價值觀去評價藝術品,在評價的同時產生對審美客體的認識。在虛無悖論中,正是審美主體的主觀價值觀念和觀察方式,使審美客體的本來面貌受到扭曲或失去了客觀存在的意義。具體而言,審美客體在虛無悖論中的影響主要來自審美主體對于它們的理解和表達的不確定性。如果審美主體對于一個藝術作品的理解和表達存在不一致,那么他們的評價和解釋可能會相互影響,從而導致后人無法真正欣賞和理解這個作品。另外,審美主體對審美客體的不確定性可能會導致人們對藝術作品的評價和推崇存在一定的保留和謹慎。當一個藝術作品過于復雜或者模糊不清,可能會導致人們對這個作品的評價存在爭議或者多元化,可能會對它的市場、傳播和影響力產生一定的影響。
三、緩解審美焦慮:主觀感受和客觀評價協同工作
虛無悖論挑戰了人們對“存在”的理解。通常人們認為“存在”是一件很簡單、不需要解釋的事情,但是虛無悖論表明“存在”并不是如此不可動搖,它充滿了哲學和語言學的細微差別和陷阱。解決虛無悖論的方法之一是在語言中限制表達的方式,以確保在說“不存在”時,不會產生自相矛盾的結論。而在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虛無悖論中,審美客體的價值因審美主體的偏離而受到影響。因此,探尋審美客體真正的價值所在需要主觀感受與客觀評價協同工作,以主客觀統一的價值觀審視審美客體。并且探究何為“正確的審美尺度”以解釋審美判斷的共識,緩解審美主體的審美焦慮。可以說,不管是解決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虛無悖論還是緩解審美焦慮,關注的都是審美的主觀性和客觀性如何平衡。
(一)審美判斷的客觀論
客觀論的核心觀點就是美在于物,主觀論的核心觀點就是美在于心,主客觀關系論的核心觀點是美在于主客體的關系中。但是在具體的審美判斷中,即使是細微的觀點差異也將表現出巨大的差距。最堅決和徹底的客觀論者堅持認為美是物的一種客觀屬性,甚至認為美的存在是不以人的存在為前提的。客觀論者一般認為審美客體的美學價值有某種公認的客觀性,這種客觀美的屬性是真實存在的,以至于一個不認同所謂的價值的審美主體會被視為審美能力有缺陷。唐納德·梅里爾提出:
1.審美判斷具有普通有效性。它不是正確的就是錯誤的。如果出現審美判斷的不一致,只能說明正確與錯誤這種矛盾的存在。
2.審美判斷與個人好惡無關。個人的情感和知覺可能導致他做出錯誤判斷,這種判斷就沒有什么普遍有效性。同樣如果一個集體做出的是錯誤判斷,它也沒有普遍有效性。
3.審美判斷的客觀性,表現為主體和客觀屬性之間的固有聯系。只是這種事物的客觀屬性是什么,在客觀論者中間存在不一致。
4.審美判斷中存在不一致,這是事實。但這一事實并不能證明主觀論是正確的。因為審美判斷有正確與錯誤之分,錯誤判斷只是一種無知,因此對那些毫無顧忌地說出自己錯誤判斷的人來說,提高自己對審美的辨別力則是他們的責任。
一件畫作,對于一個經過嚴格訓練的畫家來說,他或許會根據畫作中的細節和技術問題來評價它的美學價值。而對于一個普通觀眾來說,他可能更關注畫作所呈現的情感和主題,如畫作所表達的愛情、悲傷等情感。但梅里爾的理論意味著對普通觀眾審美權利的剝奪,因為錯誤的判斷不具備“普遍有效性”。即使人們的審美判斷與“普遍有效性”一致,也并不能說明這來自他們的自由意志——他們的評價也有可能是對“普遍有效性”的屈服,不然他們將被指為審美能力欠缺的主體。更何況“普遍有效性”實際上是難以被建立的,所謂“普遍有效性”的存在在應用中往往是“專家的意見”或是“主流的觀點”。因此,并不是美的客觀性使不同人的審美觀點變得相似,而是人們類似的審美產生了對美的基礎共識。
過分強調客體的價值而忽視主體的主觀性,不僅會導致非權威個體審美話語權的喪失,還會加強藝術作品被過分規范化或客觀化的危險,使審美判斷變得呆板和格式化。如果審美主體被審美共識馴化得逐漸失去個性化的審美判斷能力,那么也就只能相對應地欣賞平庸、缺乏創意和想象力的藝術作品。
(二)審美判斷的主觀論
審美的主觀論認為個體的審美經驗是因為個人的觀念、情感、文化背景和個人經歷等主觀因素的影響而形成的。此觀點由于強調主觀因素的重要性,因而在現代的藝術理論與學術理論中備受重視。
審美的主觀論的合理之處在于它與個體的主體性有關。不同的人可能會對同一件事物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此外,不同文化所賦予的美學價值觀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客觀的標準很難適用于所有文化和時空背景。上文提到的黃金比例實際上也只適用于一定范圍內的視覺藝術,人們不能夠斷言一個符合黃金比例的矩形就比正方形更加美,而是在不同的情況下應當運用不同的圖形。審美的主觀論側重于主體性和個性化,更好地強調了創造性和多樣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解讀藝術作品。
主觀論認為美感是主觀的、個人的和情感的體驗,無法被客觀的標準和規則進行描述和界定。然而,如果審美客體的美學價值全然仰賴審美主體的評價,那么審美主體就可以隨意抹殺掉美的存在,探究美學就沒有意義了。審美主觀論的深層邏輯置審美客體的價值于虛無之中,形成了一個矛盾的閉環。除此以外,按照主觀論,審美主體也就不會產生有關自身審美能力是否不足的焦慮,因為人們沒有必要去聽從權威的審美意見或是隨大流。因此,盡管審美主觀主義對一些社會現象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但由于它將鑒定客體美學價值的權利全部賦予個體,就造成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虛無悖論的同時,難以回答為何審美主體依然會感到焦慮的問題。
(三)主觀論與客觀論的統一
在客觀論的觀點中,美普遍被表述為審美客體的一種特殊屬性,雖然這種屬性是難以被證明和分析的。通過這種表述可以發現,客觀論者觀察美時常是從形式的角度入手,因為只有形式、表現手法等層面易于度量,而審美主體的反應則很難被量化。但評估審美客體的價值時應當將它的形式、內容、表現手法和觀眾的情感反應等多個方面都納入考量,而不是無視難以量化的評價。將主客觀的方法結合起來,可以更全面和準確地理解藝術作品的內在價值和意義,更好地享受和欣賞藝術的美感,也有利于促進人們對美的認同、分享,共同得到快樂的體驗。
雖然美不能夠脫離審美主體而存在,但審美主體的感受卻存在一定的共性。人類社群具有基本一致的生理結構和相似的生存環境,這也是為什么東方與西方的歷史大相徑庭,人們卻仍然有著類似的生活習慣和普遍的道德標準。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觀構成了審美的共通。即便結構性的一致難以被具體表述出來,也不能夠說明結構性的一致不存在。因此,客觀論的價值正在于其對普遍性的準則和標準的強調,而主觀論尊重個體的審美體驗,又對極端化的客觀論進行了制約。主客觀評價的結合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評價藝術品,消解審美主體與審美客體的虛無悖論。
四、結語
對于審美焦慮而言,主觀論強調了美的個體經驗和感覺,可以讓人在鑒賞時更自由、舒適和真實地感受一件作品。而客觀論從形式和規則上定義了作品的特征與美學屬性,可以為人們提供理性的指導和評價,減少審美主體對自身審美感受和經驗的不確定性和矛盾感。在實踐中,審美主體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運用主客觀相結合的思路,更全面、準確地評價和欣賞藝術品,帶來更豐富多彩的藝術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