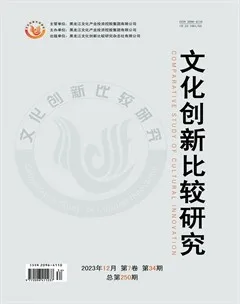中央文獻日譯的譯者立場研究
——以黨的二十大報告日文翻譯為例
齊珂,胡蓓蓓
(南京工業大學,江蘇南京 211816)
黨的二十大報告[1]等中央文獻的外譯是為黨和政府立言發聲。 不同語言之間的表達并不是一一對應的,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立場會對譯文產生深刻影響[2]。因此,在中央文獻的解讀和翻譯過程中,譯者應持有明確且堅定的立場。在強調文化自信的語境下,翻譯學界越來越重視譯者立場研究。 本文從譯者立場這一研究視點出發,分析譯者所采取的翻譯策略,以期為中央文獻外譯研究提供新啟示, 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和加快構建中國敘事體系提供方法參考。
1 立場的定義及其在外譯中的重要地位
言出必有“立場”(stance)。在社會語言學視角下Jaffe 給出了“立場”的定義:立場是言說者或作者使用語言表達命題意義的概念, 主要指言說者或作者的情感、態度、判斷和期望[3]。 這意味著在言語中,人們通過詞匯和語法來表達他們對特定命題或信息的看法和感受, 即立場的表達可以在詞匯和語法中找到,這有助于理解言語中立場表達。 Du Bois 對立場的定義進行過較為詳細的闡述, 他認為一個立場表達行為同時包含三方面的子行為:(1) 評價客體;(2)定位主體(通常是說話人本身);(3)形成與其他主體的離合關系[4]。 立場行為不僅是簡單的感情、態度或價值判斷的單向表達, 還包含立場主體在互動過程中的相互定位、關系協商和身份建構。 Kiesling認為立場包含認識立場(epistemic stance)和人際立場(interpersonal stance)兩個方面,是“說話人對自己所講內容的態度表達和說話人對與聽話人關系的態度表達”[5]。換言之,認識立場能夠體現譯者對自己所翻譯內容的態度和情感傾向, 人際立場則能夠體現出譯者與譯文讀者的關系,體現出譯者想要向譯文讀者傳達什么,而自己又是站在什么位置上向讀者傳達這些內容的,即譯文可以看出譯者對話題的態度和對譯文讀者的態度。立場體現了譯者對翻譯內容和讀者的態度, 以及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處的位置[6]。
總之,譯者立場在翻譯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譯文并不是簡單、機械的語碼轉換的結果,而是譯者與原文、譯文讀者之間深刻互動的結果。中央文獻的翻譯相比于其他文學作品的翻譯,有其特殊性:中央文獻的外譯是在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進行的, 譯者代表的是國家意志和國家立場[7]。黨的二十大報告等中央文獻的外譯是為黨和政府立言發聲。因此,在中央文獻的解讀和翻譯過程中譯者應持有明確且堅定的政治立場。 這種立場影響著譯者在翻譯實踐中的抉擇,譯文的字里行間都能透露出譯者的態度和取向。
2 黨的二十大報告日譯譯者立場的實現策略
從 Du Bois 的“立場三角”理論(Stance Triangle)出發,以黨的二十大報告日譯文[8]為例,分析譯者的立場具有互動性、動態性和建構性。 具體通過閱讀、查找、梳理、統計和分析黨的二十大報告日譯文的詞語、句法、副語言等語言表現形式,歸納總結譯者對語言信息的解碼與編碼規律, 透視譯者立場并使其顯性化的實現策略。 同時, 反映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構建中國敘事體系、彰顯國家意志的途徑、策略、原則,以及上述內容與譯者立場間的內在關系。譯者既要在篇章和修辭層面確保原文信息的真實性和流暢性,又要堅守譯者身份、立場并確保意識形態。
2.1 語氣選擇
日語是一門委婉的語言, 日語的委婉表達具有模糊、曖昧、多義等特點[9]。但黨的二十大報告日譯文中譯者則較少使用日語中委婉的語氣表達, 而是使用了更為堅定的語氣, 原因在于譯者立場植根于其身份特征、角色定位及意識形態。
表1 統計了黨的二十大報告日譯文中典型日譯句末表達的數量及例句,發現表示斷定的“である”出現了95 次之多,而表示推量的“であろう”僅出現1 次。 這不僅是譯者為傳達原文意思而做出的努力,也體現了譯者對所譯內容的認同及自信與自豪,展現出譯者的人際立場。

表1 黨的二十大報告日譯文中典型日譯句末表達的數量及例句
2.2 附加外來語文注
具有較強的政治性、 政策性色彩的關鍵表述采取附加文注的方式,術語本身用漢字表記,文注用具有一定專業性和普遍意義的外來語表記方式[10]。 根據Du Bois 的“立場三角理論”,立場具有互動性,因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必須時刻關注讀者群體的接受程度。黨的二十大報告的國外受眾主要是國外媒體、政界、學界、商界等,使用漢字表記同時附加外來語文注,實現了中日文形式和意義的統一,體現了文化自信和譯者的人際立場,即關照讀者接受,采取合作態度,主動講好中國故事,積極融入國際社會。例如:
原文: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
譯文:系統性(システミック)リスクを生じさせないという最低ラインを守り抜く。
日語常使用“系統”“系統的”,而“系統性”的表達并不常見,更為廣泛的表達是外來語“システミック”,譯者充分考慮讀者從而更準確地傳達了原文。
2.3 解釋性翻譯
此翻譯方法注重保留中文原有表達, 同時使用括號解釋其語義,體現了譯者與讀者的互動,展現譯者的人際立場。
2.3.1 四字詞語的翻譯
直接使用漢字書寫,用日文解釋其意思。在中文里同時使用多個四字詞語可以讓文章氣勢磅礴,如果在翻譯時舍棄四字詞語的使用會使氣勢削弱,因此譯者站在弘揚中國文化的立場上保留了四字詞語, 并在括號中解釋其意思。 既保證了意義傳達準確,又體現了譯者的立場。 例如:
原文:其中蘊含的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 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
譯文:そこに內包する、「天下為公(天下を公と為す)」、「民為邦本 (民は惟れ邦の本)」、「為政以徳(政を為すに徳を以ってす)」、「革故鼎新(故きを革め新しきを鼎る)」、「任人唯賢 (官に任ずるは唯だ賢才をせよ)」、「天人合一」、「自強不息(自ら彊めて息まず)」、「厚徳載物(厚徳もて物を載す)」、「講信修睦(信を講じ睦を修む)」、「親仁善隣(仁に親しみ隣に善くする)」などの考えは、中國人民の長期にわたる生産·生活の中で積み上げられた宇宙観、天下観、社會観、道徳観の重要な表れであり、科學的社會主義価値観の主張と高度に一致するものである。
2.3.2 科技專有詞匯的翻譯
科技專有詞匯較為新興, 中文為了能讓這些詞匯更具大眾性,并未使用晦澀難懂的音譯外來語,而是選用更形象的語言表達以確保大眾能夠理解。 而日語習慣于使用英文簡稱, 因此黨的二十大報告的譯者將這些名詞按照中文意義翻譯, 力求用日語中的“類義語”“外來語”等使表達變得更貼切,同時注解出英文簡稱。 例如:
原文:人工智能
譯文:人工知能(AI)
原文:物聯網
譯文:モノのインターネット(IOT)
2.3.3 地名的翻譯
中文習慣用省份簡稱來稱呼某一地區, 黨的二十大報告譯者也直接用漢字表示地區, 并注解出具體所指的省份。 例如:
原文:京津冀
譯文:京津冀(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原文: 成渝
譯文:成渝(成都·重慶)
“京津冀”不僅是地理地區名稱,它還具有重要的地區協同作用。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面向未來打造新的首都經濟圈、 推進區域發展體制機制創新的需要,是國家一個重大戰略。 因此,單純地將“京津冀”翻譯成北京、天津、河北是不恰當的,這樣體現不出我國對這整個地區的政策, 所以譯者選擇將其直譯為“京津冀”,并在其后增添解釋。
2.3.4 漢語專有詞匯的翻譯
對于中國專有詞匯, 譯者采用的翻譯策略是根據意思創造新的日語詞匯, 并在其后具體解釋出該詞含義。 例如:
原文:超大特大城市
譯文:巨大都市(人口五〇〇萬人以上の都市)
2.4 梳理與調整邏輯關系
針對具有較強的政策性色彩的關鍵表述采取了意譯的解釋, 既實現了中日文形式上和意義上的忠實統一,又為譯文賦予了時代性和先進性,更為準確易懂。 例如:
原文:港人治港
譯文:香港住民による香港統治
原文:敢于啃“硬骨頭”
譯文:硬い骨のような難題を果敢に解決し……
原文:“打虎”、“拍蠅”、“獵狐”多管齊下
譯文:「トラ退治」、「ハエ叩き」、「キツネ狩り」を同時に進め……
如上述例句中所示,“敢于啃硬骨頭” 在漢語中“硬骨頭”指的是難題,因此譯者譯為“硬い骨のような難題を果敢に解決”,即果敢地解決像硬骨頭那樣的難題。此類翻譯需要譯者準確把握原文語義,厘清邏輯關系,進行適當增譯。譯者保留了“硬骨頭”這一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詞匯,表現出極強的文化自信。
2.5 詞匯的比較選擇
原文:完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
譯文: 貧困脫卻堅塁攻略と小康社會の全面的完成という歴史的任務を完遂……
日文中有與中文“完成”相對應的“完成する”,但是譯者使用了“完遂する”,相較于“完成する”這一詞更顯鄭重,暗含“勝利地完成了”的語義,表現出譯者對中國脫貧攻堅所取得成就的自豪。
此外,中國的發展日新月異,譯者承擔著傳播中國故事的任務。因此,譯者需打造一種客觀形象與理性看法,讓外界看到更全面、更準確表述的現代化中國[11]。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里,從之前的“正しい道を歩みつつ革新”變成了“根本を貫いて革新”,字里行間無不展現著譯者堅定的文化自信立場。
3 結束語
通過分析黨的二十大報告這一中央政治文獻的日譯翻譯策略, 可以看出譯者團隊在翻譯過程中展現了鮮明的政治立場和態度。 譯者團隊選擇了更為堅定、直接、明確的語言表達,而不是沿用日語中委婉、曖昧、省略等語言表達。此外,譯者團隊還采用了附加外來語文注的方式,保留了具有強烈政治性、政策性色彩的關鍵表述, 并使用添加括號等表記手段解釋中文原文語義,體現出譯者積極與讀者互動。譯者團隊還注重保留典型的中文特色的原有表達,在翻譯過程中對邏輯關系進行了梳理和調整, 使譯文更加準確易懂。 同時, 譯者進行了詞匯上的比較選擇, 在日語中的漢語詞匯與和語詞匯都可表達源文本語義的情況下,選擇了更加正式、鄭重的漢語詞匯表達方式譯出,從而展現出對我國的文化自信。總而言之,譯者團隊在中央政治文獻的外譯策略上,體現了譯者對所譯內容的高度認同, 通過語氣和詞匯選擇、附加外來語文注、解釋性翻譯、梳理與調整邏輯關系等,展示了譯者的文化自信和人際立場。以期為推進我國文化自信自強、 構建中國敘事體系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法和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