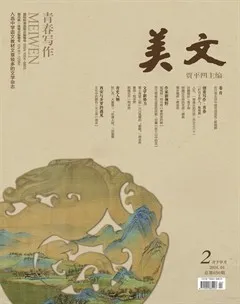人生,一場盛大的遷徙
百分之六十一
人們通常是如何定義“家”的?住所,家庭……但在筆者看來,稱一個地方為“家”更是一種對此刻生活態度、人生目標的認可。筆者通過對城市的印象,具象化地展示三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自己的主觀判斷。較為新穎地從個人感官的角度,從細節處描寫不同的城市風貌,表達自己對一種生活方式的看法,用選擇宜居城市的不易表現面對未來生活的迷茫。
筆者通過回憶居住過的三座城市,試圖尋找一個能成為后半生“家”的理想城市——抵達三座城市的距離,看似只是地理位置上的距離,實際上亦是筆者的現況與城市所對應的未來之間的距離。筆者用“遷徙”比喻更換居所的過程,試圖表達尋找理想中城市的困難,同時也強調自己擁有較為清晰的人生目標。
我是個不吝嗇將稍長期的住處都稱為“家”的人。因為這個字從嘴里說出來,總是順暢的、令人歡悅的。
從一個“家”到另一個“家”,遷徙者的路途艱難且漫長。和一座城市熟絡起來,往往并不比和陌生人做朋友簡單。衣食住行處處被滲透,新的環境,新的習俗,相距遙遠的城市差異往往大些。地域發展有快有慢,我們的長輩中很多人花了半生去完成從鄉村到城鎮的跨越——這件事曾經被我長久地忽略了,直到我的一位朋友談起:她時刻能感受到自己在大城市定居的義務,不是北京就是上海,最不濟也得深圳或廣州。為了保持家族的進步,為了給自己的事業一個更高的起點,她已經準備好一場遷徙。
那么我呢?我理想中未來的“家”,又應該在哪里?
我的前半生似乎從未面臨過這樣有分量的選擇,同時我明確地知道,朋友的路與我迥異。在模糊的意識深處,我對未來的“家”隱隱有一種幻想,那里集合了我所認知的全部美好景象,生活愜意而平靜。對于我的一生,它可以是一個階段性的開端,可以是一個令人滿意的落幕,也可以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落腳點。但我會依照“人生中不可錯過”的標準去尋找,直到我確信:是的,我就站在那里。
思緒的發散總有源頭,于是我計算起我的三處“家”與此刻坐著的地方的距離,順勢翻翻記憶里三座小城的聲音與畫面——或許擇取我愛的,撇去無法忍受的,便能組成一個完美的答案。
10355km:銅陵——科因布拉
一樹藍花楹,一條昏黃燈光照亮的小巷。是我對科因布拉最后,也最初的印象。
這是一座葡萄牙的小山城,蒙德古河穿過山腳,科因布拉大學的鐘樓聳立山頂,借由交流學習的機會,我在這里暫住了四個月。站在我的視角,整座小城猶如從上往下倒扣的一個冰淇淋,融化的一大半是甜蜜的椰子味,淌過的印跡便是居民日常聚集的范圍。酒吧、餐廳、商鋪沿著山路環繞一圈又一圈,我剛抵達時最熟悉的就是延伸到視線盡頭的石子路——盡管澳門的石子路不會鋪在山上,也不會造就科因布拉這種幾乎只適合步行的交通。
這里繽紛的顏色與澳門徹夜不熄的彩燈不同,大面積的暖黃和粉藍是陽光下觸手可及的溫度。我在的時候恰是春夏兩季,滿目的綠樹和樹上掉下來的爛橙子,沒有許多花,可空氣里總是清新怡人的味道。透過教室的窗能望見河面與河對岸的草地,波光瀲滟映照著長椅與白鴿,偶爾還會有一兩只沿著水飛來的海鷗,在圣克拉拉大橋的旗桿上落腳。深紅色的房子們很明顯地抱成團,然后粉色一列,白色一列,屋頂各有各的模樣,站在法律學院的廣場邊緣可以盡收眼底。
公寓通往大學的路遍布著名景點,拱門、雕塑、小巷、教堂,我背著書包爬山累得氣喘吁吁,旁邊導游領著旅行團串起幾百年前的風景——世界各地的游客每天都不一樣,年紀各異,語言各異,看他們真的比看景色還要有趣。城里的鴿子也和河邊不一樣,全部是灰撲撲的,無處不在。大部分餐廳室外的桌椅上方都撐著傘,很難說不與它們有關。
學生們經常光顧的小酒館開在狹長的甬道中間,正是最陡峭的一段坡,午后對著下陷的大門支起兩張小木桌,便只剩一人側身走過的寬窄。小桌齊我的膝蓋高,擺著隔壁果茶店的廣告,客人約等于是坐在臺階上,背靠另一側建筑淺藍色的外墻。陽光越過兩邊的屋頂把金色傾倒進巷子里,木板寫的餐單在門框下晃來晃去,應和著常年播放的流行歌曲。
下課以后走這段路最歡樂,一是下山遠比上山輕松,二是傍晚能遇見的居民一般多于游客,我對探究異國他鄉人們的生活還是滿懷熱情的。當地食材的單調由搭配和環境彌補,歡聲笑語中一路的遮陽傘下座無虛席,賣藝人坐在街邊高聲唱著法多,大家都在盡情享受今天最后幾個小時的日光,包括那些咕咕亂飛的灰鴿子。科因布拉人擅長享受生活,在這個常住人口不足十萬的小城里,高級餐廳約摸有上百家,算上酒吧酒館則更多。葡萄牙的酒出名,無論是餐前餐后還是搭配甜點,葡萄牙人總能想出理由來上一杯,他們甚至連咖啡都要搭配紅酒。而且在科因布拉,葡萄酒不是一種越出名越昂貴的特產,在五百克番茄要四歐元的連鎖超市里,一瓶波爾圖的白葡萄酒只需要兩三歐元。即便規模最小的便利店,也會有一整個貨架的葡萄酒可供挑選。酒精同陽光、河水一樣,給予科因布拉人充沛的幸福感。
然而在夜幕籠罩這座城市后,酒的氣味便顯得瘆人了。
夜晚的科因布拉褪去了它的溫暖,所有聲音聚集在寥寥幾個路口,大片的街巷蒼白而靜謐。這當然無礙于它的美。月光均勻地灑向教堂與城堡,從山頂到山腳不會有一處遺漏。夜間偶有進出車站的火車平行于河水,和著汽笛聲一列一列亮起燈,甚至成了一景。哪怕是街角隨意的涂鴉也有一盞路燈點綴……只是這時候這座城市并不屬于它所有的居民。它屬于流浪者,屬于買醉的常客,屬于比自由“更加”自由的那部分人。
這些問題科因布拉人是不介意的,驚慌失措、小心翼翼的只會是來山頂大學求學的學生們。四個月時間,足夠我初步認識到他們毫無理由的積極快樂。他們擅長對自己友好,即便發脾氣也是毫無負罪感地吵嚷——總之錯的不會是他們或這個世界。這座城市沒有外人給的焦慮,似乎很少人在乎物質條件的缺失,他們只需要白天源源不斷的陽光,便能夠汲取著蒙德古河的河水肆意生長。
可“他們”終究不是我,我始終不曾擁有一顆像“他們”那樣,充盈滿足感的心臟。強行留在這里,“他們”的自由即是我的枷鎖。
不僅在夜晚,那種明媚的、純粹的歡樂,時時刻刻都令我自慚形穢,刺痛我的心扉。不留心經過被占據的墻根或屋檐,陰影中的人令我生懼,我的出現卻令他生趣,那么到底誰更像是蜷縮在角落的流浪漢?
或許長久地住在這里,終有一天我能夠學會,像熱愛陽光一樣熱愛自己的每一次呼吸,或許吧……我無法肯定。
這自然不是誰的過失,一個填錯位置的正確答案,它就是定格在那里了,沒辦法勉強。
1302km:銅陵——澳門
從小長在內陸的我曾有過不切實際的設想:所有被海洋包裹的城市都是時刻響徹天然的浪濤聲,風里卷著沙灘的細沙,雨落在舌頭上也是咸一些。后來出去游玩過幾回,也知道了并不盡然。風會大些,雨會烈些,行道樹的枝丫葉片會少些。只澳門仍是尤為不同——它太小了,四十五平方公里,小得和旁人根本沒什么可比。它的土地沒有物產,它是伸出手,被托舉著長大的娃娃。即便是四面環海的島嶼,也不會比它更像是大海攥在掌心的一枚釘,閃閃發光,不斷掙扎出新的土地來。
我的大學坐落在澳門的轄區,卻不屬于澳門的土地,相隔一條隧道讓我對澳門少了許多熱情。我雖也來自內陸極小的地方,卻習慣不了本島的擁擠與嘈雜,氹仔更是連成片的高堂華屋,剛入學那一年,學著坐公交車都讓我戰戰兢兢。校外的每一處生活場景:超市、商場、醫院,全部像是地圖上標注的打卡點,相互連接的路浮在天上,找不到把我和這座城市牢牢勾連在一起的枝節。
三年里我摸索著走近它,一閉眼從天上跳到堅硬的石子路上,打了好幾個滾——老城區海浪形狀的黑白石子路,硌得我渾身疼。不過我仍需要感謝這些街巷,它們承接過我的笑聲,容納過我的信口謾罵。如今離別近在眼前,我似乎得到了重新審視這座城市的機會。
澳門,明明處處依附外界輸入的資源,可它偏有一種獨立的風格,奔流不息的水點亮日夜通明的燈,在天幕下極其渺小但極其輝煌。沿著學校的行道樹仰頭望過去,深夜的天是灰的,光扎進去就冒不出來。澳門從不會低頭看,從不缺人把花團錦簇捧給它,捧著它——只要人人都想往這兒來,它的盛況就永不落幕。
許多人眼里,我如今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如此繁華熱鬧的城市,日子偏叫我過得一成不變,假期每每窩在原地一動不動,多少顯得乏味。這同樣是我耗費三年才熟悉這城市的主因。可我心里知道,這便是我生活最舒適的模式下,在澳門所需的全部——過了橋隨便捏出一個點,站住了隨便轉一圈,往百分之七十五的方向走,一個小時以內我都能走到海邊。走到海邊,沿著熟悉的路,我會經過味道很不錯的海鮮排檔、名聲在外的蛋撻鋪子、能帶我回到書院安然躺下的公交車站……我有最喜歡的手撕雞店,清楚哪家超市外賣水果最新鮮,哪一家的便當偏甜偏辣……
聽上去接近完美了,可是留在這,依舊不可以。
因為澳門的褊狹和繁華都不會改變,這兩種特質將它鑄就成如今的模樣,成為它的本質,而為著這本質蜂擁而來的人與我注定是說不到一處。面對大海,它到底只是一枚釘子,沒有基石,沒有依托,不可能無休止地填出陸地。等釘子完全扎進海里,我追求的寧靜早晚會陷入擁擠的困境。在短暫的時間里,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去認識它,聊以自娛尚可。至于將未來寄托在此……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啊,哪里也不乏更遼曠的景色風光。
都說澳門得天獨厚,可是如果那些五彩斑斕不是屬于我的,它們與枯燥無異。如果我自認能夠在平庸中期許驚喜,那么平庸至少不是負分的答案。
0 km:銅陵——銅陵
菊科植物濃烈的氣味充滿鼻腔,清新、醒神,混著白雪融化時候的冷風灌進圍巾和帽子的縫隙里,讓人匆匆加快腳步的同時不自主地低頭去尋——恰好幾步路走完,待視線落到雪壓著的幾叢枯黃支著嫩黃,這氣味也便隱約消散了。風成片地撲在裸露的皮膚上,尤其是臉頰,平時最金貴的地方不加遮掩,寒意直刺進血肉,微微碰著骨頭。地上的花倒是無所謂金貴不金貴,自然枯萎,自然零落,可惜這些并不是田間野地的產物,只是在街頭的行道樹下整整齊齊種著,略顯突兀。
我一向喜歡菊花,一時不記得這條路夏天栽的什么花。又過一條街,相同的氣味仿佛正凝結在街心有了形狀,懸在一人高的位置,經過便忽視不得,遠了便尋不見。
這就是銅陵的優勢了,倚著長江的南岸,四季分明,冷也是斷斷續續的,浸不透我脆化的骨頭。耳畔雪化的聲音,由高低晃動的樹葉作為載體具象了,這聲音在澳門是聽不見的。
一日雪,一日晴,這時候的天地總是格外安靜。江南的小城,山水富足,人口不多不少,似乎擁有我所需的一切——然而它偏偏是我的故鄉。
安徽的溫度積不起鵝毛似的雪毯,留得住花草,就藏不住底下枯腐的樹葉。大多是杉樹和樟樹,踩踏多了,葉片會凍在半融化的雪里或攪進一片鞋底的泥水。臟污、濕滑,但這偏是行人、季節抹不去的痕跡,是這座小城無數件平凡瑣事的縮影。我在這里平緩地生活了二十年,時間沁入每一處角落的記憶,從長度延展到深度。
故鄉,故鄉,我待它的情感猶如糾結纏繞的藤,干枯粗糙的皮覆蓋住活生生的內在。這里的土地擁有我潛意識里最深的本能,直接反映在細微的口音變化,它淡然自若地等著我,抓住了我,沒有辦法躲避。父母的嘮叨、親戚的應酬、朋友的攀比……一個人成長的痕跡把我捆在“子女”“晚輩”“同學”的位置上。無論在故鄉以外我是誰,回來了,就得被迫直視從小到大幼稚糟糕的經歷,不得不擠出微笑面對所有自己試圖掩蓋的錯誤,和記得它們的人。
于我,銅陵是一處“本應該靜止”的地點。我希望它前面二十年的改變都定格在我遠行的那一天,永遠等著我回來,永遠作為我記憶封存的載具,把自身全部拋下……這當然是妄想。離開四年我終于發覺,正視它的變遷原來很艱難,而正視這種變遷勢必不會停止的事實則更加艱難。
故鄉就是這樣,是你必須離開的、必須忍耐的、必須牽掛的。某種程度上它和一位既年老又年輕的親人并無區別,正如同我那顆不斷被現實磋磨的、放不下的本心。在養育我身體的土地上長出這樣一顆心,我不意外地夢想著有一座類似它的城市能容我繼續屬于我的生活。越像它越好,卻不能是它。
因為在故鄉,我除了“我”之外擁有更多的身份:我是母親的女兒,爺爺的孫女,老師的學生……我的故事擺脫不了既定的開頭,且難以走出譜好的基調。留在這里,故事必須從根系開始枝繁葉茂,每一段銜接的邏輯都得清晰明了——完完全全展示給別人。所以我選擇逃跑。
或許將來我終會回到這里,由離開的那些年組成無需解釋的答案。
……
三座小城,我從一座走到另一座,又走向下一座……距離跨越半個地球,遷徙者也走到了大學即將畢業的十字路口。
10355公里之外,到了學期結束的季節,首都里斯本的藍花楹稠迭連綿,在科因布拉我記得的倒只有一株,正擋在巷子口,是回公寓的必經之路。樹下有一家生意紅火的甜品店,蜂蜜香和堅果香每天勾著放學下山的我。但是我怕太胖也太貴一直沒去吃過——直到離開的前一天下決心去嘗,卻發現店主周末休息。
我的人生軌跡留有許多這樣的遲疑,十八歲前我按部就班,仿佛總害怕時間虛度了,急忙去完成所有任務,追尋認可和成就感,相信為了最終的目標拋棄一些微不足道的愿望不算什么。然而漸漸地,我開始力不從心,我的愿望和現實爆發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可怕的是我已經過了逃無可逃的年紀,擺在我面前四通八達的全是退路……違逆著明明朗朗的那條大路,它們的終點淹沒在陰影里。
我知道中間有一條是我追求的捷徑,也知道行差踏錯的代價。高昂的試錯成本,讓年輕的我左右搖擺,長輩的意見毫無意外傾向保守,可是我的心臟僅僅是靠近自己選定的方向都會躁動——它在捕捉另一個和我契合的正確答案,鼓舞遷徙者勇敢地前進。
1302公里看起來近了許多,澳門和銅陵也均分了我大學四年大部分的時間,我跨越半個中國像候鳥一樣往返,聽過許多夸贊澳門是個好平臺、好階梯的話。許是城市都不大的關系,我其實常常拿它們相互比較,旁的差異數不勝數,偏在當跳板這件事上實屬異曲同工——一個往國外跳,一個往上海、江蘇、浙江周邊跳。仿佛每個階段的人都勢必有如躍遷的原子那樣神奇,過程是觀測不到的,結果是絕對顯著的。
人生只有一次,外人盯著每步的高度,不知道維持現狀已經用了你許多努力,雖然不一定是拼命,可一呼一吸也擔上了重量。“已經做到的事情”是沉沒在遭受的埋怨中的,人們仿佛只能為自己滴著血達到的進步受鼓勵。我深感這不應當,卻不得不承認自己是短視且被懶惰俘虜的性子,本質上我厭惡一切要拼盡全力去做的事情……恰逢支撐我在正踩著的這條路上走到如今的動力,不知不覺地自燃殆盡了。我獨自一人的遷徙,目標掛在天邊,除了我的一顆心沒有其他任何助力。
我后半生的“家”啊,只存在于我幻想中的答案,你究竟在哪里?
遷徙者總要經歷這樣的尋覓,由遠及近,再重復離去。有些找到合適的落腳點,延綿出新的故鄉;有些兜兜轉轉,一生漂泊如浮萍仍拒絕扎根;有些被外面的風吹疼了,吹傷了,索性回到故鄉去……這不僅是對一片土地的感情,更是對自己人生的認知,對一切選擇的肯定與接受。
不管你在這個瞬間做了什么樣的決定,留下或離開,開始或結束。請相信,人生是一場不會結束的遷徙,長路漫漫,隨時都可以回頭——所以無需懼怕,邁步,去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