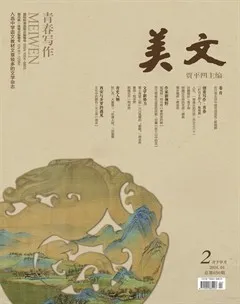自幽微處
高子堯
文章已經構思了很久,只是一直沒有機會將它訴諸筆端,每次動筆寫下的句子耐不住咀嚼,立意也很幼稚,像是沒有骨架支撐的血肉一樣。我只得暫且擱置,耐心等待。今年八月,我坐上前往香港的飛機,從一個塞北小城到國際大都市求學。剛到香港時,我總是小心翼翼地模仿當地人的一舉一動,盡力隱藏所有情緒,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社交。與外界幾乎隔絕,這驅使我窺視內心幽微處。每當夜幕降臨,我躺在床上回憶著故鄉。一千九百多公里的距離沒有模糊我對故鄉的印象,反而在夜復一夜的回憶中愈加清晰,甚至發現了許多被我忽略的地方。許多人的身影在眼前閃過。我想捕捉他們:遷徙者、堅守者、開拓者。我想記錄他們生活過的地方,我想給他們在后人的記憶里留下一席之地,連同完成我為故鄉寫作的未竟的心愿。作為一個故鄉的書寫者,我并不在故鄉,我沒有“在場”的經驗,可能有失真實,但卻獲得了全新的角度。我更加自由地觀察故鄉的生活,更加自由地回憶故鄉的人和事。就像是《樹上的男爵》中的柯西莫,他選擇生活在樹上,才能看清自己的故鄉。這是一個完美的時機。我感到一股難以抑制的情感涌現,這些記憶來自于我的內心幽微處。
草原上青色的季風推著我的年輪,一步步向前,我總是抱怨能不能再快些、再快些,但當我感受到潮熱的海風時,回過頭它早已消失不見,只有一絲草腥味在空中飄蕩……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帶著故鄉的風,這風養育我們長大,在它的懷抱中我們像麥子一樣,抽節生長。那些日夜不息的青色季風,在我的內心呼嘯,雕刻出我的過往,預言著我的未來。我的故鄉。生于斯,長于斯。
祖 輩
就是黃河幾字灣下的那片土地,五百多年前,我的祖先從關中來到這里。農耕文化的故土情結猶如種子撒滿了草原。他們開墾出農田,在水草豐茂的地方扎根。養牛羊、種糜子、打籬笆、砌灶臺。男人們用鋤頭鋤出糧食粒粒,巧婦們用針線織出布衣件件。干旱少水,那就打出汩汩清泉。黃沙遍野,那就種出片片綠林。糜子熟了做成糕,寓意著步步高;牛羊大了牽去集市,賣個好價錢。過年吃一頓餃子,象征著日子越過越紅火。在無垠塞外,我的祖先們憑借著有力的雙手和堅定的信念,把困苦的生活過得有滋有味。他們無疑是堅強的,在青色季風吹拂的夜晚,他們也會向南邊望去,關山難越,阻擋不了他們對故園的凝視。那時候的夜空,像童話故事里描述的一樣澄澈透明。浩瀚群星,是他們內心的鏡子。他們從山里走出來,群山回唱賦予他們隱忍與堅毅,到這片塞外曠野,季風滋養他們寬廣與包容。這是他們的雙城記,從大山到草原,他們像糜子一樣,被帶到塞外貧瘠的土地,執著地生根、發芽,拼命拱出黃土,用力吸收太陽和雨露的饋贈。等到長出莖葉,在青色季風吹過之時,用力捕捉生命的歡愉和躍動。故事永遠也講不完。我的祖輩,他們是那批開拓者中最為勇敢的人,祖先將我們從大山帶到草原,祖輩將我們從鄉村帶到城市。我的祖輩懷著巨大的決心走出那片世世代代耕種的田地,放下開天拓地的農具,離開故土,就像布恩迪亞家族一樣,孤獨是他們的命運,離開故土是我們的命運。祖父的故事也是如此。
祖父50年代生人。在與我相仿年齡時,踏上求學路。后來,祖父多次用自豪的語氣回憶。他的聲音,讓我得以沿著記憶河流而上,在一條土路上找到我的祖父。那是一條幾乎不能被稱之為路的土路,只是被行人用腳踩硬的泥土。沒有標識,沒有歇腳的地方,祖父沿這條路走了三天,卻如同走出了時間。我常常打斷祖父的回憶,好奇那些被孤獨無限拉長的夜晚,好奇那些扭曲的天空。在那條土路上,祖父背著油布包,背負著后輩的命運,在灰色的記憶里一直走下去。我看到祖父徘徊的影子,我在想,如果祖父掉轉頭,沒有走下去,我的命運又是如何?祖父緩緩轉身,用悲哀的眼睛看向我,毅然走進前方的黑暗。祖父沒有高瞻遠矚,沒有聰敏過人的頭腦,只有同千千萬萬農民出身的,對改變命運的人一樣的渴望。他們不是草原上的馬或鷹,而是荒坡上那挽木犁的牛,實實在在地扎根土地。我的祖輩,偉大遷徙者的后代,血液里仍然回響著大山的轟鳴,腳下踩的仍然是厚實的黃土。祖輩的故事不會停止,在人類文明危如累卵之際,正是他們拯救風雨飄搖的文明。祖父在陰冷的教室里,將一塊又一塊煤投入爐中,仿佛燃燒自己。爐火騰騰,火焰躍動,灼燒空氣,生出圈圈波紋。祖父不斷靠近,嘴唇抖動發紫,他像一切偉大的冒險者一樣,不斷深入未知,感受恐懼與好奇的共同支配。他們賭上一切,人類文明因未知的誘惑而前進,祖父火中取栗一般,改變了家族的命運。祖父回頭的注視,不是猶豫,不是徘徊,是同既有命運的漫長告別。
故鄉不斷擴張,我們穿梭于山與河,但它的內核卻在迅速坍塌。故鄉的哀鳴不再回蕩,盲人演奏的二胡被喇叭聲撕扯。他常在暮色四合時出現,茍延寄身在短暫的暮色中。二胡的聲音不斷穿梭于生死邊界,充當陰與陽的擺渡人。那邊的亡魂順著指引,尋向這一邊的家人,在風中徘徊,等待生者的呼喚。我問起他的生活,他將二胡拉得更急了些,于是,風聲又大了些,我想到了我的曾祖母。
我的曾祖母是一個堅強的女人。丈夫過早離世,她獨自撐起養育五個兒女的重擔。在動蕩不安的歷史中,她像一個嫻熟的水手,把著風帆,在海上航行。艱苦的生活養成了她精明能干的性格。前半生的操勞,換來后半生的四世同堂。打我記事以來,曾祖母總是將頭發梳得齊整,衣服穿得熨帖。衰老的容貌沒有磨平她眼中的堅強,反而讓這一份韌勁更加動人。在相片中,曾祖母坐在最中間,她的一雙小腳陪她行走一生。她是這片土地上最偉大的堅守者,同所有相仿年紀的老人一樣,出色地完成故鄉的囑托,化為大地的一部分。我不清楚,葬禮埋葬的是一個孤獨的靈魂,還是一段不曾言說的苦楚。在曾祖母的葬禮上,我看到紙錢燃燒產生的青煙升上天空。煙塵帶著我們的思念,向遠方飄去。當我后來到曾祖母的墳塋,周圍植被繁盛,野花遍開。那些煙塵,并沒有消散在風中,而是來到這里。思念也如草木一般,生生不息。棺槨中,曾祖母面容輕柔。父親說,曾祖母走得很安詳,沒有痛苦地掙扎。在時間的漩渦中,我的記憶不斷閃回,我記起了那些時日。莫失莫忘,我的祖輩這樣教導我。我仍然記得她住的房間,淡黃色陽光如何在她臉上的皺紋流動,紅瓦窗沿的燕子如何啼鳴,青石板上的野草如何晃動。這些景象,在我生命中,給予了我長久的溫暖,也給予了我曾祖母坦然接受生命枯萎那一刻的力量。那些離開我們的人,沒有消散在無垠的荒野,而是融入了時間。時間不斷地穿梭,我們也得以與逝去之人一次又一次重逢。我們帶著思念,仰望天空,雙腳用力踩著這片先祖堅守的土地,我們頑強地生活,奮舟而上,不被潮水帶走。在許多年以后,曾祖母會以夢境的形式與生者重逢,在那夢境中,流水不再流動,野草不再晃動,飛鳥不再飛翔,我們在這一邊看著曾祖母,她在另一邊看著我們,中間隔著跨越生死的屏障,唯有故鄉深遠的召喚,穿屏而來……
孩 子
當我再一次在草原上看到落日時,我無比期望它不會再次升起,認為自己走出了故鄉,走出那片廣袤無垠的草原。而遠方的群山依舊散發未了的余韻。
事實上,沒有人能夠走出故鄉,我也沒走出那片草原,它過于廣袤,足以讓每一株草處在故鄉的中央。所有構成我身份共同體的故事,都發生在這片土地上。我們出生,成長,相愛,死亡。憑著腳下細微但致密的聯系生生不息。我在四歲的時候第一次見到草原,看到薄霧中飄搖的水汽。它們指向群山那邊。悠揚深遠的回唱在群山之巔激蕩,而那一邊常常闖入夢境。在某個月亮凍結的夜晚,借著堅冰一樣的、剖開肋骨的光,視線穿透山脊。河流沿山而下,在另一邊開疆拓土,孕育了起伏緩和的小丘。綠色的火焰在坡頂燃燒。大地每隔十五分鐘震動一次,古老的力量從地心涌出,在平緩的河流中濺起水花,凝結成群星。而在河的盡頭,偌大的湖不斷分娩日月,她以溫暖的姿態接納了我,賦予我輕盈的翅膀。
祖輩教導我,莫失莫忘。故鄉的肌理和呼吸,早已被我所銘記。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寫道:“組成這城市的并不是這些東西而是它的空間面積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系:燈柱的高度、被吊死的篡朝者擺蕩的腳與地面的距離;系在燈柱與對面鐵欄之間的繩索、女皇大婚巡行時沿路張結的彩帶;柵欄有多高、偷情的男子如何在黎明時分躍起爬過它;檐槽的斜度、他閃進窗子時一頭貓怎樣沿著檐槽走過。”
我們的城市不是由宏偉的建筑,無限延展的馬路或者是日夜轟鳴的工廠構成,而是由昏黃路燈下獨步前行的陌生人,路邊販賣食物氤氳的熱氣和街角的理發店構成。我們的生命體驗和記憶,構成了城市,而城市在不同人眼中也呈現出千姿百態的面貌。
我的記憶塑造了我的城市,它總是從饑腸轆轆中蘇醒。住宅樓底下的拉面館喂飽了早晨那些異常饑餓而又缺乏耐心的疲倦身體。“老板,來一個二細,不要香菜,蔥花辣子多放。”食客與老板之間總有心照不宣的默契,老板揮一揮手,食客轉過身去,坐在老位置上。接一點熱水燙一下瓷杯。拿起桌子上的水壺,一揭蓋兒,棗香四溢。微傾壺身,朱紅的棗茶氤氳著熱氣,漾開在杯盞。啜口棗茶,先把胃暖起來。甘甜的味道順著茶水,幾乎是涌上了舌尖,滋潤了干燥的口腔。吃拉面,茶葉蛋是必不可少的。一旁的鐵鍋咕嘟著,誘得人食指大動。趁著茶蛋滾燙,手忙腳亂地剝開雞蛋皮。奶白色的蛋清彷佛被氧化似的泛起了棕色,茶葉和香料的濃郁,像一道道印記,織在蛋清上。這邊食客準備著,那邊老板也沒閑著。取出一塊面團,發酵一晚的面團潔白光滑,隨手揉搓捏轉,面團變成了均勻的長條。拇指捻動,像是在拔瓶塞,長條變成了一個個小劑子。棉麻布噴上點油,蓋在面劑子上,餳面!焦急的食客已經向后廚張望了,老板也很識相,回過身擰開燃氣灶,把煮面的水熱上。揭開棉麻布,揮手撒一層生粉,把面劑子在案板上揉勻了面粉,像銀元寶一樣。老板用手心一壓,面劑子攤開,取一搟面杖,邊攤邊搟,到面劑子成一長扁條后,把面條對折,再攤開,對折,再攤開,如此反復數次。鍋中的水慢慢沸騰,冒出水汽。長條狀的面劑子在手中飛舞,拉長后要螺旋對折。雙手套在面上,面團韌勁十足,老板一抻一拉,銀元寶變成了銀絲線,后廚變成了戰場。面條一提一摔,在面板上啪嗒作響,好似戰鼓手,擂響鼓鼙;銀白色的面條被他舞得呼呼生風,猶如沖鋒在前的旗手,將旗幟昂揚;但也像俠客,把面條灑進鍋中,如刀劍收鞘一般瀟灑。抄起漏勺,在水中攪動,當煮面的水涌起,澆一勺冷水,如此重復,到第五次的時候撈出面條。這時,把鹵好的牛肉鋪上幾大片,扭頭用大勺舀湯,自下而上用牛肉湯沖淋,濃香四溢。放兩片水靈靈的白蘿卜,打上兩勺青花瓷碗里的油潑辣子,撒上一把蔥花。一清是湯清,二白是蘿卜晶瑩剔透,三紅是油潑辣子,鮮亮紅透,四綠是蔥花,五黃是面條黃亮。食客迫不及待,挑起一筷面條,往口中送去,棗茶的預熱讓面香更為凸顯,蔥花的辛味讓味道更加立體。泡熱泡軟的牛肉,飽蘸湯汁,肉香四溢。無須多言,食客的沉默就是對這一碗面的贊許,而老板猶如高人一般,看著食客狼吞虎咽,自己卻吹開水壺里的茶葉,慢飲一口。北方的冬天,天寒地凍。凜冽的北風吹緊了皮膚,繃在骨頭上,顯得人憔悴。而那永遠散發著熱氣的澡堂子,便是溫柔鄉了。澡堂子是北方人對于公共浴室的別稱,讀起來讓人心生愉悅。推開木門,熱氣氤氳,打一個哆嗦,身上的寒氣就抖了下去。不管你在外面穿的是貂皮大衣還是羽絨棉服,在這里,每個人都赤條條、光溜溜,都是一副肉身。中間是一個大池子,兩邊各有一個小池子。中間的溫水池,最是舒服。當熱氣蒸進每個人的血液,血氣上浮,整個人輕飄起來,臉上又浮現出坨紅,繃緊的皮膚逐漸松弛下來。沒泡過澡的人像一個稚氣未脫的小孩寫出來的字,緊緊巴巴,顯得局促匆忙;泡了澡的人,果真如書法家寫的“人”字一樣,一撇一捺,舒緩自如。這一池溫熱的水讓所有人在這里放下戒備。甚至品味出一點無欲無求、平靜自然的佛學之意。血氣上頭,又難免高唱幾句,老頭們臉上敷一條毛巾,扯開嗓子,叫吼了幾句老戲,曲調荒腔走板,但有誰在意呢?咿咿呀呀的聲音更讓澡堂里面多了幾分外面那個天寒地凍的世界沒有的縱情。搓澡師傅是每個北方澡堂的標配。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不同口音,依仗這門手藝,在北方的小城里養活自己。聽著各省的口音,我想象著他們的故鄉和經歷。東北口音抑揚頓挫;山西方言古重平實;川渝口音俏皮饒舌;湖南口音霸蠻直橫……一聲聲吆喝里,搓澡師傅套上搓澡巾,胳膊一伸一縮,腰身一直一欠,雙腿一搖一晃,水汽蒙在他們的肌骨上,在燈光照射下,晶瑩地閃著。手臂上的肌肉一張一縮,青筋一隱一現……當走出澡堂,一身的疲憊和憔悴早已洗去。身子里就像有一個火爐,暖意由里到外散發開來。就算是冬天的北風,也沒有先前那么凜冽了。
故鄉的風將我養育成人,城市是空曠的,沒有很高的建筑,也沒有密不透風的樓房,我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躍行于大街小巷。那狹窄的巷子里承載了我的過往,沿著崎嶇不平的紅磚路,我再次踏入記憶的河流。小巷不怎么整潔,兩邊卻開滿了商鋪。啞啞就在巷子門口修補自行車胎。他是一個啞巴,沒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只是大家都叫他啞啞。啞啞身形矮小,有些佝僂,還是一個跛腳。他總是坐在陽光下面,笑瞇瞇地補著車胎。補一次車胎并不貴。啞啞有時候看到是一個小孩,便擺一擺手示意不要錢。小孩們當然也不會虧待啞啞,總是會用家里人給的零花錢,買幾塊糖,遞在啞啞手里。啞啞高興地剝開糖衣,潔白的奶糖在他粗糙的手心躺著。混著陽光,他便一口吃下去。當陽光綻開時,他就咧嘴大笑,引逗著小孩們一齊笑著。啞啞有一條狗,每個陽光明媚的下午,一人一狗就會坐在巷子口。啞啞坐在折疊椅上,而他的狗就蜷縮在腳邊。陽光毫不吝嗇地布撒在他們身上。啞啞微笑面對太陽,周圍的空氣也變得柔軟起來。他手握著工具,飛快地補好車胎。在空氣中泛起晚意之時,回到他的舊屋子。一個簡陋的棚屋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太過促狹,但啞啞似乎很知足。啞啞從來不羞于向我們展示他的匱乏,也從不吝嗇于向我們施舍他的富足。很多新奇的小玩意被他變魔法般的制造出來。他可以和小孩蹲坐在門口玩一下午,也可以安然接過大人遞的一支煙,有時會走進某一個小區的麻將房,老頭老太們會讓啞啞玩上幾圈,他也會欣然接受。他和我們并無兩樣,我們也不把他當作不一樣的人。啞啞總是坐在巷子口,看著街上的車來來去去,看著路上的人走走停停。他從來都是對著陽光微笑。后來我再也沒有見到啞啞,舊院里的老人大多衰老病死,離我們遠去。原來的住戶陸陸續續地搬走。當我再次去回憶巷子門口那個修補車胎的啞啞時,這段記憶卻越加模糊,我只能記得他對著陽光微笑,在某一個午后,帶著他的狗,剝開一塊糖,在嘴里咀嚼陽光……
現在,我在南國回憶故鄉。窗外吐露港霧氣迷蒙,游船劃過灰色的水面,泛起白色漣漪。遠處青山褪去了顏色,只剩簡單的線條和濃淡不一的墨色。極目遠眺,目光在某一處戛然而止,仿佛卷入了無盡的水波。海濱路旁的棕櫚樹擺動它寬大的葉面,在葉子的邊緣,生命逐漸褪色,海風把枯敗之意沾染,將凋落的訊息傳播到遠方。當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最適合回憶。讓意識隨意流動。舊日的時光掀起一片漩渦,瑣碎的片段在流動的意識里不斷重組,變形,讓暖意和溫情短暫地隔絕南國冬天的陰冷。我推開窗子,咸濕冷冽的海風扯碎了心中蕩起的漩渦。它在提醒,我不在故鄉。故鄉的風帶著泥土和牧草的清香,而香港的海風,濕潤得似乎要將整個人包起來。最近的日子,朋友們都在說故鄉下雪了,我有一瞬恍惚,仿佛又回到了那個無憂無慮的日子。拉面館永遠散發著陣陣麥香,而澡堂里熱氣氤氳,巷子口的啞啞和他的狗,對著陽光微笑。我們都富足而又快樂的生活著。記憶就像一座山,離得太近就什么也看不見,當最終遠去的時候,才能看到山地全貌,但再也找不到來時的路,只剩下一串充滿猶豫、迷惘和彷徨的腳印。有的人原地踏步,有的人誤入歧途,而有的人一路向前……
再一次看到朋友分享的雪景,我發覺到,作為一個亞熱帶城市,香港是不下雪的。昨晚在維多利亞港看到中環的高樓,燈火輝煌,周圍人聲鼎沸,天空飛過一只鳥。我靠近護欄,海水吞噬噪音。我只聽到海浪拍打礁石后化作泡沫的一聲微弱的嘆息,轉瞬即逝。對岸的LED燈反射在海面,波浪涌動,攪碎了幻影。戀人在擁抱接吻;月亮若無其事地懸掛在天空;尖沙咀的街道上車水馬龍;游人興奮地談論著城市的繁華;而遠處的太平山寂靜無聲。我別無所求,只希望香港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