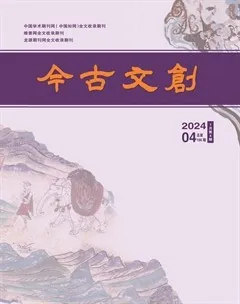瘋癲: 洞見生存本相的符碼
【摘要】本文通過對余華小說《一九八六年》中的瘋癲敘事進行分析,發現其獨特之處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內容上余華以“瘋癲”作為解讀世界的符碼,不僅將“瘋癲”作為重構歷史的起點,揭示了歷史的非理性真相與暴力本質,還將“瘋癲”作為人性暴力欲望的敞視點,從而發現了隱藏在人性深處的本我暴力欲望和人類群體中的精神暴力現象,完成了對人性本惡這一主題的論證;二是敘述上采用了二重奏式的敘事方式,在文本中主要體現為暴力書寫的“外冷內熱”和敘述場面的“輕”“重”交織這兩點。
【關鍵詞】《一九八六年》;瘋癲;暴力;二重奏敘事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4-001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4.006
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大概是余華思想上最為混亂的時期,既有價值觀念的顛覆和日常生活經驗的虛偽性導致他一度對世界的真實性產生懷疑。在這種懷疑主義眼光的審視下,余華看到了被秩序、常識、文明包裹起來的理性世界背后所展現的另一種真實——非理性。在強大的非理性力量面前,理性總是顯得束手無策,“因此我們置身文明秩序中的安全也就不再真實可信”[1]167。這種全新的發現既讓余華深感不安和疑惑,也給他精神上帶來一絲探索的興奮與沖動。以非理性為坐標去測量世界,得到的將是一個全新的生存維度:在這里,“瘋癲”——作為非理性的極端表現形式——成為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和演繹真實的唯一工具。當“瘋癲”成為余華重新解讀世界的符碼時,一切日常生活經驗與邏輯秩序都面臨著被顛覆、架空、消解的命運,隨之而來的是非常態暴力景觀的呈現與崛起。這種世界觀的突轉造成了余華與現實生活之間的緊張關系,然而卻使他意外地迎來了寫作上的“革命”,并“自由地接近了真實”[1]165。這一時期的余華創作出了《現實一種》《河邊的錯誤》《一九八六年》及《四月三日事件》等作品,其中《一九八六年》以恣肆的想象和冷酷的文筆達到了對“瘋癲”的極端呈現,成為余華瘋癲敘事的經典之作。
在《一九八六年》中,余華用“瘋癲”撕開人性與歷史的虛偽面紗,對現實世界進行冷靜地解剖,并將其混亂、血腥、殘暴的內在肌理暴露在我們面前,從而使我們得以探知生存世界的另一種殘酷本相。
一、瘋癲:重構非理性歷史的起點
余華在《一九八六年》中以“瘋癲”作為歷史想象的起點,對歷史進行了顛覆性的重構,從而揭示了歷史的暴力本質。小說中歷史老師年輕時迷戀刑罰研究,在后來的特殊年代因為一張記錄古代刑罰的紙條而遭到迫害變瘋,瘋后的歷史老師從在幻覺中對他人實施刑罰轉變為對自己的肉體進行自戕,最終淪為了刑罰的獻祭品。
古代刑罰是維護權威的一種強力手段,是一套精細的馴服肉體的技術,也是一臺制造合法暴力的冰冷機器。“酷刑是以一整套制造痛苦的量化藝術為基礎的”[2]37,它建立在肉體敏銳的知覺功能上,通過殘忍地折磨肉體制造一種恐怖感,以達到對受刑者的懲戒作用。歷史老師在大學期間進修的是歷史專業,那么學習的應該是官方書寫的正統歷史,但他卻唯獨對被官方歷史所隱藏遮蔽的古代刑罰制度感興趣,這種狂熱的興趣本身就意味著一種歷史選擇。
在充滿反叛意味的先鋒文學中,歷史理性被肆意解構,“它不再相信直線發展的歷史觀”[3],所謂的歷史只不過是非理性現實的堆砌。在《一九八六年》中,余華正是借助“瘋癲”撥開了歷史理性的迷霧,探及了歷史的非理性真實。對歷史暴力懷有本能恐懼的歷史老師,正是在瘋癲以后才承擔起了重述歷史的職能。如同魯迅筆下的狂人一樣,正是“瘋癲”使其意外接近了歷史的真相,并成為敘述真相的先知。他在一九八六年初春之季的歸來,不僅僅是地理空間上的轉移,還隱喻著歷史非理性本質的顯現。歷史老師是以一個瘋癲者的身份回歸的,“瘋癲”是理性的退場,也意味著個體現實心理時間的停滯和人格的固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瘋癲”將歷史教師拋擲出現實時間的線性運動軌道,造成其心理時間與現實時間的錯位,并將其永恒地遺留在那段歷史之中。
余華將瘋子回歸的時間設置在一九八六年,并且有意將這個特殊時間節點作為小說的題目凸顯出來,實際上正表達了他對歷史災難周期循環、卷土重來的隱憂和警惕。瘋子作為歷史非理性本質的象征走進人們的視野之中,他瘋癲的精神狀態和傷痕累累的肉體是對歷史的指證與提醒,他“已將人們決意忘記的過去轉化成了可感可觸的實體,呈現到了大眾面前”[4]。然而,“他們都看到了他,但他們誰也沒有注意他,他們在看到他的同時也在把他忘掉”[5]119。并且,這種對歷史的遺忘還象征性地體現在女兒對待兩個父親的態度上。
面對大眾對歷史的遺忘,瘋子的慘烈自戕是一種強有力的喚醒手段。他在癲狂意識的主導下將肉體獻祭給刑罰,這就使得其身上不僅承載著對于歷史的災難記憶,同時也成為整個歷史的言說者。他對自己身體施以極刑,實際上是將歷史的暴力本質通過肉體暴力直觀地呈現出來,從而達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瘋子非理性行為的背后實則隱含著敘述者對歷史理性精神回歸的呼喚。與此同時,余華也在歷史老師的瘋癲行徑中完成了對民族歷史的重構。他將瘋子此前的身份設定為一名歷史老師,這本就為他重新詮釋歷史提供了便利;而歷史老師在遭遇迫害后的“瘋癲”則戲劇性地賦予了他言說歷史的自由并成為其重構歷史真實的起點。
二、瘋癲:人性暴力欲望的敞視點
“余華一定認為人類生活本質上是非理性的,是荒誕不經的,在貌似秩序井然有條不紊的外表下,世界其實是混亂不堪和莫名其妙的”[6],因此,“瘋癲”才是人類的精神常態。由于“瘋癲”以其強大的破壞力沖決了理性思維的束縛,釋放出人的原始欲望,而這些欲望往往將人類內心最隱秘的瘋狂、非理性本能以及混亂的潛意識不加修飾地呈現出來,并展現了關于人性的另一種真實,這就導致余華慣于從人的內心欲望而不是性格去理解人的生存狀態。
“而一個作家,如果從欲望結構開始對人類的存在旅程的探查,他首先要面對的一定是人類內部那些難以阻遏的暴力景象”[7]176,所以,余華首先關注到的便是存在于人性深處的暴力欲望。在《一九八六年》中,余華正是通過“瘋癲”這一視角探及了人性中的“暴力欲望”并對其作了全景式的敞視。
(一)瘋癲釋放出強大的本我暴力
循規蹈矩的歷史老師年輕時獨獨對歷史酷刑產生濃厚的興趣,“除了出于探究歷史之謎的專業目的,不能說沒有攻擊性本能的無意識外投”[8]。刑罰將肉體作為釋放暴力的場地,“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細劇烈的痛苦’”[2]37。對于這樣一種殘忍的懲罰制度,歷史老師除了好奇與迷戀的態度以外,并沒有其他任何人道主義情感的流露,這表明他身體內本身就隱藏著一種暴力型人格。于是余華便借用了“瘋癲”的力量將其釋放出來——“瘋癲”使歷史老師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本我暴力欲望沖破自我理性的牢籠,將其人性之惡放大到極致,使人在酒神精神般的迷狂中心甘情愿地淪為本我的奴隸。
在理性的眩暈中,瘋子看到的是一個血腥殘暴的世界:太陽是“一顆輝煌的頭顱,正噴射著鮮血”[5]122;小鎮成為一座巨大的墳墓;被樹蔭遮蔽的水泥路像一根蒼白的骨頭躺在地上;街邊的路燈則是懸掛著的人頭……一切都是非常態暴力景觀的映現。而此時的瘋子則成為一臺暴力制造機器,在幻覺與現實中不斷享受著殺戮與鮮血帶給他的極致快感。可以看到,瘋子始終是以施刑者即劊子手這一角色自居的。在幻覺中,他肆意對路人大開殺戒,尤其是在展銷會上,這種對他人施刑的暴力想象達到了極致。瘋子沉迷在腦海里這場肢解肉體的狂歡盛宴中,毫無節制地宣泄著心中的原始惡欲。在這充滿濃厚血腥氣息的幻象中,瘋子的殘暴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幻覺中的殺戮并不能徹底滿足瘋子心中的暴力欲望,于是他以自己的肉體為中介,將行刑的場面由想象中的真實轉化為現實中的真實:路過鐵匠鋪的瘋子抓起燒紅了的鐵塊對自己施行了墨刑;在陽光鋪灑的街道上,他又對自己的肉體輪流實施著劓、剝皮、宮等刑罰;最后在街道的一隅,瘋子找來一把遲鈍的菜刀,瘋狂地砍割著自己的大腿……在瘋子的自戕中,他扮演著施刑與受刑二位一體的角色,但在潛意識中他仍然是以施刑者的身份自居的。
瘋子的主體性在施刑的過程中得以彰顯,其肉體則淪為被動承受的客觀對象。這就使得他能在自殘中獲得一種仇殺般的快感,這種快感能覆蓋其肉體上的劇烈疼痛感,使他的受刑者意識處于被壓抑的狀態。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瘋子更多的是以施虐者的身份而不是受虐者的身份出現的。
對刑罰的迷戀是歷史老師人性中無意識暴力欲的體現,而“瘋癲”則以其激烈而極端的方式攻破了理性的最后一道防線,從而將本我暴力徹底釋放出來。
(二)瘋癲召喚出精神暴力的制造者
顯然,余華對“瘋癲”與“暴欲”的思考遠不止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而是更為深刻。當人們還沉浸在瘋子癲狂的暴力行徑帶來的驚駭中時,余華已經開始了更深層次的探索。
在《一九八六年》中,他通過對瘋子與他人之間冷漠關系的描寫,向我們揭示了“瘋癲”所召喚出來的另一種新的暴力話語體系。它產生于除瘋子以外的人群中,所遵循的是一種隱性的精神暴力法則,因此在話語表現上是緘默的。同時,由于它的締造者是精神正常的大眾,因而它在表現形式上是理性的,在存在方式上則是普遍的。文中瘋子的存在是引發這種精神暴力的關鍵,同時,他也因為處于這場暴力的圍困中心而成為被其公開處決的對象。
當瘋子在春暖花開的季節走進小鎮時,人們都沉浸在自己的幸福中而對他視而不見,瘋子怪異的舉動和瘋癲的情狀要么使他們避而遠之,要么成為他們肆意嘲弄的對象。這是一種精神上的規避與排擠,是一種零度的暴力。它建立在“理性”與“瘋癲”二元對立的結構上,是一場“理性”對“瘋癲”的精神驅逐。在理性無聲的強壓下,“瘋癲”則因其勢單力薄而陷入一種孤立無援的境遇,從而淪為邊緣化的存在。
在瘋子的行刑場面中,這種精神暴力在圍觀群眾集體無意識的默契中達到了最強程度。瘋子通過慘烈的刑罰儀式將街頭變成一個象征意義上的刑場,“如果說支撐刑罰的主體是施刑者和受刑者,那么支撐刑場的主體則是圍觀者(看客)”[9],觀刑者的出現不僅意味著看與被看這一關系結構的確立,而且其本身也在一種血氣彌漫的恐怖感中承擔著某種語義功能。在施刑過程中,瘋子是被看的主體,他用血肉撕裂的方式展現了一種喧囂的瘋癲話語,它以鮮血淋淋的視覺畫面和慘絕人寰的哀號直接刺激著在場人群的感官,從而成為一種可感的顯性存在。但瘋子的慘烈受難并沒有引起圍觀者的絲毫同情,投射在他傷痕累累的肉體上的目光里只有好奇、驚異、恐怖和冷漠。于是,在瘋狂的刑罰獻祭儀式上,一種于人性中隱藏得更深、更為可怕的暴力話語被召喚出來。它在看客中間悄然崛起,以冷峻的目光和沉默的態度回應刑罰現場的血腥事實,并與瘋子施刑過程中所釋放的瘋癲力量構成了一種無聲的對峙局面。
瘋子的妻女也是這場精神暴力的締造者,她們與小鎮的人群共同聯手完成了對瘋子的精神處決。當歷史老師失蹤后,他的妻子沒有選擇等待他的歸來,而是在幾年后改嫁他人,并更改了女兒的名字——“那是因為女兒原先的姓名與過去緊密相連”[5]110,這本身就意味著一種主動的割舍與忘卻。當歷史老師再度出現在小鎮上時,心靈上感應到他回歸的妻子并沒有對此感到開心和期盼,而是深陷于一種極度恐懼不安的情緒中無法自拔。她將自己幽閉在家里,以逃避的方式表明了對他的拒絕態度。盡管妻子沒有目睹歷史老師的自戕場面,但她仍然感應到了他痛苦的喊叫并洞見了其鮮血淋漓的形象。她深知曾經的丈夫正在遭受慘烈的折磨,卻依舊不聞不問。而瘋子的女兒一見到他就感到厭煩恐懼,唯恐避之不及。直到瘋子死去,母女倆才感到一種如釋重負的輕松。這不由得讓人想起卡夫卡的《變形記》,文中的瘋子跟小說中變形成甲殼蟲的格里高爾一樣,他們都因為自身不幸的變故而遭受到了來自家人的精神冷暴力,最后在被遺棄與厭惡的狀態中孤獨地死去。
在《一九八六年》中,人人都是瘋癲的。如果說瘋子是瘋癲的絕對體現者,那么他的妻女和小鎮上冷漠的人群則淪陷于一種理性的瘋癲之中,他們的存在足以說明:“人類必然會瘋癲到這種地步,即不瘋癲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瘋癲。”[10]1顯然,相較于前者,后者更令人感到絕望與窒息。
三、二重奏式的瘋癲敘事
在《一九八六年》中,癡迷于古代刑罰的瘋子是余華進行瘋癲敘事的主要憑借工具——瘋子精神上的“瘋癲”為他書寫人性與歷史提供了極大的想象自由,而瘋子的肉體賦予了其隨意處置和利用的權利。因此,余華在瘋子的腦海中和肉體上自由地展開了他的一系列瘋癲敘述。總的來說,余華在《一九八六年》中的瘋癲敘事具有音樂上的二重奏調式的特點,它具體表現為兩種感情色彩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話語模式在一種和諧的敘述旋律中交織并存,同時卻又相對獨立地保持了自身的風格調式。而文本內涵和敘事形式也在兩種相反話語模式制造的反差感中擁有了極大的豐富性和更多的可能性。
(一)暴力書寫的“外冷內熱”
“瘋癲”和“暴力”天然就是一對親密無間的孿生兄弟:“瘋癲”是釋放“暴力”的最佳途徑,而“暴力”則以極端的激情展現著“瘋癲”。在《一九八六年》中,余華正是將暴力書寫作為瘋癲敘事的主要策略之一,從而完成了對瘋子癲狂情狀的展示。他通過“刑罰”這一意象,進行了大量的暴力書寫,同時,還對這些暴力血腥場面作了直露式的展示,并在一種冷漠的語氣中達到了對其近乎客觀紀實般的呈現。盡管余華在描述暴力場面時采取了零度的寫作姿態,但在其平靜的話語下面顯然洋溢著一股敘述上的亢奮與激情,這就使得他的暴力敘事表現出一種“外冷內熱”的特征。
比如,余華對瘋子在展銷會上所幻想的殺人場面的敘述:“無邊無際的人群正蜂擁而來,一把砍刀將他們的腦袋紛紛削上天去……他專心地撥開左肺,挨個看起了還在一張一縮的心臟。”[5]142這是一場殺戮的盛宴,余華雖然對此進行了不動聲色的描述,但我們仍然可以從中感受到一種想象的激情和瘋子施暴的快感。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余華的暴力書寫實則是用有節制的語言對“暴力”進行著無節制的展示。這種對暴力書寫的內在熱情在瘋子行刑的血腥場面中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現:實施酷刑是一件極其恐怖殘忍的事情,“而余華的字里行間則充滿了豪華奢侈的感官快意,對行刑過程慢鏡頭式的描述和對血腥場面濃墨重彩的渲染都暴露了余華思維的缺乏自制,他沉醉在自己制造的語言迷境中無力自拔”[11]。余華慣于以一種漫不經心的語氣達到對慘烈血腥場面的極致呈現,在理性表述的話語背后,潛藏著余華對暴力敘事的不自覺迷戀。可以說,他的暴力書寫是一場冷靜的狂歡。
對暴力的心醉神迷與敘述話語上的理性克制構成一種二重奏式的敘事結構,它一方面向讀者呈現出最恐怖血腥的丑陋場面,另一方面又以一種零度語言強化了接受者的壓抑性體驗,這就導致接受者往往從心理上感到不適并難以接受,也于某種程度上弱化了作者批評人類精神狀態異化這一現象的嚴肅意圖。
(二)敘述場面的“輕”“重”交織
小說中,隨著瘋子的內聚焦視角與敘述者的外聚焦視角來回切換,兩個截然不同的平行世界交織呈現在讀者眼前:一個是瘋子身處的幻覺世界,另一個則是小鎮人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歷史老師的發瘋是置換這兩個世界的關鍵,它們相互重疊交叉卻又各自獨立,并且永遠無法融合為一個和諧的整體。
歷史老師在遭遇了不幸的變故后儼然已變成一個瘋子,“其顯著的心理特征便是失去了與外界的現實聯系而在自己心中建立了一個現實世界”[6]。“瘋癲”使他永久地遁入了內心的幻覺景象之中,并由此裂變出一個非理性的獨立世界,將人類的同一生存空間一分為二。
在瘋子的內聚焦視角中,現實以非常態的猙獰面目顯現,而他成為這里的絕對主宰者,肆意操控著生殺大權,親手制造著死亡與暴力。在這個瘋癲意識締造的混亂幻象中,一切都顯得那么沉重、壓抑和恐怖。敘述者時常對瘋子腦海中的暴力幻覺畫面作細節式的觀察,并試圖達到對血腥暴力場面的逼真描述,因而敘述節奏也相對緩慢沉悶。
然而,當敘述者轉變觀察角度,從零度的外聚焦視角打量瘋子生活著的現實世界時,映入其眼簾的則是一片歡樂祥和的景象:溫暖的春天已然降臨,燦爛的陽光和璀璨的群星裝點著小鎮人民的白天和黑夜;人們懷著對生活的憧憬涌進各式各樣的繁華商店和擁擠的電影院,就連空氣中都飄蕩著歡聲笑語……顯然,敘述者在對小鎮人民所生活的世界作觀察描述時,語調明顯變得輕松明快起來,就連瘋子殘忍自戕的場面,敘述者都能予于一定的抒情化描寫。
比如,對瘋子鋸鼻子的形容:“那鋸子鋸著鼻骨時的樣子,讓人感到他此刻正怡然自樂地吹著口琴。”[5]134由此,施刑行為的沉重性被輕松歡樂的氣氛徹底解構。小鎮人民貪婪地享受著生活的安寧與幸福,無暇也不愿顧及舉止怪異、衣著骯臟、遍體鱗傷的瘋子,他們已經被劃分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當瘋子通過當眾自戕的行為試圖建立起兩個世界的聯結時,小鎮人群卻將這一沉重事件化解為飯后閑暇之余的歡樂談資,從而徹底取消了兩個世界溝通的可能性。這就使得它們只能作為對立的存在,其結果便是加劇了小說中敘述場面的分裂性和反差感。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災難的結束不過才短短十年,人們卻早已在徹底的遺忘中埋葬掉了那段痛苦的記憶。瘋子的出現則將苦難的歷史推置人們眼前,使得歡樂的假象被打破,現實的和平幻象與歷史的暴力真相也就并置于同一時空之中,這便造成了一種反諷和嘲謔的敘事效果。
敘述者通過視點的輪流切換,使得沉重和輕松的敘述場面由此交織在一起。在一種鮮明的對比意味中,歡快輕松的場面不再給人幸福的感覺,而是淪為沉重場面的一種底色鋪墊,它的功能只在于從最大程度上彰顯瘋子命運的悲劇性,從而引起讀者的憐憫和反思。
四、結語
小說《一九八六年》是余華瘋癲敘事的經典之作,其不管是在內容上還是敘述上都體現出典型的余氏風格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瘋癲敘事既成為余華反抗傳統敘事和傳統美學觀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時又傳達出他對人類真實生存境遇的感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九八六年》亦是進入余華瘋癲敘事的一個特殊解碼符,從中不難觸及另一種生存真實。
參考文獻:
[1]余華.虛偽的作品:沒有一條道路是重復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2](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
[3]楊慧.現代性的兩種“瘋癲”想象——重讀“尋根文學”與“先鋒文學”中的“瘋人”譜系[J].藝術廣角,2010,(01).
[4]摩羅,楊帆.虛妄的獻祭:啟蒙情結與英雄原型——《一九八六年》的文化心理分析[J].文藝爭鳴,1998,(05).
[5]余華.現實一種[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
[6]王彬彬.余華的瘋言瘋語[J].當代作家評論,1989,
(04).
[7]謝有順.先鋒就是自由[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
[8]畢光明.“無法愈合的疤痕”:啟蒙敘事與歷史記憶—— 《一九八六年》再解讀[J].當代作家評論,2019,(03).
[9]蔣麗娟.刑罰的意味—— 《檀香刑》《紅拂夜奔》《一九八六年》及其他[J].理論與創作,2005,(04).
[10](法)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
[11]孫彩霞.刑罰的意味——卡夫卡《在流放地》與余華《一九八六年》的比較研究[J].當代文壇,2003,(03).
作者簡介:
劉童,西華大學在讀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