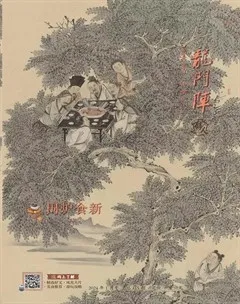冬日摸魚
李坤
“啪啪啪”的擊水聲,加上孩子們歡快著急的吶喊聲,把冬日曬場的摸魚大戲又推向了另一個高潮。
秋天的農事剛結束,鄉親們就在醞釀著冬日摸魚了。
破冰摸魚,兒時在老家村上可是一件大事,這不僅關乎提高自家餐食質量,還事關男人展現強壯體魄——會捉魚的男人在村上是受人尊重的。
老家的曬場很大,東面是菜園,南面是村前的大河,西面和北面是莊稼地。一條丁字形的大河,是菜園和曬場的分界線,同時又把曬場分為南北兩片,這條河一年四季流水不斷。
每年稻子脫粒后,鄉親們都要把稻谷在曬場上晾曬十天半個月,為了堆放稻谷和看護方便,每家都在自家的曬場邊建一個用土壘墻、稻草覆頂的小房子。
因為有房子存放糧食,稻子脫粒后每家并不急于晾曬,慢騰騰地挨到了河面結冰的時候還有人家在晾曬。零星幾家晾曬的稻谷,一群群起落的麻雀和鴿子,給偌大的谷場增添了些許生氣。
此時,一年一度的冬日破冰摸魚大戲即將上演。
按照往年習慣,小隊長喊上身強體壯的男人們開個小會,這些男人早就準備好了。破冰摸魚一般選在晚上,因為白天男人們都忙著農事。
選定的男人們穿著皮衩,因為需要彎腰在水里摸魚,這種皮衩都是全身武裝的。天色漸暗,“皮衩們”已經聚集在曬場躍躍欲試,小隊長說了要求后,“皮衩們”排成一排,從河的一頭拉開了大戲的帷幕。
河就是曬場中間的丁字形河,從我記事起這條河就沒有干涸過。村上的冬日摸魚只捉半斤以上的大魚,小魚繼續留在河里生長。
摸魚開始了。“皮衩們”站成一排,每人腰間掛著一個柳條編的魚簍,魚簍口上卡著用稻草編成的倒刺,魚只要進了魚簍是絕對出不來的。“皮衩們”人手一根兩米長的粗木棒,用木棒使勁地擊打水面向另一個方向趕魚。受驚的魚只能向前逃竄,“皮衩們”邊擊打水面邊前行幾步,還會蹲下身子在水里摸索一番,有些慌不擇路的魚倒游回來正好落入了“皮衩們”的手中。還有個別魚直接被猛烈擊打所產生的沖擊波震暈,直挺挺地漂在水面上,在月光下翻著白花花的肚皮,被“皮衩們”順手丟入簍中。
穿著皮衩,再加上揮舞大棒破冰,“皮衩們”汗流浹背。塘邊的大人們拿著手電給“皮衩們”照亮,孩子們一遍遍地從河這頭跑到那頭,再從那頭跑回來,也是興奮得一身汗。“這兒!這兒有一條!”間或發現一條暈在河面的魚,孩子們蹦跳著連聲大叫。“啪啪啪”的擊水聲,加上孩子們歡快著急的吶喊聲,把冬日曬場的摸魚大戲又推向了另一個高潮。
這樣邊趕著魚邊行進,到了最后二三十米是魚兒最多的,“皮衩們”在水里矮下身子,細細摸索起來。冬季魚都是貼著水底游動,擊打水面的聲音擾亂了魚的生活習慣,“皮衩們”捉起魚是手到擒來,魚撞擊魚簍的“嘭嘭嘭”聲傳得老遠。
終于開始分魚了。會持家的主婦都希望分點小雜魚,回家多剁點蘿卜煮個魚凍,夠吃上一段時間,那些大魚愿意要的人并不多。分魚過程中大家免不了一陣挑選、嫌棄、說和。
帶了袋子裝起魚來方便,沒帶袋子的便順手在塘坎邊折一根荊條,在荊條下端打個結,從魚鰓穿過魚口,把魚串起來拎回家。凌晨時分,塘邊終于歸于平靜。
月明星稀的夜晚,家家戶戶的窗戶里都隱約地透出朦朧的燈火,像天上的群星隕落人間,灶屋里飄出的腥味急得家里的貓抓耳撓腮,“喵喵”直叫喚。
下半夜,塘邊貓們呼朋引伴、爭搶魚的叫聲此起彼伏,熱鬧非凡。后半夜的塘邊,是貓們的天下,直到幾顆星星在西天掙扎的時候,它們才心滿意足地散開。
如果第二天早晨去得早,我們偶爾還能在水面的犄角旮旯撿到幾條被木棒砸死的魚,打個牙祭過個嘴癮綽綽有余。
隨著村莊發展,丁字形的河道早被侵占了大半,剩下的承包給了個人,每年歲末都是簡單粗暴地戽魚,全然沒有了冬日摸魚的樂趣。那曾經熟悉的破冰摸魚場景,只能在記憶中慢慢回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