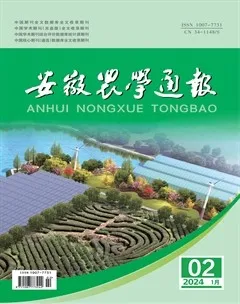鄉鎮尺度下W 縣生態—經濟—社會耦合協調評價
駱 云
(重慶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重慶 401331)
鄉村經濟社會由經濟發展、自然生態和社會人文等子系統組成[1],這些子系統的結構、比例關系對整個系統的狀態和功能至關重要[2]。鄉村是一個兼具自然、社會和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為實現“農業強、農民富、農村美”的目標,須加快鄉村內部生態、經濟和社會各系統之間的協調融合發展[3]。因此,揭示鄉村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耦合協調發展水平,促進生態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田園城市”構想的提出[4],人們開始意識到應將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作為一個整體去探討,這就要求經濟社會得到快速發展的同時,須同步推進生態系統的發展[5]。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CK)很好地解釋了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各系統之間不應互相排斥,而應互相成就[6]。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矛盾日益趨緊,在該領域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相關學者以三峽庫區[7]、國家公園[8]、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9]及生態主體功能區[10]等具有代表性的區域為研究對象,探討了區域生態、經濟和社會綜合協調發展特征。
縱觀現有研究,對縣域尺度生態、經濟和社會復合系統的研究比較少,以鎮域尺度探討鄉村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發展水平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本研究區域W縣地處三峽庫區重慶段,是重點生態功能區,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尚待提升,該地經濟生產總值排名位次靠后,因而有必要關注其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的協調發展。本文基于鎮域尺度,采用CRITIC-TOPSIS模型、耦合協調度模型,探討該地區的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之間耦合協調水平,為推行更加有效的系統治理體系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耦合機理
生態系統是基礎和載體,是鄉村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鄉村可持續發展實現的落腳點在于自然生態系統、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經濟系統是主導和支柱,鄉村可持續發展的目的是加快三產融合效率和深度,增加經濟系統發展帶來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主要通過確保鄉村生產活動的轉型升級,提高鄉村生產總體水平,進而促進鄉村經濟快速發展。社會基礎是影響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好的社會基礎有利于鄉村經濟的發展。
1.2 評價指標體系
參照相關研究成果[11-12],并結合W縣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發展的實際情況,本文擬定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如表1 所示。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官網,該地2022 年統計年鑒、2021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鄉鎮數據庫統計數據,以及第七次人口普查資料。

表1 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評價指標體系
1.3 研究方法
1.3.1 CRITIC-TOPSIS 模型設Cj為第j個指標所包含的信息量,則Wj設為第j個指標的客觀權重,Wj的計算公式如下[13]。
1.3.2 耦合協調度模型在參考已有研究基礎上,引入物理學中的耦合模型來分析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耦合協調度,計算公式如下[14]。
式中,C為耦合度,D為耦合協調度,T為3 個系統綜合度,α、β、δ代表3個系統的權重。考慮到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的重要程度一致,將α、β、δ均賦值為1/3,并將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進行等級劃分,如表2所示。

表2 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的等級劃分標準
2 結果與分析
2.1 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綜合發展水平
通過TOPSIS模型計算出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綜合評價值,利用ArcGIS10.8 對各系統綜合指數進行空間可視化表達,并按照自然斷點法將其分為低水平、較低水平、一般、較高水平和高水平5個等級。
生態系統指數介于0.196~0.490,均值為0.296,共有17 個鄉鎮的生態系統指數低于均值,占研究區的56.67%,其中,處于低、較低水平,高水平占比最少,僅有6.67%。生態系統發展水平居前列的鄉鎮,主要得益于以生態為基,發展生態產業和綠色產業。而生態系統指數最低的鄉鎮,其綠化覆蓋率較低,土壤侵蝕較嚴重,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其生態功能的發揮。
社會系統指數介于0.189~0.553,均值為0.366,共有14個鄉鎮的社會系統指數低于均值,占研究區的46.67%,超50%鄉鎮處于一般以上水平,有12 個鄉鎮的社會系統指數處于低水平和較低水平,占整體的40.00%,高水平的鄉鎮有5 個,占整體的16.67%。排名靠前的鄉鎮得益于其醫療、教育和路網等基礎設施建設比較完善。而社會發展水平靠后的鄉鎮,主要原因是其教育、醫療水平,文化旅游發展水平有待提升,常駐人口較少以及勞動力資源較為短缺等。
經濟系統指數介于0.09~0.597,均值為0.230,共有18個鄉鎮的經濟系統指數低于均值,占研究區的60%,其中有12個鄉鎮的經濟系統指數屬于低水平、較低水平,高水平鄉鎮有6個,占整體的20.00%。其中經濟發展指數為高水平的鄉鎮,是全國重點鎮和市級中心鎮之一、市經濟百強鎮,綜合實力居該地第一位。而排名最后的鄉鎮,其經濟發展較弱,人均收入低,旅游收入居該地末位,除此之外,其農業收入、特色農產品產量低都是阻礙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2.2 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耦合協調度
2.2.1 耦合度該地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的耦合度在0.409~1.000,基于前文對耦合度等級的劃分,其生態、經濟及社會系統的耦合度整體處于拮抗階段以上,表明該地區30 個鄉鎮的生態、經濟及社會系統之間的關系較為緊密,相輔相成,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各鄉鎮的經濟、社會系統發揮了基礎和載體作用,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生態、社會系統提供了支持。
該地各鄉鎮三系統之間的耦合度存在一定差距,但是整體耦合度較高,30 個鄉鎮中處于磨合階段的鄉鎮有10 個,占整體的33.33%,處于高水平耦合階段的鄉鎮有16 個,占整體的53.33%,而處于良性共振耦合的鄉鎮有1 個,該鎮作為全國重點鎮,其規模較大、人口較多,且經濟較發達、配套設施較完善,是該地輻射能力較強的農村區域性經濟文化中心。
2.2.2 協調度該地生態、經濟及社會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在0.254~0.995,均值為0.524,說明三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整體處于勉強協調以上階段,且鄉鎮數達17個,占整體的56.67%。根據耦合協調度的分級標準及數據狀況,三系統的耦合協調度可表現為7種類型:初級協調的鄉鎮有8個,占整體的25.00%,分布較為分散,北部、中部、南部均有分布,西部分布相對集中;優質協調的1 個鄉鎮屬該地西南地區,得益于該鎮的悠遠歷史、人文薈萃、山文奇美和地廣物豐等優勢。30個鄉鎮中,耦合協調度水平靠后的鄉鎮近些年因地制宜規劃了農業產業布局,以提升其產業發展水平。
3 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W縣為研究對象,采用CRITIC-TOPSIS、耦合協調度探討其生態—經濟—社會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狀況,主要得出如下結論。
(1)從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的發展均值來看,該地經濟系統綜合發展水平有待提升,社會系統綜合發展水平較好。從空間上來看,生態—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發展有一定的相似性,主要表現在該地西南地區發展較好;同時也存在差異性,主要表現在各發展階段鄉鎮的集中性。
(2)該地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的耦合協調度整體處于勉強協調以上階段。各鄉鎮間生態—經濟—社會系統之間的耦合度存在一定差距,整體耦合度較高。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鄉鎮尺度研究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之間的耦合協調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對該地的鄉村可持續發展提供借鑒,但本研究存在研究時間尺度跨度短,未探討影響生態、經濟和社會系統耦合協調發展的因素等不足。因而在未來的研究中,應拉長研究的時間尺度,以便更加清晰地對比分析該地鄉村復合系統的發展現狀,同時,根據該地鄉村可持續發展實際以及立足區域特點,探討影響鄉村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