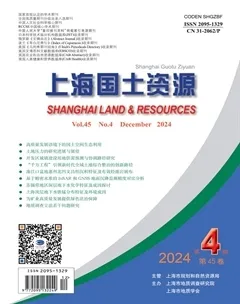農牧交錯帶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對于生態環境的影響研究








關鍵詞:土地利用變化;生態環境質量;農牧交錯帶;空間分異;生態保護
中圖分類號:F301.24; X17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1329(2024)04-0019-08
地利用是一種社會經濟行為,具體表現為人類根據自身發展需求和土地資源的自然特征使用和改造土地[1]。然而,人類對土地資源的開發利用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對區域生態系統產生了顯著影響[2]。近年來,我國面臨著日益增加的環境壓力與生態風險,如何提升生態治理能力與治理水平、構建經濟與生態協同發展的可持續模式成為了當前我國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3]。當前,我國正處于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時期,而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與提升則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題中之義[4-6]。因此,應切實探明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對區域生態環境所產生的影響,并了解不同情境下的區域未來土地利用變化趨勢。
當前,學界關于土地利用結構變化與優化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對于土地利用結構的時空演變[7-8]、土地利用多情景模擬[9-10] 與變化特征[11-12] 均開展了廣泛研究,并將機器學習[13]、強度分析[14] 等前沿方法引入到了土地利用結構變化與優化相關的研究領域之中,且逐漸關注到了土地利用結構同碳儲量[15]、生態風險[16-17] 及生態系統服務價值[18-19] 等要素的關聯。然而,現有土地利用模擬研究較多運用FLUS 模型,盡管FLUS 模型也可對某地區未來的土地利用格局進行預測,但PLUS 模型具有更優于FLUS 模型的空間擬合效果與模擬精度。同時,就研究視角而言,較少學者關注到了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具體影響,且在研究區域的選擇上,現有研究也較少關注到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這一生態脆弱地帶。
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對維系我國生態安全起到了重要的屏障作用,對維持區域生態系統功能的穩定也具有重要意義[20],該地帶包括內蒙古、寧夏、黑龍江、吉林、等9個省( 自治區) 的154個縣( 旗、市),面積62.1 萬hm2,在中國人地關系地域系統中屬于一種特殊地域類型,具有防風固沙、涵養水源、凈化江河、防止水土流失等特殊生態作用,同時, 該地帶也是自然生態環境惡化最嚴重、經濟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具有生態脆弱與生態敏感的雙重特性 [21]。伊金霍洛旗地處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該地生態問題突出、治理成效顯著、地理位置關鍵[22],是位于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典型地區。因此,本文以伊金霍洛旗為研究區,引入生態環境質量指數與土地利用變化生態貢獻率,探究該地區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對生態環境產生的影響,并運用PLUS 模型對2030 年自然發展、生態保護情景下的伊金霍洛旗土地利用變化進行了模擬、預測以了解區域未來土地利用變化趨勢,進一步探究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及其同區域生態環境質量之間的關聯,以此為類似地區生態環境治理工作的開展提供參考。
1研究區與數據來源
1.1研究區概況
伊金霍洛旗為鄂爾多斯市下轄旗, 地理坐標108°58′~110°25′ E,38°56′~39°49′ N,總面積5 489.65平方公里。該旗地處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是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過渡的半干旱、干旱地帶。區內草地分布廣泛、面積遼闊,且具有草地與耕地交錯分布的土地利用特征。同時,該旗介于庫布奇沙漠與毛烏素沙地之間,地理位置特殊、生態環境脆弱[23-24]。
1.2數據來源
本文土地利用數據來源于中科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數據平臺,將各用地類型劃分為耕地、園地、林地、草地、濕地、建設用地與其他用地,人口密度與GDP 的空間數據同樣獲取自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與數據中心平臺。DEM 數據獲取自地理空間數據云平臺。交通路網與水系數據獲取自OpenStreetMap。各類空間數據的分辨率均為30 m×30 m。
2研究方法
2.1生態環境質量指數
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將土地利用變化與生態環境質量相關聯(表1),以此使區域內生態環境質量的總體狀況得以表征[25-26]。其計算公式如下:
2.3 PLUS模型
PLUS模型包括了用地擴張分析策略(LEAS 模型)和基于多類隨機斑塊種子的CA模型(CARS 模型),可在探究土地利用變化影響因素的同時模擬、預測土地利用斑塊的變化[30]。其中LEAS模型所需要的驅動因子數據集包含三大類,共10個驅動力因子:一是自然環境數據,包括高程、坡度、坡向三項驅動因子;二是社會經濟數據,包括人口密度、GDP、兩項驅動因子;三是交通路網及水系分布數據,包括公路、鐵路、城市道路、鄉村道路、河流湖泊五項驅動因子。本文共設置自然發展與生態保護兩個情景,由a至g分別為七種土地利用類型,轉移成本的確定以相關文獻[31-32]與研究區具體情況為依據,各情景轉移成本如下(表2):
本文對于預測結果進行了精度檢驗,預測結果總體精度達到84.61%,FOM值達0.26,結果達到模擬要求。
3研究結果
3.1土地利用變化情況
3.1.1數量變化
2010—2020年伊金霍洛旗土地利用面積變化情況如表3所示。2010年各地類面積占總面積之比從大到小依次為草地、林地、耕地、建設用地、濕地、園地。至2020年,伊金霍洛旗建設用地面積占總面積之比超過耕地,園地面積占總面積之比超過濕地。具體來看,2010—2020年間各地類面積占總面積之比變化幅度較大的主要有草地、林地與建設用地。十年間,伊金霍洛旗草地面積大幅度下降,占比由59.03% 降至47.90%;林地面積占比顯著提升,由27.17% 提升至36.97%;建設用地面積占比由5.21% 提升至7.37%。雖然伊金霍洛旗耕地面積占比變化甚微,但在全國耕地面積在2010—2020年減少1.13億畝的背景下呈現上升趨勢,體現出了該地耕地保護工作的力度與成效。
3.1.2空間變化
伊金霍洛旗位于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十年間,其土地利用空間結構所具有的農牧交錯特征并未改變,具體表現為草地面積廣闊且耕地、草地相互交錯,該特征在區域中部、西部地區最為顯著。草地與林地在空間維度上的變化顯著:一方面,區域中部地區的草地大量縮減,草地大量向耕地與林地,另一方面,林地在區域中部、南部、西部地區呈現出了大幅擴張的特征。建設用地斑塊呈現擴張趨勢:區域東部建設用地斑塊密度顯著增加,中北部建設用地集聚區域在十年間呈現向外擴散的趨勢,但區域中東部邊緣地區建設用地斑塊在十年間密度減小,由集聚狀態轉為了分散狀態。
3.2轉移情況
2010—2020年間,伊金霍洛旗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社會經濟高速發展。與此同時,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也受到了高度重視。區域的多元發展特征改變了土地利用方式,土地利用結構也因此相應發生了變化。十年間,伊金霍洛旗土地利用結構變化顯著,各地類之間的流動頻繁,不同土地類型間均呈現不同程度的空間位置轉換與數量變化。因此,本研究建立土地利用轉移矩陣(表4)以揭示土地轉換趨勢。
在地類變化中,草地轉出最多,為12 6915hm2,主要轉變為林地;其次為林地,主要轉變為草地和建設用地。2010—2020年,林地的面積增長最多,增加了111516hm2,主要由草地、耕地、建設用地的轉入;其次為草地,主要由林地和建設用地轉入。建設用地新增加26883hm2,流出15033hm2,且大部分轉出為草地和林地,耕地新增加19172hm2,流出17661hm2,二者均呈現流入大于流出的地類變化特征。
3.3 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的生態環境響應
3.3.1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分析
表5為基于公式(1)計算得出的伊金霍洛旗2010年和2020年的土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在2010—2020年,耕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由0.01613提升至0.01682,林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由0.25811提升至0.35123,建設用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由0.00782提升至0.01105,園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由0.00002提升至0.00062。上述數據表明該地區耕地、林地、建設用地、園地生態環境質量得到了改善,其中林地生態環境質量提升最為顯著。草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由0.44275降至0.35926,其他用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由0.00068降至0.00045,表明該地草地、其他用地生態環境質量下降,其中草地生態環境的惡化趨勢最為顯著。總體上,伊金霍洛旗2010—2020年生態環境質量指數由0.729提升至0.73962,表明該地生態環境質量呈現出了緩慢上升的態勢。
此外,本文運用自然斷點法對2010年和2020年伊金霍洛旗生態環境質量指數進行了分級(圖4)。分級結果表明,伊金霍洛旗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分級標準在十年間也發生了變化,具體表現為低質量區、高質量區最低值提升而最高值下降,中質量區最低值下降而最高值提升。
3.3.2土地利用轉型生態貢獻率分析
由圖5 可知,對伊金霍洛旗生態環境質量提升具有較高貢獻度的轉化類型分別為耕地轉化為林地、草地,建設用地轉化為林地、草地,其他用地轉化為林地、草地以及草地轉化為林地。其中,草地轉為林地的面積最大,所具有的生態貢獻率高達3.44%,貢獻比重達到43.72%,由于草地與林地之間生態背景值差值較小,可知草地轉為林地所帶來的高貢獻率主要受到轉化面積影響。由于耕地與林地之間生態背景值的差值較大,同時轉化面積僅次于草地向林地流轉的面積,達到了10171hm2,因此耕地轉為林地的貢獻率達到1.30%,僅次于草地向林地轉換所帶來的生態貢獻率,其貢獻比重為16.49%。同時耕地向草地的轉化所帶來的生態貢獻率也較高,達到0.49%,貢獻比重達到6.18%。建設用地轉為草地、林地所帶來的生態貢獻率分別為0.95% 與0.37%,貢獻比重分別為12.07% 與8.44%。上述情況一方面是由于建設用地向次二種地類轉化的面積較大,另一方面歸因于建設用地與草地、林地之間生態背景值差值較大。其他用地向林地的轉換雖規模較小,僅達到1801hm2,但由于其他用地同林地之間所具有的生態背景值差異巨大,因此其他用地向林地的轉換也帶來了0.29% 的生態貢獻率與3.75%的貢獻比重。其余用地轉型所帶來的生態貢獻率皆小于0.1%,貢獻比重皆小于1%,因此對區域生態環境質量提升所產生的影響較小。從總體上看,林地面積的提升對于生態貢獻率的提高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草地次之。
從負效應來看,導致伊金霍洛旗生態環境質量下降的用地轉換類型主要包括草地向耕地、建設用地、其他用地轉換與林地向草地、耕地與建設用地轉換兩類。可以看出草地與林地的轉出是導致生態環境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草地向建設用地轉化所導致的負效應最為顯著,其負向生態貢獻率低至-1.72%,負向貢獻比重低至-25.22%;同時,草地向耕地、其他用地的轉化也對區域生態環境造成了顯著的不利影響,所帶來的負向生態貢獻率分別為-1.22% 與-0.39%,負向貢獻比重分別為18.04%與-5.67%。其次,林地向草地轉化所造成的負向生態貢獻率低至-1.67%,負向貢獻比重低至-24.48%,主要是由于林地向草地的轉化面積較大,達到45796 hm2,同時,林地向建設用地、耕地、其他用地的轉化也使得區域生態環境質量下降,所帶來的負向生態貢獻率分別為-1%、-0.55% 與-0.1%,負向貢獻比重分別為-14.62%、-8.12%與-1.54%。其余地類轉化所造成的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負貢獻率均高于-0.1%,負貢獻比重均高于-1%,因此對于區域生態環境質量負面影響較小。
3.4 土地利用變化多情景模擬
基于2010—2020年伊金霍洛旗土地利用變化情況,本文模擬了自然發展情景和生態保護情景下2030 年伊金霍洛旗土地利用結構(表6 和圖5)。2030年,在自然發展情景下,耕地、林地、建設用地呈現擴張趨勢,其變化率分別為0.69%、8.11%、與16.87%。其中,建設用地擴張最為顯著,耕地擴張幅度最小。園地、草地、濕地、與其他用地面積縮小,其變化率分別為-1.33%、-7.52%、-22.08%、-9.85%, 其中濕地面積減少幅度最大。在生態保護情境下,林地呈現擴張趨勢,變化率為22%,起到了保護生態環境的目的。其他地類面積均呈縮減的趨勢,其中濕地縮減幅度最大、建設用地次之。
從空間上看,生態保護情景下林地相對于自然發展情景具有明顯差異,具體表現為生態保護情境下林地斑塊總體擴張明顯、密度提升,林地斑塊的擴張侵占了大量草地斑塊,該現象在伊金霍洛旗中部與南部地區最為顯著。生態保護情景下建設用地斑塊相較于自然發展情景呈現收縮趨勢,該現象在區域東部最為顯著。
4 討論
2010—2020年,伊金霍洛旗土地利用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地類變化對區域生態環境產生了顯著影響。本文對伊金霍洛旗地區土地利用結構特征、土地利用變化及其生態環境影響進行了分析,并運用PLUS模型對2030年自然發展和生態保護情景下的區域土地利用變化進行了模擬研究。依據研究所得結論,本文深入剖析伊金霍洛旗土地利用特征形成的內在根源,并對該地區未來土地利用走向展開前瞻性思考與探討。
農牧交錯帶是介于農耕區與畜牧區之間的地帶,但農牧交錯帶并非僅具有生產方式上的過渡、交錯特征,更具有自然地帶上的邊緣、過渡的特征。在地理學中這一環境地帶屬于生態敏感帶,而此種生態敏感的特性顯著影響到了區域的土地覆被[33]。伊金霍洛旗處于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在農牧交錯帶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下,草地成為了該地區的優勢地類,該地類面積廣泛、分布廣闊,生態適應性較強。但地區干旱缺水、風力侵蝕顯著的自然資源特征使得草地面臨極大的退化風險,草地的保有對于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林地面積的保有是開展區域生態保護與治理工作的有效抓手[34-35]。農牧交錯帶的自然地理特征造成了林地立地條件較差的現實問題,但在該區域中,林地對氣候波動尤其是降水量波動的響應弱于草本植物和農作物,可有效緩解農牧交錯帶地區的生態敏感特征。因此,林地面積的擴張對于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
伊金霍洛旗耕地與草地交織分布,并呈現零散分布、斑塊細碎的空間特征。農牧交錯帶中耕地利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處理生產與生態之間的關系。農牧交錯帶生態環境脆弱,氣候波動較大,各類自然資源時空分布不均,不當的耕地利用行為在此類地區極易引發耕地退化、地力衰竭的嚴重后果。因此在此區域開展耕地保護工作的難度較高但意義重大。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應首先從質量與數量兩個方面加強對于草地資源的保護,加大草原保護力度,落實基本草原保護制度。其次,要加強對森林資源的保護與林地面積的保有工作。再次,要加強耕地保護力度,嚴守耕地保護紅線,在保護耕地資源中堅守優質耕地紅線,確保良地良田糧用。最后,要嚴格落實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制度,將國土空間規劃作為區域各類開發、建設、保護工作的基本依據,確保國土空間利用過程中的底線思維、宏觀視野與系統布局,避免區域發展進程中出現無序開發、粗放擴張、破壞生態等不良現象。
5 結論
通過引入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和生態貢獻率開展農牧交錯帶土地利用結構變化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研究,并運用PLUS 模型對2030年自然發展和生態保護情景下的伊金霍洛旗土地利用變化進行了模擬、預測,基于上述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結論:伊金霍洛旗林草面積廣闊、分布廣泛、變化劇烈,十年間大面積的草地轉為林地,造成草地面積下降與林地面積增長。耕地面積穩中有進,體現出了區域耕地保護的力度與效能。其他用地面積減少、建設用地面積增加,體現出了該地區在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方面的措施。濕地、園地面積較小且變化不顯著,并非區域土地利用結構變化的主要因素。
2010—2020年,伊金霍洛旗耕地、園地、林地、建設用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得以提升,而草地、其他用地生態環境質量指數下降,表明該地草地、其他用地生態環境質量下降,其中草地生態環境惡化最為顯著。總體而言,2010—2020年間,伊金霍洛旗整體生態環境質量得以提升,體現了該地生態保護工作的力度與成效。
十年間,對伊金霍洛旗生態環境質量提升具有較高貢獻度的轉化類型分別為耕地轉化為林地、草地,建設用地轉化為林地、草地,其他用地轉化為林地、草地以及草地轉化為林地。其中,草地轉為林地的面積最大,同時所帶來的生態貢獻率最高。從負效應來看,導致伊金霍洛旗生態環境質量下降的用地轉換類型主要包括草地向耕地、建設用地、其他用地轉換與林地向草地、耕地與建設用地轉換兩類。林地、草地的質量保護與數量保有是改善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的重要抓手,其中對于林地的保護尤為重要,而其他各類用地對林地、草地的侵占是導致區域生態環境惡化的主要原因。
預測結果顯示:2030年,在自然發展情景下,耕地、林地、建設用地呈現擴張趨勢,其中,建設用地擴張最為顯著,耕地擴張幅度最小。同時,園地、草地、濕地、與其他用地面積縮小,其中濕地面積減少幅度最大。在生態保護情境下,林地呈現擴張趨勢,其他地類面積均呈縮減趨勢,其中濕地縮減幅度最大、建設用地次之。從空間上看,生態保護情景下林地相對于自然發展情景林地斑塊總體呈現擴張趨勢,該現象在伊金霍洛旗中部與南部地區最為顯著。生態保護情景下建設用地斑塊相較于自然發展情景呈現收縮趨勢,該現象在區域東部最為顯著。
(責任編輯:趙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