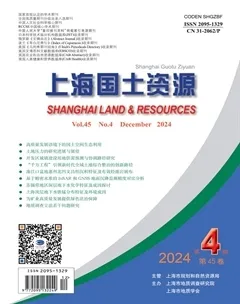國土空間規劃下生態保護格局構建




關鍵詞:生態源地;生態阻力面;生態廊道;生態保護格局
中圖分類號: TU9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1329(2024)04-0087-07
生態保護格局是國土空間開發戰略構建實施的重要組成內容[1],是縣域國土空間保護與修復、開發與利用的行動前提,也是實施空間治理并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基本依據與手段。《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提出國土空間規劃需明確空間發展目標,優化全域布局,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等要求[2]。近年來各地產業發展迅猛,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鄉建設活動日趨頻繁,生態環境壓力也不斷增加,生態保護格局是維護生態平衡、保障生態安全并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3],也是劃分生態保護重點區域、劃定國土綜合整治與生態修復區域、優化生態空間配置的重要依據[4-5]。以人為本的生態保護格局構建原則,是解決城市發展及人類社會面臨的突出問題的主要依據。
生態保護格局構建的要素主要包括生態源地、生態阻力面、生態廊道等,前人對生態源地的選擇采用直接法,將區域內的生態斑塊或者生態保護紅線直接定義為生態源地的方法,合理性不足[4]。對于生態廊道的識別,直接選用軟件的自動識別結果,這很容易忽略自然界原有的生態骨架[6-7]。目前國內關于生態安全格局開展了較多研究[8-10],例如:張曉平等[11] 以江西大余為案例,結合運用生境質量、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等要素識別生態源地并進一步識別生態保護修復關鍵區;吳可等[1] 對山東省進行了生態安全格局的識別及優化;童亮等[12] 通過生態服務功能評估劃定生態源地,利用InVEST軟件計算并模擬市域的生態阻力面,基于電路理論構建生態安全格局。然而,相對生態安全格局,生態保護格局更注重對生態重點區域的識別與研究,對重要生態功能區的保護建設與管護機制的建立具有重要促進作用,目前對區域性國土空間生態保護格局的研究較少。
本研究在借鑒前人[13-16]關于生態保護格局研究的基礎上,綜合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堅持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結合襄城縣目前生態環境所面臨的挑戰及問題,按照生態系統保護連續性的原則,做好與江河湖海等水體、林地、綠地系統、農田等重要生態要素之間的有效銜接與聯通。依據區域協調原則,各種生態要素不可避免的要與周邊地區通過物質、能量、信息交流的耦合而形成復雜的網絡,需要明確其與周邊地區之間各自的功能定位,進一步尋找適合全域發展、滿足生態保護安全的策略與途徑。對重要生態廊道及生態節點進行重要性分析,運用綜合分析法對襄城縣生態源地進行識別,選取生態阻力因子進行生態阻力面的提取,采用軟件識別與自然生態廊道相結合的方法進行生態廊道的確定,從而形成全面、持續、健康的綠色生態空間網絡。確定重要的生態區域,明確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領域,適當設置基礎設施廊道[17-19],同時提出襄城縣縣域整體生態保護格局,以期為市縣級生態系統的保護及縣域生態修復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為實現經濟社會、生態環境的相互協調發展提供一定保障。
1研究區概況
襄城縣位于河南省許昌市,是“中原之中、伏牛之首、汝河之濱”,東側倚靠伏牛山脈,西側接壤黃淮平原,西南部是連綿起伏的伏牛山余脈的淺山區,北邊分布著丘陵地帶,中東部是平原,東部較為低洼,全縣的地勢呈現出西高東低的形勢(圖1),縣域中有紫云山、首山等9座山頭;北汝河、潁河、文化河、柳河等16 條河流,全域呈“九山九崗十六水”的山水資源狀況。全年平均氣溫為14.7℃,縣域風向與季節變化同步,其中冬季大多為偏北風、夏季較為盛行偏南風,西南風在全年中出現的頻率最高。
襄城縣自然保護地面積較小,主要有紫云山森林公園、北汝河國家濕地公園。縣域內水系以北汝河和潁河為主,是淮河水系的一部分,其中流經襄城縣縣域內的北汝河河段面積達到241 km2,過境河段長達46.9km,是許昌市重要的水源地,更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中的備用水源;潁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農業灌溉的重要水源點,潁河沿岸的氣溫相對較高,所以冬季很少結冰。縣域內有首山、令武山、紫云山等山體,山體多為疏林地、草地,水源涵養林較少,森林防護功能有待進一步提升。
2研究方法
基于許昌市雙評價成果中生物多樣性評價、水資源重要性評價、水土保持功能重要性評價體系進行生態源地識別,利用國土調查的土地利用現狀、坡度數據、DEM數據、距水源、道路距離數據進行襄城縣生態綜合阻力面構建,通過對襄城縣國土空間生態源地識別、生態阻力面的構建進行生態廊道和生態戰略節點的識別,進一步構建襄城縣生態保護格局。
2.1生態源地識別
生態源地[1,4,12] 是維系區域生態安全、區域可持續發展等必須保護的地方,也是生態系統與景觀層面保持整體功能,發揮物種擴散、生態功能流動、物質能量信息交換等重要作用的起源點。以往研究簡單將生態斑塊或者保護區作為生態源地的方法[20],主觀性較強,本研究采用定性識別的方法進行襄城縣生態源地識別。基于許昌市的國土空間開發適宜性、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評價結果,運用自然間斷點分級法篩選出襄城縣域范圍內面積較大(面積> 2km2)的圖斑,將這部分圖斑視為襄城縣生態服務功能較好的生態源地,生態用地面積越大,其所發揮的生態規模效應也就越大[21]。
2.2生態阻力面構建
物種遷徙、擴散過程需要穿過一定的“阻力”,生態阻力面所表達的是物種間基因交流、信息傳遞及遷移擴散的難易程度[12,22-24],對構建生態保護格局有重要的作用,生態阻力面構建是計算物種在克服阻力情況下擴散路徑的基礎[25-26]。基于襄城縣域的生態本底現狀,按照不同的影響因子對生態源地擴張過程的相關程度的不同,本次研究選擇相關程度較高的部分影響因子作為構建阻力面的變量,選擇土地利用類型、距鐵路和公路的距離、距水源及河流的距離、坡度、DEM數據作為生態阻力的評價因子[11,27-28]。按照從各個生態源地向其他不同景觀單元擴散的難易大小設定最小阻力值,參考相關文獻設定各種生態因子所對應的基本生態阻力系數[20,27-31](表1)。通過各生態因子綜合阻力值疊加構建襄城縣生態阻力面,用以判斷其他各個景觀單元到生態源地的可達性、連通性等。
2.3生態廊道識別
生態廊道具有較高的生態服務功能[32],主要包括能減輕景觀破碎化的程度、能維系自然界動態的生態過程、能連接分散的動物棲息地等。運用最小累積阻力模型(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33-35]的方法來識別生態廊道,最小累積阻力模型與其他方法相比,適用性強、兼容性較好的優勢很突出,能較好的反映景觀格局的變化、生態過程的演變及其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所以多被應用于生態保護格局的構建。本研究利用ArcGIS10.2平臺的Linkage Mapper工具,把識別的生態源地數據和生成的綜合生態阻力面數據做輸入因素,然后識別襄城縣域內各個生態源地之間的潛在生態廊道。由于襄城縣縣域東部、北部地區生境質量不高,廊道明顯不足,需結合水系建設濱水型生態廊道。結合生態景觀要求,根據河道的不同等級,增加一定的濱水綠化,同時與城市所規劃的防災避難系統相互結合,把水系兩側的綠化場地也作為防災和避難場所、疏導路徑等,但是要禁止在河道溝渠的兩側、水庫的周邊違法占用耕地、永久基本農田等需要保護區域超標準建設生態通道。
2.4生態戰略節點識別
生態戰略節點是區域內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景觀要點,也是區域景觀中對物種遷移、 擴散過程起到關鍵作用的區域,是生態要素交換和聯系的關鍵位置[36-38]。生態戰略節點在廊道網絡中的主要作用就是墊腳石,為生物物種的遷徙提供優良的暫息地,增加景觀之間的連接性,促進各個物種在不同斑塊間的運動,一方面可以形成區域生態安全的關鍵保護點,控制著生態安全重要節點,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改良對應區域的生態環境質量。
3結果分析
3.1生態源地分布情況
襄城縣共識別出23個生態源地,總面積63.01 km2,經過自然間斷點分級法識別出面積大于2 km2 的生態源地共5處(圖2),總面積為59.70 km2,其中極重要區域面積2.43 km2,重要區域57.27 km2。從空間位置上看,生態源地主要位于縣域西南方向,主要分布在紫云鎮、湛北鄉、潁陽鎮、茨溝鄉等位置,依托于襄城縣紫云山、首山、令武山、潁河、北汝河、潁汝干渠區域。將識別的生態源地結果與襄城縣的生態保護紅線范圍相比,發現生態源地內涵蓋生態保護紅線區域,因此該種方法選擇的襄城縣生態源地結果較為合理。襄城縣內所選擇的這些斑塊區域是襄城縣域生物物種的集聚地,同時也是其生存、繁衍的重要棲息地,這些生態斑塊所發揮的生態意義很重要。
3.2生態阻力面分布狀況
綜合土地利用現狀、水源、道路、DEM、坡度等生態因子,形成襄城縣生態綜合阻力面。結果顯示,水系林地等生態用地區域的阻力值較小,水體、森林等用地類型有利于物種遷徙等生命活動,能夠更大程度的發揮水體、森林等用地的生態服務功能,生態流運行暢通。
道路耕地等稍有人為活動參與的區域 ,生態阻力值較高。襄城縣中心城區以及各個城鎮村的建設用地斑塊的生態阻力值最高,主要是因為建設用地多的地方不利于生態流通過,對生物的遷徙等生命活動的影響較為明顯,并且城鎮中人類活動較為集中,人類活動會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其他生物的生存、棲息、遷徙等生命過程,從而阻礙著景觀生態過程的發展(圖3)。
3.3生態廊道構建
根據襄城縣縣域內識別的主要生態源地和最小累積阻力模型生成的襄城縣生態阻力面數據。基于MCR 模型,以任一生態源地為起點,其余生態源地作為目的地,利用ArcGIS 中的成本距離(cost-distance)工具,生成對應的成本回溯鏈接(cost-backtracking link),根據生態源地之間的成本距離和成本回溯鏈接生成成本路徑(costpath),識別出襄城縣域內的生態廊道。結果顯示:襄城縣縣域內共生成7 條生態廊道(圖4),生態廊道總長度為9.54 km,主要分布于縣域西南部區域,連接十里鋪鎮、紫云鎮、湛北鄉、山頭店鎮、潁陽鎮區域,主要依托于北汝河、紫云山、潁河、首山、令武山等生態源地(表2)。
3.4生態戰略節點分布及生態緩沖區建立
基于生態戰略節點的重要性,擬選擇生態廊道連接較多的重要生態源地作為襄城縣生態戰略節點(北汝河、首山、令武山和紫云山森林公園、潁河)(圖5)。生態緩沖區的建立是為了保護生態保育區內存在的自然生態過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為生態緩沖區內的區域是生態敏感性較低的區域,在不影響生態環境的情況下,可以適當開展一定的活動,緩沖區內建立的所有設施及建筑物必須與周邊的自然環境相協調。根據襄城縣的生態源地和生態廊道及生態戰略節點位置,需要設置一定寬度的生態緩沖區,為襄城縣主要山體、河流及生態廊道設置寬度為120m的生態緩沖區,緩沖區之外的區域為一般區域。生態緩沖區的寬度應根據當地的生態現狀等因素確定,一般情況下,生態效益越高,所設置的生態緩沖帶越寬[39],當緩沖帶用以保護動植物棲息地為主要目標時,其寬度最少需要設置120m[40](圖6)。
3.5生態保護格局構建
根據襄城縣生態源地識別、生態阻力面構建、生態廊道自動識別與現實構成、生態戰略節點識別以及生態緩沖區的建立過程,形成襄城縣生態保護格局的構建(圖7)。以紫云山、令武山、首山、北汝河、潁河區域為重要生態源地,以生態源地之間識別出的潛在生態廊道和自然濱水型生態廊道作為生態骨架,以襄城縣內紫云山、首山、令武山、北汝河、潁河作為生態戰略節點,以襄城縣不同因子綜合影響下生成的生態阻力面為生態保護網絡本底,總體形成山、水、林、田、城鄉相互交融的結構,共同構成襄城縣“一屏- 三帶- 多廊道”的全域生態保護格局(表3)。
“一屏”指襄城縣西南方向的紫云山、令武山、首山所形成的山林(伏牛山系)生態屏障,生態源地的面積占比是最大的,其物種也最為豐富,能夠發揮一定的生態功能,其生態功能主要包括水土的保持、生物多樣性的維護、防風固沙等。
“三帶”分別是指沿潁河濕地公園、沿北汝河國家濕地公園和沿潁汝干渠構成的三條水源涵養功能帶,保障了區域的水源涵養功能。
“多廊道”是指識別出的潛在生態廊道及自然濱水型生態廊道,連通襄城縣域內生態源地和重要河流,實現縣域內各種生態環境資源的聯動保護,相互形成連通的生態網絡格局,能夠有效保障區域內的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對于縣域西南部伏牛山系形成的生態屏障,可實施一定的水土保持工程,提高生物多樣性維護保育能力。對于水源涵養功能帶,可以開展河道清淤、河岸綠化和生態護坡等工程,提高防洪、供水等一系列的生態服務功能與價值。生態廊道是串聯各個要素的重要渠道,對于維護生態平衡、生物多樣性、生態安全等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于縣域內的多條生態廊道,采取一定的工程手段加以保護。
4 結論與展望
4.1 結論
該研究采用景觀生態學原理,以河南省許昌市襄城縣為例,運用“生態源地- 生態廊道- 生態保護格局”模型,通過對生態源地識別、生態阻力面構建、生態廊道識別與生態保護格局構建,為襄城縣國土空間規劃生態保護提供系統性的理論支持與借鑒。得到主要的結論如下:
(1)襄城縣識別出面積較大的5處生態源地,總面積達59.70km2,占縣域內總的生態要素面積的90% 以上,占縣域總面積的6% 以上,且襄城縣綜合生境質量水平較高。模型生成的7 條潛在生態廊道總長度為9.54km,由于縣域西北部生態要素較少,因此將自然濱水型生態廊道也納入到總的生態保護格局內,結合識別的5 處生態戰略節點,最終形成縣域“一屏- 三帶- 多廊”的生態保護格局。
(2)紫云山、令武山、首山(均屬于伏牛山系)生態屏障作為生態保護格局的“一屏”,該屏障內生態源地的面積占比是最大的,其物種也最為豐富,能夠發揮水土保持、生物多樣性維護、防風固沙等生態功能。潁河濕地公園、北汝河國家濕地公園和潁汝干渠構成水源涵養功能帶,能夠保障區域的水源涵養需要。多條生態廊道能夠幫助實現縣域內各種生態環境資源的聯動保護,相互形成連通的生態網絡格局,有效保障區域內的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
(3)生態保護格局是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有力措施,也是國土空間規劃的重要內容。襄城縣縣域內用地類型豐富,山水相望,可以作為研究國土空間生態保護格局的典型,為襄城縣建設用地的擴張與布局的優化提供一定的管控要求,同時為同類國土空間生態保護格局的構建提供一定的參考。
4.2展望
國土空間規劃中生態保護格局的構建基于生態學原理及方法基礎,在構建生態保護格局中要注意整體性及系統性的囊括[4]。已有研究發現外部人為因素對構建合理的生態保護格局也會存在一定的影響[12],因此需要從社會、生態、經濟等各方面對生成的保護格局的合理性進行分析探討。生態廊道的寬度對物種遷徙等生命活動有一定的影響,已有研究存在兩種觀點:一方面為生態廊道越寬越好[41],另一方面為廊道過寬會影響生物流動速度[42]。然而,本次研究所識別選擇的生態廊道未能定義其寬度,因此,生態廊道的寬度是今后對生態保護格局研究的重要問題。
此外,為滿足區域建設發展需求,區內土地布局面臨不可避免的優化調整。在此背景下,需要定期對區域內的生態源地、生態廊道、生物多樣性、水環境安全等生態指標進行監測評估,以及時了解生態保護狀況,為規劃編制及優化保護措施等提供科學依據[43]。作為區域內重要的生態資源,生態源地和生態廊道保護和修復對國土空間規劃涉及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體的系統保護及生態文明建設極為重要。生態保護格局構建與生態文明建設之間也存在著相輔相成的關系,通過生態保護格局的構建與管理,可以進一步推動生態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