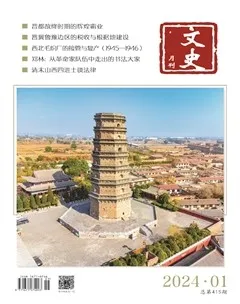清末山西四進士談法律
衛洪平
庚子之亂,將腐朽的大清王朝推向了崩潰的邊緣。慈禧、光緒兩宮倉皇逃至西安,喘息稍定,即下詔變法,開始推行新政。史學家蔣廷黻說:“戊戌年,康有為要輔助光緒帝行的新政,這時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過了。”
新政中倍受關注的便是采納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的上奏,史稱“江楚會奏”。新政變通科舉章程,改革沿襲了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八股文被徹底廢除。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舉行的癸卯科會試,將各國政治、藝學(包括政治、地理、武備、農工、算法之類)列入了必考范圍。后來的殿試策問分為設官分職、明刑弼教、生財之道、環球交通四個方面。其中,明刑弼教和環球交通兩個方面涉及到不少法律知識,尤其是西方的法律。
山西參加癸卯科殿試的共有12人,其中,趙城張瑞璣、平定李慎五、鄉寧吳庚、武鄉李華炳4人的殿試策,不知因何緣故,如今都保存于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東亞圖書館。幾年前,朋友郝岳才給我發來了趙城張瑞璣殿試策的黑白圖版。去年,又有熱心人士把4人殿試策的彩色圖版發到了網上。下面,主要介紹幾份殿試策中論及法律的部分,重點說說張瑞璣的。
李華炳大概屬于國粹派,他在殿試策中寫道:“今萬國交通,刑法各異,西律有合于《周禮》三事。監禁作工,則圜土施職事之法也;重犯充役,則有罪役諸司空之法也;入錢贖罪,則罰鍰之法也。海外之書,暗合古人之遺意,殆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乎?國家法律極為美備,通商以來,外人借口于刑法之重,自設領事以理各埠之詞訟。臣愚以為宜考古制,參用西律,示以大公,勿使有名實不符,致滋疑議。庶口岸自治之權可以漸收歟。”談及外國商律時寫道:“商律一門,西人有專書,所以維持商務,其能致厚利正由于此。”
吳庚偏重公法,文中寫道:“今者東西各國法學大盛,雖殊方異俗,不能變而用之,而按之罪疑惟輕之理,則西律諸書未嘗不可傳也。且中外交涉日多,執我之法,不能律彼之人,嘗有同一罪也,而華民置大辟,西民僅監禁者。然則西律之學亦當務之急也……惟各(國)互市以來,所恃以交涉往來者,此公法耳。持公法以相衡,則彼此轄治之權,自必歸之公論,而不至受其欺。”
李慎五由商戰的害處,進而認識到商律的重要性。他認為:“今者環球共集,其法律之輕重異同,無不昭然可揭……至于商律一門,尤為最急。今日海外各國有以兵為戰者,有以商為戰者,兵戰者害淺,商戰者害深。”

與這三人相比,張瑞璣的視野要更開闊些,思想也更解放。其殿試策全文1310字,文中提出,當此正值“時局艱難之會,強鄰窺伺之秋”,中國應該借鑒英、法、美等國家的法律,尤其是要借鑒其商律,擴大國際貿易,以此帶動國內的經濟發展,實現國家的自立自強。他在文中寫道:“今者東西各國,若英、若法、若美、若德、若意、若俄、若日本,法律之學皆各設專科,其大旨雖不能盡合乎古,而其中亦不無可取焉。要之,刑法者天下之公理也。刑法公,則天下之是非明而人心定;刑法不公,則天下無是非,而人心亦從可知矣。合歷代之律者,萬國之公例,人人之公理,不易之經也。若私法則出于強國,不可言法矣。使臣四集,商人麇來,亦應有一定之律以治之。而轄治之權或屬之人,或屬之地,各歧一是者,何也?蓋東西之律未通,而萬國之法或有內外也。若夫商律,尤西人所亟亟加意者。利之所在,膺充者嚴其禁,中飽者申其罰,故能商賈云興,橫絕四海。今當變法之始,采其意而參合以中例,則商務必日興矣。不惟此也,稅務一宗,內關財政,外系邦交,國計民生,皆視此為消息。其利在減出口稅,加入口稅,則工藝之業亦借此以勸,不獨惠及商旅。之為仁政也。”
在張瑞璣看來,英、法、美等國的法律都分專科,值得我國效法。法律最重要的是公平合理,如果私字當頭、強橫霸蠻,那就稱不上法了。現在,各國使臣會集在中國,各國商人也成群結隊地來了,朝廷應該著手制定相應的法律。西方人尤其重視通商的法律,在通商中禁止什么,懲罰什么,都有明確的條款。我國正處于變法之初,應該借鑒東西方各國的做法,結合國情制定通商法律,這樣的話,“則商務必日興矣”。他又進一步說,稅務“內關財政,外系邦交”,國計民生都要依靠它;在國際貿易中,關鍵是要“減出口稅,加入口稅”,這樣就能盈利,同時國內各類出口商品生產者的積極性也就調動起來了。這才是富民強國的仁政。民富國強了,吏治、民生、國用、邦交才有依靠。文末還引用《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以強化他的觀點。
中國傳統的法律結構是“諸法合體”,一部《大清律例》既是刑法典,又包括了民事、訴訟、行政等法律內容,民與商不分。張瑞璣提出應該仿效上述七國的做法,“采其意而參合于中例”,制定我國的商律。這與同時期刑部左侍郎沈家本和出使美國大臣伍廷芳,受命兼取中西、改革傳統法律結構是一致的。其后不久,朝廷設立修訂法律館,又設商部,出臺《商人通例》,并開始編制《大清商律草案》。這也是新政的一項重要內容。
值得注意的是,張瑞璣殿試策中提出應該學習借鑒的七個國家,都是兩年多前侵入北京,逼迫清政府簽訂《辛丑條約》的“八國聯軍”(未提奧匈帝國)。這樣的眼光和胸襟不能不令人欽佩。
若是再深入一層,我們還可以看到,120年前張瑞璣參加殿試時內心的苦痛和憂郁。他在一首詩中,寫到進京后耳聞目見的,竟是“太平笙歌團圓月”,是“虎神健兒挑酒去,鸚鵡名士駕衣冠”,一派刀槍入庫、馬放南山、歌舞宴樂的景象。于是大聲疾呼:“危堂燕雀釜底魚,袞袞諸公知也無?”又說他要畫出庚子亂離影、殘山剩水圖,“使我四萬萬人同觀之,勿忘此役長自警!”
張瑞璣帶著這樣的心情,走進保和殿。面對“朕將親覽焉”的策問,作出理性的回答:向強敵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