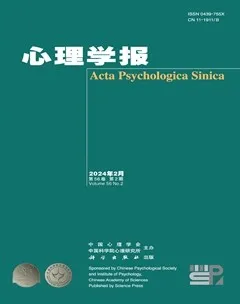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
許麗穎 王學輝 喻 豐 彭凱平
(1 武漢大學心理學系,武漢 430072) (2 清華大學社科學院心理學系,北京 100084)
1 引言
職場物化(objectification)并不鮮見,“工具人”“打工人”“社畜”等流行語的一度風靡已然說明問題。物化源于康德之描述,指“將一個人,即一個有人性的存在,降低為物的地位(Kant,1797/1996,p.209)”。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深化了此概念,并以工具性、否定自主性、惰性、可替代性、可侵犯性、所有權及否認主觀性概括其特征(Nussbaum,1995,1999)。其中,工具性是物化概念的核心(Orehek&Weaverling,2017),并被廣泛研究(如Calogero,2013;Gervais et al.,2014)。究其本質,物化即將人(他人或自身)視為達成目的的工具,否認人性,進而以對待物的方式對待人(許麗穎 等,2022)。物化研究多集中于性物化(如Calogero,2013;Saguy et al.,2010;Schmidt &Kistemaker,2015;Skowronski et al.,2021),但物化之對象顯然并不局限于女性。職場物化便是其一,即在工作場所將人視為物的過程和傾向,主要反映了工作關系中的工具性和對人性的否定(Baldissarri et al.,2017;Belmi &Schroeder,2021;許麗穎 等,2022),是一種負面的人際互動方式和工具理性。職場物化的影響因素一方面與人相關,如權力(Gruenfeld et al.,2008)等,另一方面與工作相關,如工作的重復性等具體特征(Baldissarri et al.,2017)、工作環境的匿名性(Taskin et al.,2019)等。職場物化的測量通常包括顯性測量(如問卷;Belmi&Schroeder,2021)和隱性測量(如IAT;Baldissarri et al.,2017)兩種。職場物化反映了現代工作中的異化現象(Marx,1844/1964)。自工業革命以來,生產力急劇發展,分工勞動成為可能。個體從人變為職場之“工人”,每個人都變為社會分工之“螺絲釘”,當人類勞動從本能變為工具,人由其生產之價值來衡量本身時,異化產生,人遂成工具(Marx,1844/1964)。隨著人工智能技術崛起并滲入生活,機器人甚至一同進入職場工作,它或以程序形式輔助思維決策、或以實體形態提供現實幫助(張語嫣 等,2022)。人機關系逐漸變化、人機界限愈漸模糊,這是否會導致人更將他人物化?
若如此,則當引發憂慮。機器人勞動力的發展若搶占人類勞動崗位,則可能讓人產生“人可被當作工具”的合理化信念,即物化(如 Pew Research Center,2017)。機器人主要可以分為兩種:工業機器人和服務機器人。工業機器人是指“自動控制的,可重新編程的,多用途的機械手,三個或更多的軸可編程,可以固定的地方或移動用于工業自動化應用”(ISO 8373:2012),服務機器人則是指“為人類或除工業自動化應用外的設備執行有用任務的機器人”(ISO 8373:2012)。本研究中的職場機器人既包括工業機器人也包括服務機器人,即在職場環境中出現的、與人類一同工作的各種實體機器人。職場機器人之廣泛使用對人類就業和安全等方面產生威脅,也對人類身份和人類獨特性產生威脅(Yogeeswaran et al.,2016)。畢竟機器人作為一種人造物,即使其智能程度未來能比肩甚至超過人類,它也更可能被當作另一實體,而成為人類的外群體。群際威脅理論(Stephan et al.,2016)表明,外群體會讓人產生現實威脅(realistic threat)與象征性威脅(symbolic threat)。前者為資源威脅,涉及到對內群體的身體傷害以及對內群體權力、資源和福祉的威脅;而后者是指對內群體認同、價值觀和獨特性的威脅(Stephan et al.,2016)。現實威脅自不必說,機器人更易管理,成本也更低(Borenstein,2011)。它既不需要協調復雜人際關系,也不需要支付除購買維護外的工資,甚至其勞動時間還可以更長(McClure,2018)。機器人對于技術工作與體力勞動的替代大于創造性工作,而較為年長、教育程度較低且學習能力較弱的工人更容易被取代(Borenstein,2011)。當然,除了對工作崗位的現實搶占,機器人也可能在互動中對人類安全造成擔憂而產生現實威脅(Murashov et al.,2016)。更重要的是,機器人由于其能力與外觀擬人,造成了認同威脅(即群際威脅理論中的象征性威脅)。機器人的計算與承重等身體能力依然超越人類,造成人類需要認知失調地對待人類的定義性特征問題(喻豐,2020;喻豐,許麗穎,2018);同時,機器人外觀也可擁有和人別無二致的觀感,人與擬人化機器人外貌的模糊,不得不經由擬人化過程(許麗穎 等,2017;喻豐,許麗穎,2020)而造成對人類自身獨特性的認同威脅。
機器人進入職場,讓人感知到現實威脅和認同威脅,人便可能喪失控制感,而保持和強化控制是人面對威脅時的主要反應(Greenaway et al.,2014)。威脅傾向模型(threat orientation model)已然表明,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缺乏是經歷威脅的必然結果(Thompson &Schlehofer,2008)。獲得對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控制是人類基本心理需求,人有控制自身生活的動力(Landau et al.,2015)。一旦控制感受損,則人將力圖進行補償。補償控制理論(compensatory control theory;Kay et al.,2008;Kay et al.,2009;Landau et al.,2015)認為,人們對于減少控制感的事件和認知會采取補償策略,意圖將控制感拉回基線。然如何補償?一種策略是尋求并偏好對世界的簡單、清晰和一致的解釋。物化便是忽視他人復雜的信念、欲求與心理活動,將他人簡單化為具體之物,從而讓人簡單、清晰而一致地解釋他人主觀狀態和外部客觀世界,進而產生控制補償。研究發現,如果男性感覺自己缺乏影響女性的能力,他們就會更傾向于將女性物化,后續在職場情境中的研究也發現,在實驗中那些對自身影響同事的能力產生懷疑的被試更傾向于將同事物化(Landau et al.,2012)。這種控制補償策略被稱為肯定非特定結構(nonspecific structure)的控制補償策略。基于此可知,機器人勞動力對人產生現實威脅與認同威脅,而這兩種感知機器人威脅會導致控制感減弱,為補償控制感,人們采用肯定非特定結構方式作出職場物化。
當然,肯定非特定結構是相對于控制補償的其他三種策略而言的,即加強個人能動性(personal agency)、支持外部能動性(external agency)以及肯定特定結構(specific structure) (Landau et al.,2015)。肯定特定結構是指人們傾向于相信做出特定的行為能夠可靠地產生預期結果,而此從行為到結果的清晰路徑是針對減少感知控制的具體情境的。舉例而言,如果人們在感知到機器人威脅時采用肯定特定結構的策略來補償感知控制,那么人們可能會相信某種與機器人密切相關的“行為-結果”,如他們拔掉機器人的電源(行為)就一定能夠控制住機器人(結果)。特定結構即指機器人本身,而物化人類則是肯定非特定結構,即不直指對人類造成威脅的機器人本身。加強個人能動性是指“認為一個人擁有必要的資源來執行產生特定結果或達到特定目的所需的一種或一組行為的信念”(Landau et al.,2015),如自我肯定自身能夠控制機器人的資源和能力,認為自己比機器人的能力更強,可以指揮機器人做自己安排的工作等。而支持外部能動性則表明個體可以依賴自我以外的系統,如將個體能動性交付于神或者政府,相信外部系統會調動資源來實現個體目的,以此重獲掌控。換言之,人們也能在感知到機器人威脅時更加支持政府或者更加信仰神,以此相信政府或神能夠控制機器人并保護他們。肯定非特定結構與這三種策略均不相同,它不直接針對個人對自身資源的信念,也不直接針對個人對外部系統的信念,它針對的是社會和物理環境的某些方面,而這些方面不在感知控制減少的具體情境范圍內(許麗穎 等,2022)。但因為后三種控制補償策略或曰信念依然能夠恢復因感知機器人威脅而受損的控制感,因此其應能調節感知機器人威脅導致的職場物化結果。
雖然依社會認同路徑而推導的感知機器人威脅會造成職場物化的結果合乎邏輯,且威脅會對人際關系造成負面影響是直覺所知(許麗穎 等,2022),即威脅會產生負面人際結果,如增加人們對物質的不安全感,則會導致他們更多地感知到移民和外國工人的威脅,從而增加對反移民政策的支持(如Frey et al.,2018;Im et al.,2019),但于機器人而言依然存在爭議。例如也有研究發現,機器人勞動力作為外群體能夠凸顯人類的共同身份,從而減少對人類外群體的偏見(Jackson et al.,2020)。有趣的是,在同一研究中,從37 個國家所收集的數據表明,過去42 年自動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對外群體的外顯偏見也增加了,這一影響在一定程度上與不斷上升的失業率有關(Jackson et al.,2020)。這也側面表明,機器人可能會因其對人類產生的失業等威脅而對人際關系造成負面影響。因此,本文對于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影響的探討,一方面有助于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大背景下更好地深入理解職場物化這一熱點社會問題和物化研究核心議題(許麗穎 等,2022),另一方面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人工智能以何種方式影響人際關系這一尚存爭議的重要話題,并通過對職場中機器人負面影響的關注預警現實問題。
本文分為3 個遞進研究,基本假設是感知機器人威脅會增加人們對同事的職場物化,其中控制補償(控制感)作為中介機制,而其他補償策略則會調節其效應。研究1 用2 個子研究探討感知機器人威脅是否會增加職場物化,在現實中和在網絡上重復驗證該現象的存在,證明這一現象的穩健性,并排除人類共同身份(泛人類主義)的作用。研究2 包括3 個子研究,探究感知機器人威脅為何會增加職場物化,即驗證控制補償的中介機制,解釋這一現象的發生原因,并通過不同的操作方式驗證。研究3包括3 個子研究,基于控制補償理論所提出的補償控制策略,將個體能動性、外部能動性、特定結構信念作為調節變量,探討這一現象存在的邊界。
2 研究1:感知機器人威脅與職場物化的關系
研究1 包含兩個子研究以證明感知機器人威脅與職場物化的初步關系,其中研究1a 采用實際機器人公司中的高生態效度樣本以量表相關證明其初步關系,而研究1b 則采用操縱自變量的實驗方法考察其因果關系,并排除泛人類主義影響。
2.1 研究1a:感知機器人威脅與職場物化的相關
2.1.1 被試
從3 家知名的機器人公司中實地采集數據。研究共招募1587 名被試,排除未填完以及未通過注意檢查者共361 人,最終有效被試為1226 人,其中男性830 名(67.7%),女性396 名(32.3%),平均年齡31.38±7.01 歲。所有被試自愿參加實驗并知情同意。
2.1.2 材料
感知機器人威脅。采用Yogeeswaran 等人(2016)編制的感知機器人威脅量表。該量表有兩個維度: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和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每個維度包含5 個條目。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的條目如下:(1)“我們日常生活中機器人使用的增加正在導致人類失業”;(2)“機器人無法代替人們的工作”;(3)“從長遠來看,機器人對人類的安全和福祉構成直接威脅”;(4)“機器人技術的發展會威脅人類的就業和機會”;(5)“機器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日益普及對人類安全構成了威脅”。其中條目2 為反向計分。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的條目如下:(1)機器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使我感到困擾,因為它模糊了人類和機器之間的界限;(2)看起來有生命的機器人是令人不安的,因為它們與人類幾乎無法區分;(3)技術的最新進步對人類的本質提出了挑戰;(4)機器人領域的技術進步正威脅著人類的獨特性;(5)機器人開始模糊人類與機器之間的界限。量表為Likert7點量表,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本研究中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4。
職場物化。職場物化的測量基于 Belmi 和Schroeder (2021)的研究進行修改(將條目中的主體修改為“同事”)。量表包含7 個條目,囊括了物化特征的7 個維度(Nussbaum,1999),修改后的具體條目如下:(1)我重不重視某個同事,主要是看他/她能為我做些什么;(2)我很少關注同事的希望和意愿;(3)我認為同事對我來說是可替代的;(4)我會迫使同事去做我想讓他/她做的事;(5)我會把同事當做一個工具來對待;(6)我會關心同事的感受,因為我真的在乎他/她的人格;(7)哪怕同事不同意我的意見,我也會繼續我自己的計劃。其中條目6 為反向計分。量表為Likert7 點量表,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1。
為了進一步增強研究結果的穩健性,研究還加入了以下控制變量:(1)工作場所是否有機器人:是/否;(2)每天平均與機器人打交道的時長(以小時為單位);(3)對機器人的熟悉程度(Leo &Huh,2020):你對機器人有多熟悉?(1=一點也不,5=非常)、與普通中國人相比,你認為你對機器人有多了解?(1=一點也不,5=非常);(4)主觀社會階層(Adler et al.,2000)。以及性別、年齡、職位、學歷、公司幾項人口統計學變量。
2.1.3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與檢驗
本研究通過采用匿名數據收集、部分項目反向計分等措施從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龍立榮,2004)。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未旋轉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共3 個,最大因子方差解釋率為31.22% (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1.4 結果
職場物化與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呈顯著正相關(r=0.15,p< 0.001),與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也呈顯著正相關(r=0.18,p< 0.001)。加入性別、年齡、工作場所是否有機器人、交互時長、機器人熟悉度和主觀社會階層作為協變量后,職場物化與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以及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仍然均呈顯著正相關(r現實=0.16,r認同=0.20,ps < 0.001)。
2.2 研究1b: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
2.2.1 被試
通過軟件G*Power 3.1 來確定所需樣本量,根據已有關于機器人勞動力相關研究(Jackson et al.,2020),取中等效應量f=0.2,顯著性水平α=0.05,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需要共266 名被試才能達到90%的統計檢驗力。由于研究職場物化,研究設置了填寫條件為目前在職,并且考慮到注意檢查會排除掉一些被試,因此共在Credamo 平臺上共計招募了507 名被試。其中106 名被試沒有通過注意檢查,最終被試量為401 人。被試平均年齡為29.41歲(SD=5.24),女性201 名(占50.1%)。
2.2.2 過程
本研究為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被試被隨機分配到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男性94 人,女性96人)或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男性106 人,女性105人)。參考已有研究(Jackson et al.,2020)的操縱材料,制作了兩張不同的新聞網頁圖片。如圖1,在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被試閱讀了一篇名為“機器人:取代人類勞動力?”的科技新聞,新聞描述了機器人如何越來越多地搶走人類的工作。在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被試閱讀了一篇名為“機器人:只是一時流行?”的科技新聞,文章描述了機器人永遠無法取代大多數人類工作。兩個新聞網頁的布局、新聞的長度和格式都是相同的。被試看完新聞材料后填寫了機器人威脅量表作為操縱檢查(測量同研究1a,在本研究中,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85,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9)。

圖1 感知機器人威脅的操縱材料
在實驗之前,我們還提前選擇了3 種不同的辦公場景,并分別請不同的男性和女性在場景中拍攝,共拍攝了6 張員工工作照片(見圖2,已獲得授權)。研究者告訴被試,這是一項“社會知覺研究”,他們將看到一篇科技新聞和一些照片,每張照片中有不同的人,請被試想象他們正在照片所示的環境中與照片中的人一同工作,即照片中的人是他們的同事。6 張照片呈現的順序是隨機的,被試看到每張照片后都填寫相應的問卷(職場物化的測量同研究1a,將對6 張照片的得分平均后,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8),重復這個過程,直到對6 張照片后的問題都回答完畢。

圖2 職場物化對象圖片材料
接下來,被試填寫泛人類主義測量,采用McFarland 等(2012)編制的泛人類主義量表。被試被呈現6 組圖形,每組圖形都有兩個圓圈,但圓圈的重疊程度各不相同。其中一個圓圈代表“自我”,另一個圓圈則代表“人類”。被試被要求選擇最能代表他們如何看待他們自身與全人類之間關系的圖形。例如,選擇兩個完全獨立的圓圈表示被試認為自身與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隔絕,而選擇兩個完全重疊的圓圈則表示被試與所有其他人類的極度親密。
之后填寫控制變量。與研究1a 不同,本研究使用圖片材料作為被試想象的工作場景和物化對象,因此不涉及工作具體屬性和工作場所環境的控制變量。參考已有關于職場物化的研究(Belmi &Schroeder,2021),主要的控制變量為權力和照片中人物的特點,具體條目如下:(1)自身權力:“這張照片讓我感到強大”(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2)社會階層:你認為照片中的人處于(1 為低社會階層,7 為高社會階層);(3)吸引力:你認為照片中的這個人的外表有吸引力嗎?(1 為一點也沒有吸引力,7 為非常有吸引力);(4)尊重:一般來說,你認為人們會尊重照片中的這個人嗎?(1 為絕對不尊重,7 為絕對尊重);(5)物化對象權力:你認為照片中的這個人有權力嗎?(1 為一點也沒有權力,7 為非常有權力);(6)喜歡:僅僅是看著照片中的這個人,你有多喜歡他/她?(1 為一點也不喜歡,7 為非常喜歡)。
接著進行注意檢查,以上量表中穿插了兩道注意檢查題目,如“本題請選擇非常同意”。此外,還對操縱材料的內容進行了注意檢查,題目如下:(1)根據研究,現在機器人占據的工作崗位比例(1 為很大,2為很小);(2)根據這項研究作者的說法,機器人能力和智能的進步所需的時間將比預期(1 為更長,2為更短)。
最后填寫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年收入、職位級別和工作單位類型六項人口統計學信息。
2.2.3 結果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現實威脅(M=4.69,SD=0.99)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3.10,SD=0.98),F(1,399)=260.72,p< 0.001,=0.40;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認同威脅(M=4.43,SD=1.26)也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3.22,SD=1.19),F(1,399)=97.31,p< 0.001,=0.20,表明操縱有效。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職場物化(M=3.54,SD=1.01)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3.32,SD=0.92),F(1,399)=4.94,p=0.027,=0.01。這一結果是穩健的。控制了被試的性別、年齡以及年收入后,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職場物化(M=3.53,SD=1.01)仍然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3.32,SD=0.92),F(1,395)=5.19,p=0.023,=0.01。繼續加入權力作為控制變量,結果表明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職場物化(M=3.53,SD=1.01)仍然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3.32,SD=0.92),F(1,394)=6.02,p=0.015,=0.02。再加入對于照片中人物的評價作為控制變量,結果表明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職場物化(M=3.53,SD=1.01)仍然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3.33,SD=0.92),F(1,389)=4.01,p=0.046,=0.01。
對泛人類主義進行檢驗,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泛人類主義(M=4.32,SD=1.14)與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4.28,SD=1.11)無顯著差異,F(1,399)=0.10,p=0.748,<0.001。并且,將泛人類主義作為控制變量,結果表明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職場物化(M=3.54,SD=1.01)仍然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3.33,SD=0.92),F(1,389)=4.88,p=0.028,=0.01。
3 研究2: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研究2 包含3 個子研究,研究2a 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探討控制感在感知機器人威脅兩個維度(現實威脅與認同威脅)影響職場物化中的中介作用;研究2b 用實驗操縱感知機器人威脅(不區分維度)的方式重復了這一中介作用;研究2c 則分別啟動機器人現實威脅與機器人認同威脅,來考察控制感究竟在哪種威脅條件下起中介作用。
3.1 研究2a:控制感在感知機器人威脅影響職場物化中的中介作用(問卷研究)
3.1.1 被試
本研究采用G*Power 3.1 軟件(Faul et al.,2007)確定所需樣本量,對于本實驗適用的相關分析,參考研究1 的相關分析結果取較小效應量p=0.16,顯著性水平α=0.05,要達到90%的統計檢驗力至少需要402 名被試。考慮到可能有被試中途退出或未通過注意檢查,因此本研究在兩所高校共招募了480 名本科生參與此研究,完成后可獲得相應課程學分。被試通過Qualtrics 平臺填答網絡問卷,并在研究正式開始前閱讀了指導語并知情同意。最終共75 名被試未完成研究或未通過注意檢查,得到有效數據405 份,其中女性213 名(52.6%),所有有效被試的平均年齡為18.75 歲(SD=1.61)。
3.1.2 過程
感知機器人威脅(在本研究中,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7,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1)與職場物化(由于本研究的被試為本科生,因此該測量前加入以下指導語:“請想象你畢業后進入一家公司工作,你有許多同事,請選擇你對以下陳述的同意程度”,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1)的測量同研究1a。
控制感的測量采用Lachman 和Weaver (1998)編制的控制感問卷的中文修訂版(楊沈龍 等,2016)。該問卷包含兩個可相加的維度:掌控感和限制感(反向計分),分別為4 個條目和8 個條目,共12 個條目。掌控感的條目如下:(1)“任何我決心要做的事情,我幾乎都能做到”;(2)“我要是真想做一件事,一般都能夠找到成功的辦法”;(3)“我能否得到我想要的東西,在我的掌控之中”;(4)“我的未來如何,主要取決于我自己”。限制感的條目如下:(1)“我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多半是由他人決定的”;(2)“對于我生活中很多重要的事情,我都無法改變”;(3)“在處理生活中的一些問題時,我常感到無助”;(4)“我生活中所發生的事情常常在我的掌控之外”;(5)“當我想去做某件事情時,總會受到其他事情的干擾”;(6)“我幾乎不能控制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7)“我真的沒有辦法來解決我所有的問題”;(8)“有時我感到在生活中我被別人支使來、支使去”。量表為Likert 7 點量表,1 為完全不同意,7 為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明控制感越高。在本研究中,全部條目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3。測量條目中穿插有注意檢查題目,最后填寫人口統計學信息。
3.1.3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與檢驗
本研究通過采用匿名數據收集、部分項目反向計分等措施從程序上控制共同方法偏差(周浩,龍立榮,2004)。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對數據進行共同方法偏差檢驗,未旋轉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 的因子共8 個,最大因子方差解釋率為16.75% (小于40%),因此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1.4 結果
相關分析結果表明,職場物化與感知機器人威脅及其兩個維度均呈顯著正相關(r現實=0.12,p=0.017;r認同=0.18,p< 0.001),職場物化與控制感及其兩個維度均呈顯著負相關(r控制=-0.12,p=0.020;r掌控=-0.12,r限制=-0.23,p< 0.001)。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與控制感呈顯著負相關(r=-0.11,p=0.025),而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與控制感負相關不顯著(r=-0.07,p=0.152)。
為了驗證控制感是否在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使用 SPSS 的PROCESS 程序進行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檢驗(Hayes,2013),選擇模型4,反復抽樣5000 次。在95%的置信區間下,將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作為自變量,將職場物化作為因變量,將控制感作為中介變量,做中介效應分析。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不包含0,因此控制感中介了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間接效應=0.02,SE=0.01,95% CI [0.002,0.038]),在控制了控制感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直接影響仍然顯著(直接效應=0.11,SE=0.03,95% CI [0.042,0.170]),說明控制感起部分中介作用。
3.2 研究2b:控制感在感知機器人威脅影響職場物化中的中介作用(實驗研究)
3.2.1 被試
本研究通過軟件G*Power 3.1 來確定所需樣本量,根據已有關于機器人勞動力相關研究(Jackson et al.,2020),取中等效應量f=0.2,顯著性水平α=0.05,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需要共266 名被試才能達到90%的統計檢驗力。由于研究職場物化,因此設置了填寫條件為目前在職,并且考慮到注意檢查會排除掉一些被試,在Credamo 平臺上共計招募了359 名被試。其中62 名被試沒有通過注意檢查,最終被試量為297 人。被試平均年齡為31.52歲(SD=5.68),女性184 名(占62.0%)。
3.2.2 過程
本研究為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被試被隨機分配到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或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在最終有效被試中,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148 人,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149 人。被試所閱讀的操縱感知機器人威脅程度的實驗材料同研究1b,被試看完材料后填寫了機器人威脅量表(感知機器人威脅的測量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現實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2,認同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2)作為操縱檢查。然后進行控制感測量(測量工具同研究2a,在本實驗中,控制感全部條目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和職場物化測量(職場物化的測量同研究1a,本實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測量條目中穿插有注意檢查題目,最后填寫人口統計學信息。
3.2.3 結果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M=4.83,SD=1.11)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2.83,SD=1.14),F(1,295)=210.81,p< 0.001,=0.42;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M=4.49,SD=1.37)也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2.91,SD=1.25),F(1,295)=108.42,p< 0.001,=0.27,表明操縱有效。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職場物化(M=2.85,SD=0.90)顯著高于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M=2.64,SD=0.65),F(1,295)=5.49,p=0.020,=0.02。相關分析結果表明,感知機器人威脅程度(低威脅組=0,高威脅組=1)與控制感呈顯著負相關(r=-0.14,p=0.018),與職場物化呈顯著正相關(r=0.14,p=0.020),控制感與職場物化呈顯著負相關(r控制=-0.50,p< 0.001)。
為了驗證控制感是否在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使用SPSS 的PROCESS程序進行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檢驗(Hayes,2013),選擇模型4,反復抽樣5000 次。在95%的置信區間下,將感知機器人威脅作為自變量(低感知機器人威脅組=0,高感知機器人威脅組=1),將職場物化作為因變量,將控制感作為中介變量,做中介效應分析。中介效應檢驗結果顯示,95%的置信區間不包含0,因此控制感中介了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間接效應=0.11,SE=0.05,95% CI[0.020,0.228]),在控制了控制感后,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直接影響不再顯著(直接效應=0.11,SE=0.08,95% CI [-0.051,0.266]),說明控制感起完全中介作用。
3.3 研究2c:控制感在不同威脅影響職場物化中的中介作用(實驗研究)
3.3.1 被試
本研究通過軟件G*Power 3.1 來確定所需樣本量,根據已有關于機器人勞動力相關研究(Jackson et al.,2020),取中等效應量f=0.2,顯著性水平α=0.05,單因素三水平被試間設計需要共321 名被試才能達到90%的統計檢驗力。由于研究職場物化,因此設置了填寫條件為目前在職,并且考慮到注意檢查會排除掉一些被試,在Credamo 平臺上共計招募了359 名被試。其中10 名被試沒有通過注意檢查,最終被試量為349 人。被試平均年齡為31.49歲(SD=7.14),女性196 名(占56.2%)。
3.3.2 過程
本研究為單因素三水平被試間設計,被試被隨機分配到現實威脅組、認同威脅組和對照組,在最終有效被試中,現實威脅組115 人,認同威脅組117 人,對照組117 人。
為了對感知機器人威脅程度進行操縱,被試首先需要根據一段指導語進行寫作,其中現實威脅組的指導語如下:
“隨著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如今所有行業超過50%的工作都已經被機器人所占據,未來機器人將必然作為新的工作者與人類進行競爭,對人類產生了現實生活中的威脅。在不久的未來,機器人還會勝任更多高層次工作,進入人類工作的各個領域,最終取代人們現在從事的許多工作,對人類造成更大的現實威脅。請想象并描述你目前的工作崗位現在或以后如何被機器人所威脅和取代,以及被威脅和取代之后你將會面臨的情況(不少于100 字)。”
認同威脅組的指導語如下:
“隨著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機器人與人類的相似度越來越高,人與機器會變得難以區分。在外形方面,許多機器人與人類的外形相似度極高,看起來跟真人一模一樣,甚至難以區分;在能力方面,許多機器人能力與人類相當甚至超過人類,對人類的獨特性產生了威脅。人工智能技術也會將人和機器進行結合,在未來可能很難定義什么是人、什么是機器人。請想象并描述一個與人類高度相似甚至無法區分的機器人會對你作為人類一員的獨特性所產生的威脅,以及被威脅之后你將會面臨的情況(不少于100 字)。”
對照組的指導語如下:
“隨著人工智能的發展,機器將會協助人類進行許多社會活動。請想象并描述一個未來機器人協助人類的場景(不少于100 字)。”
在完成寫作任務后,被試依次填寫感知機器人威脅量表(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現實威脅維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數為 0.82,認同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8)、控制感問卷(同研究2a,在本實驗中,控制感全部條目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0)和職場物化量表(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7),量表中穿插有注意檢查題項如“本題請選擇非常不同意”,最后填寫人口統計學信息。
3.3.3 結果
以組別(對照組=1,現實威脅組=2,認同威脅組=3)作為自變量,以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作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組別的主效應顯著,F(2,346)=44.35,p< 0.001,=0.20。事后多重比較(Bonferroni)表明,對照組的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評分(M=3.70,SD=0.99,95% CI[3.52,3.88])顯著低于現實威脅組(M=4.55,SD=0.96,95% CI [4.38,4.73])和認同威脅組(M=4.85,SD=0.95,95% CI [4.68,5.03]),ps < 0.001,而現實威脅組和認同威脅組的差異不顯著,p=0.057。以組別作為自變量,以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作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組別的主效應顯著,F(2,346)=52.35,p< 0.001,=0.23。事后多重比較(Bonferroni)表明,對照組的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評分(M=3.54,SD=1.26,95% CI [3.31,3.77])顯著低于現實威脅組(M=4.47,SD=1.10,95%CI [4.27,4.68])和認同威脅組(M=5.07,SD=1.10,95% CI [4.87,5.27]),ps < 0.001;并且,認同威脅組的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評分顯著高于現實威脅組,p<0.001。這表明,操縱效果基本符合預期,其中認同威脅的操縱對于感知機器人威脅的增加效果較強。以感知機器人威脅(即組別;對照組=1,現實威脅組=2,認同威脅組=3)作為自變量,以職場物化作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感知機器人威脅的主效應顯著,F(2,346)=3.68,p=0.026,=0.02。事后多重比較(Bonferroni)表明,認同威脅組的職場物化評分(M=3.11,SD=0.82,95% CI [2.96,3.26])顯著高于對照組(M=2.85,SD=0.72,95% CI [2.72,2.98]),p=0.028,而現實威脅組與對照組以及認同威脅組均無顯著差異,ps > 0.05。為了驗證控制感是否在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使用SPSS 的PROCESS程序進行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檢驗(Hayes,2013),選擇模型4,反復抽樣5000 次。在95%的置信區間下,以感知機器人威脅作為自變量(對照組=1,現實威脅組=2,認同威脅組=3)并將其在程序中設置為分類變量,以職場物化作為因變量,以控制感作為中介變量,做中介效應分析。結果表明,在以對照組為參照時,現實威脅組通過控制感對職場物化的中介效應值為0.064,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025,0.166],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不顯著;認同威脅組通過控制感對職場物化的中介值為0.116,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027,0.215],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且加入中介變量控制感后,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直接效應為0.132,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030,0.330],包含0,表明其直接效應不再顯著,控制感起完全中介作用。以上結果表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會增加職場物化,這是由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會降低人們的控制感,進而使人更傾向于物化職場中的他人。
4 研究3:補償控制策略作為感知機器人威脅與職場物化關系的調節
研究3 包括3 個平行子研究,分別考察個體能動性、外部能動性、特定結構信念是否能夠作為調節變量影響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作用。3個子研究均采用實驗操縱方式進行,其中研究3a將感知機器人威脅的操縱分為了現實威脅與認同威脅,結合研究2 中現實威脅的不顯著結果和研究3a 中現實威脅的陰性結果,在研究3b 與研究3c 在考察調節時均只采用認同威脅與對照組對比。
4.1 研究3a:個人能動性的調節作用
4.1.1 被試
采用軟件G*Power 3.1 來確定本研究所需的樣本量,根據已有關于機器人勞動力相關研究(Jackson et al.,2020),取中等效應量f=0.2,顯著性水平α=0.05,單因素三水平被試間設計需要共321 名被試才能達到90%的統計檢驗力。由于研究職場物化,因此設置了填寫條件為目前在職,并且考慮到可能有被試無法通過注意檢查,并在Credamo 平臺上共計招募了340 名被試。其中10 名被試沒有通過注意檢查,最終被試量為330 人。被試平均年齡為31.56 歲(SD=7.25),女性179 名(占54.2%)。
4.1.2 過程
本研究為單因素三水平被試間設計,被試被隨機分配到現實威脅組、認同威脅組和對照組,在最終有效被試中,現實威脅組110 人,認同威脅組110 人,對照組110 人。對現實威脅組、認同威脅組和對照組的操縱過程同研究2c。在完成寫作任務后,被試依次填寫感知機器人威脅量表(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現實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1,認同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0)、控制感問卷(同研究2a,在本實驗中,控制感全部條目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個人能動性量表和職場物化量表(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1)。
個人能動性的測量一部分改編自以往的補償控制文獻(Beck et al.,2020;Shepherd &Kay,2018),并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和情境進行了相應修改。這部分測量共包括3 個條目:(1)我認為我自己可以決定對機器人的控制;(2)我認為我對控制機器人有責任;(3)我認為控制機器人在我的掌控之中。另外,還根據補償控制理論中個人能動性的定義,即“認為一個人擁有必要的資源來執行產生特定結果或達到特定目的所需的一種或一組行為的信念”(Landau et al.,2015),補充編制了3 個條目:(1)我認為我可以控制機器人;(2)我認為我有能力可以控制機器人;(3)我認為我有資源可以控制機器人。以上測量個人能動性的條目均為Likert7 點量表,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量表中穿插有注意檢查題項如“本題請選擇非常不同意”,最后填寫人口統計學信息。
4.1.3 結果
以組別(對照組=1,現實威脅組=2,認同威脅組=3)作為自變量,以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作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組別的主效應顯著,F(2,327)=22.44,p< 0.001,=0.12。事后多重比較(Bonferroni)表明,對照組的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評分(M=3.93,SD=1.04,95% CI[3.73,4.12])顯著低于現實威脅組(M=4.71,SD=1.04,95% CI [4.51,4.90])和認同威脅組(M=4.74,SD=0.98,95% CI [4.55,4.92]),ps < 0.001,而現實威脅組和認同威脅組的差異不顯著,p=1。以組別作為自變量,以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作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組別的主效應顯著,F(2,327)=22.06,p< 0.001,=0.12。事后多重比較(Bonferroni)表明,對照組的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評分(M=3.83,SD=1.43,95% CI [3.56,4.10])顯著低于現實威脅組(M=4.55,SD=1.28,95% CI[4.31,4.79])和認同威脅組(M=5.00,SD=1.24,95% CI [4.76,5.23]),ps < 0.001;并且,認同威脅組的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評分顯著高于現實威脅組,p=0.037。這表明操縱效果基本符合預期,其中認同威脅的操縱對于感知機器人威脅的增加效果較強。
以感知機器人威脅(即組別;對照組=1,現實威脅組=2,認同威脅組=3)作為自變量,以職場物化作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感知機器人威脅的主效應顯著,F(2,327)=4.76,p=0.009,=0.03。事后多重比較(Bonferroni)表明,認同威脅組的職場物化評分(M=3.23,SD=0.93,95% CI [3.06,3.41])顯著高于對照組(M=2.88,SD=0.71,95% CI [2.74,3.02]),p=0.007,而現實威脅組與對照組以及認同威脅組均無顯著差異,ps > 0.050。
為了驗證控制感是否在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使用SPSS 的PROCESS程序進行偏差校正的Bootstrap 檢驗(Hayes,2013),選擇模型4,反復抽樣5000 次。在95%的置信區間下,以感知機器人威脅作為自變量(對照組=1,現實威脅組=2,認同威脅組=3)并將其在程序中設置為分類變量,以職場物化作為因變量,以控制感作為中介變量,做中介效應分析。在以對照組為參照時,現實威脅組通過控制感對職場物化的中介效應值為0.107,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001,0.244],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不顯著;認同威脅組通過控制感對職場物化的中介值為0.133,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024,0.268],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應顯著;且加入中介變量控制感后,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直接效應為 0.217,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021,0.412],不包含0,表明其直接效應仍然顯著,控制感起部分中介作用。以上結果表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會增加職場物化,這是由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會降低人們的控制感,進而使人更傾向于物化職場中的他人。
為了驗證個人能動性是否在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調節作用,使用 SPSS 的PROCESS 程序進行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檢驗(Hayes,2013),選擇模型1,反復抽樣5000 次。在95%的置信區間下,以感知機器人威脅作為自變量(對照組=1,現實威脅組=2,認同威脅組=3)并將其在程序中設置為分類變量,以職場物化作為因變量,以個人能動性作為調節變量,做調節效應分析。調節分析結果表明,在以對照組為參照時,現實威脅與個人能動性的交互作用不顯著(b=-0.14,SE=0.11,t=-1.30,p=0.193),認同威脅與個人能動性的交互作用顯著(b=-0.32,SE=0.11,t=-2.79,p=0.005),現實威脅組與對照組的職場物化無顯著差異(b=0.84,SE=0.58,t=1.45,p=0.148),認同威脅組的職場物化顯著高于對照組(b=1.81,SE=0.59,t=3.09,p=0.002),個人能動性的高低對職場物化無顯著影響(b=-0.07,SE=0.09,t=-0.75,p=0.452),模型的ΔR2=0.02,F(2,324)=4.02,p=0.019。在低個人能動性條件下,現實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不顯著(b=0.28,SE=0.17,t=1.58,p=0.116),而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有顯著影響(b=0.57,SE=0.17,t=3.30,p=0.001);在高個人能動性條件下,現實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不顯著(b=-0.03,SE=0.15,t=-0.19,p=0.848),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也不顯著(b=-0.10,SE=0.16,t=-0.62,p=0.536)。以上結果表明,認同威脅與個人能動性有顯著的交互作用,當個人能動性低時,認同威脅會顯著增加職場物化;而當個人能動性高時,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影響不顯著。由于研究2 和研究3a 中現實威脅的效應并不顯著,因此我們將后續研究的推進聚焦于認同威脅,即對認同威脅組與對照組進行比較。
4.2 研究3b:外部能動性的調節作用
4.2.1 被試
采用G*Power 3.1 軟件(Faul et al.,2007)確定所需樣本量,對于本實驗適用的單因素方差分析,根據已有關于機器人勞動力相關研究(Jackson et al.,2020),取中等效應量f=0.2,顯著性水平α=0.05,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需要共200 名被試才能達到80% (1-β)的統計檢驗力。考慮到可能有被試中途退出或未通過注意檢查,因此在某高校共招募了256 名本科生參與此研究,完成后可獲得相應課程學分。被試通過Qualtrics 平臺填答網絡問卷,并在研究正式開始前閱讀了指導語并知情同意。最終共42 名被試未完成研究或未通過注意檢查,得到有效數據214 份,其中女性121 名(56.5%),所有有效被試的平均年齡為20.17 歲(SD=1.37)。
4.2.2 過程
本研究為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被試被隨機分配到認同威脅組和對照組,在最終有效被試中,認同威脅組107 人,對照組107 人。在完成寫作任務后,被試依次填寫感知機器人威脅量表(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現實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1,認同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0)、控制感問卷(同研究2a,在本實驗中,控制感全部條目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76)、外部能動性量表和職場物化量表(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6)。
外部能動性的測量一部分改編自以往的補償控制文獻(Beck et al.,2020;Shepherd &Kay,2018),并根據本研究的目的和情境進行了相應修改。這部分測量共包括5 個條目:(1)我希望將對機器人的控制權交給政府;(2)我希望政府代表我控制機器人;(3)我對機器人的控制似乎由政府決定;(4)我對機器人的控制由政府負責;(5)我對機器人的控制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另外,還根據補償控制理論中外部能動性的說明,如采用這一策略的人會放棄對自己生活的自主控制,將個人能動性交給外部系統如神或政府,通過對外部系統的依賴來恢復控制感,相信外部系統會調動資源來實現符合他/她利益的結果(Landau et al.,2015),補充編制了3 個條目:(1)我認為政府可以控制機器人;(2)我認為政府有能力可以控制機器人;(3)我認為政府有資源可以控制機器人。以上測量外部能動性的條目均為Likert 7 點量表,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2。量表中穿插有注意檢查題項如“本題請選擇非常不同意”,最后填寫人口統計學信息。
4.2.3 結果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認同威脅組的現實威脅評分(M=4.19,SD=0.78,95% CI [4.04,4.33])顯著高于對照組(M=3.88,SD=0.71,95% CI [3.74,4.01]),F(1,212)=9.22,p=0.003,=0.04;認同威脅組的認同威脅評分(M=4.20,SD=1.18,95%CI [3.97,4.42])也顯著高于對照組(M=3.69,SD=0.95,95% CI [3.51,3.87]),F(1,212)=11.91,p=0.001,=0.05。操縱效果良好。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認同威脅組的職場物化(M=3.18,SD=0.59,95% CI [3.07,3.30])顯著高于對照組(M=3.00,SD=0.63,95% CI [2.88,3.12]),F(1,212)=4.66,p=0.032,=0.02。
為了驗證控制感是否在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使用 Hayes(2013)提供的SPSS 插件PROCESS (Model 4),以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為自變量(對照組=-1,認同威脅組=1),控制感為中介變量,職場物化為因變量,設定Bootstrap 樣本量為5000,采用偏差校正的方法,選取95%置信區間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數據結果顯示,控制感的中介效應值為0.02,95%的Bootstrap置信區間為[0.003,0.051],不包含0,表明中介作用顯著;并且在控制中介變量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直接效應為 0.07,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012,0.151],包含0,表明其直接效應不再顯著,控制感在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以職場物化為因變量考察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照組=-1,認同威脅組=1)與外部能動性的交互作用,結果表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和外部能動性對職場物化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b=-0.10,SE=0.05,t=-1.98,p=0.049),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職場物化顯著高于對照組(b=0.09,SE=0.04,t=2.17,p=0.031),外部能動性的高低對職場物化無顯著影響(b=0.02,SE=0.05,t=0.44,p=0.661),模型的ΔR2=0.02,F(1,210)=3.92,p=0.049。交互作用如圖3 所示,簡單斜率分析結果表明,在低外部能動性條件下,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顯著(b=0.18,SE=0.06,t=2.63,p=0.004);而在高外部能動性條件下,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不顯著(b=0.01,SE=0.06,t=1.10,p=0.920)。

圖3 外部能動性的調節作用
4.3 研究3c:特定結構信念的調節作用
4.3.1 被試
使用G*Power 3.1 軟件來確定本研究所需的樣本量,根據已有關于機器人勞動力相關研究(Jackson et al.,2020),取中等效應量f=0.2,顯著性水平α=0.05,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需要共200 名被試才能達到80%的統計檢驗力。由于研究職場物化,因此設置了填寫條件為目前在職,并且考慮到可能有被試無法通過注意檢查,并在Credamo 平臺上共計招募了208 名被試。其中8 名被試沒有通過注意檢查,最終被試量為200 人。被試平均年齡為31.62 歲(SD=7.44),女性125 名(占62.5%)。
4.3.2 過程
本研究為單因素兩水平被試間設計,被試被隨機分配到認同威脅組和對照組,在最終有效被試中,認同威脅組100 人,對照組100 人。認同威脅組和對照組的操縱過程同研究2c。在完成寫作任務后,被試依次填寫感知機器人威脅量表(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現實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1,認同威脅維度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9)、控制感問卷(同研究2a,在本實驗中,控制感全部條目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84)、特定結構信念量表和職場物化量表(同研究1a,在本實驗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4)。
根據補償控制理論中對肯定特定結構的說明,如相信做出特定的行為能夠可靠地產生預期結果,并且這種清晰、可靠的“行為—結果”可能性是針對減少控制感的具體情境的,結合本研究目的及具體情境,編制特定結構信念測量條目如下:(1)我認為拔掉電源可以控制機器人;(2)我認為編寫代碼可以控制機器人;(3)我認為破壞機器人的系統可以控制機器人;(4)我認為有特定的行為可以控制機器人。以上測量條目均為Likert 7 點量表,1 為非常不同意,7 為非常同意。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為0.62。量表中穿插有注意檢查題項如“本題請選擇非常不同意”,最后填寫人口統計學信息。
4.3.3 結果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認同威脅組的現實威脅評分(M=4.89,SD=0.86,95% CI [4.72,5.06])也顯著高于對照組(M=3.87,SD=0.93,95% CI[3.69,4.06]),F(1,198)=63.85,p< 0.001,=0.24;認同威脅組的認同威脅評分(M=5.07,SD=1.06,95% CI [4.86,5.28])顯著高于對照組(M=3.80,SD=1.21,95% CI [3.56,4.04]),F(1,198)=61.84,p< 0.001,=0.24。操縱效果良好。
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顯示,認同威脅組的職場物化(M=3.32,SD=0.65,95% CI [3.19,3.44])顯著高于對照組(M=3.10,SD=0.66,95% CI [2.97,3.23]),F(1,198)=5.59,p=0.019,=0.03。
為了重復驗證控制感是否在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中介作用,使用Hayes(2013)提供的SPSS 插件PROCESS (Model 4),以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為自變量(對照組=-1,認同威脅組=1),控制感為中介變量,職場物化為因變量,設定Bootstrap 樣本量為5000,采用偏差校正的方法,選取95%置信區間進行中介效應檢驗。數據結果顯示,控制感的中介效應值為0.03,95%的Bootstrap置信區間為[0.003,0.067],不包含0,表明中介作用顯著;并且在控制中介變量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直接效應為0.08,95%的Bootstrap 置信區間為[-0.005,0.169],包含0,表明其直接效應不再顯著,控制感在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以職場物化為因變量考察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照組=-1,認同威脅組=1)與特定結構信念的交互作用,結果表明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和特定結構信念對職場物化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b=-0.14,SE=0.05,t=-2.76,p=0.006),感知機器人威脅組的職場物化顯著高于對照組(b=0.11,SE=0.05,t=2.38,p=0.018),特定結構信念的高低對職場物化無顯著影響(b=0.01,SE=0.05,t=0.25,p=0.806),模型的ΔR2=0.04,F(1,196)=7.63,p=0.006。交互作用如圖4 所示,簡單斜率分析結果表明,在低特定結構信念條件下,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顯著(b=0.24,SE=0.07,t=3.64,p< 0.001);而在高特定結構信念條件下,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不顯著(b=-0.02,SE=0.07,t=-0.27,p=0.784)。

圖4 特定結構信念的調節作用
5 討論
通過3 項研究(共8 項子研究),結果發現,感知機器人威脅會增加職場物化,控制感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并且補償控制的另外三種策略,即加強個人能動性、支持外部能動性以及肯定特定結構,能夠調節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具體而言,首先通過對機器人公司員工的大規模問卷調查發現了感知機器人威脅與職場物化的正相關關系(研究1a),然后又通過多種研究方法反復驗證感知機器人威脅會增加職場物化(研究1b~3c)。通過對被試控制感的測量,進一步發現了控制感是感知機器人威脅影響職場物化的中介機制,即感知到機器人威脅降低了被試的控制感,進而通過職場物化來進行補償(研究2a~2c),并且發現主要是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造成了職場物化的差異(研究2c)。通過對其他三種補償控制策略的測量,研究還發現了個人能動性(研究3a)、外部能動性(研究3b)以及特定結構信念(研究3c)對感知機器人威脅影響職場物化的調節作用。
更為有趣的是,如果將感知機器人威脅細化,本研究實際上發現了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效應要勝于感知機器人現實威脅,同時控制感中介的是認同威脅到職場物化間的路徑。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更多導致了職場物化增加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前人對機器人威脅的相關研究結果的差異,如Huang 等人(2021)的研究發現相對于機器人現實威脅,認同威脅更能預測人們對機器人的負面態度。這一結論也不是絕對的,如Z?otowski 等人(2017)則發現機器人現實威脅和認同威脅都是導致對機器人的負面態度和對機器人研究的反對增加的中介因素,不過現實威脅的中介效應還更強。本研究實際上均發現了現實威脅和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效應,但認同威脅效應更強,且控制感只能中介認同威脅,控制補償的其他三種策略也只能調節認同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這都表明,機器人認同威脅是增加職場物化的主要因素,也是導致控制補償的主要機制。這可能與本研究所探討的因變量職場物化有關,由于“職場”這一概念本身就與對工作的現實威脅密切相關,因此認同威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已然包含了現實威脅,且較其程度更甚。
而機器人認同威脅在職場物化情境下,除了越來越多地取代人類的工作,是因為模糊了人與機器之間的界限,從而造成對人類獨特性的威脅(Yogeeswaran et al.,2016)。在同樣的情境下,實際上人類獨特性可以被威脅,也可以被凸顯,這似乎是一件事情的兩面,從何種角度看待則會造成不同的結果。如也有研究發現機器人或許能夠提升人們的泛人類主義,更多地將人類同胞視為自己的內群體從而減少偏見,產生正面人際效應(Jackson et al.,2020)。本研究從感知機器人威脅的角度切入,發現其會增加職場物化,從而驗證了機器人對人際關系可能的負面影響,這明顯與Jackson 等人(2020)所發現的機器人對人際關系的正面影響是相反的。本研究也對泛人類主義進行了測量,但并未發現與前人研究類似的積極效應(Jackson et al.,2020)。這一差異可能是由于職場的競爭特征,導致從“威脅”角度來看待同一問題的可能性要大于“凸顯”角度。當然,本研究雖然實驗操縱材料基本一致(本文所使用的實驗操縱材料為中文翻譯版),但在Jackson 等人(2020)所探討的自變量僅為機器人的“凸顯”,并未涉及機器人“威脅”,但本文被試在閱讀實驗操縱材料后填寫了感知機器人威脅量表作為操縱檢查,這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對機器人威脅進行了提醒和強調。本研究的結果實際上與之前的機器人影響人類之間關系的研究結果相似,如研究發現,由于機器人對人類社會有限資源的擠占,機器人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會使人與人的關系更加緊張而非更加積極(如Frey et al.,2018;Im et al.,2019)。此外,從相對意義而言,物化他人的同時也會造成自身與他人的區隔,即在物化他人的同時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自身的優越感,產生“對比”效應。本文關注的重點在于對他人的物化,未來研究可以更加深入探討人們在受到機器人威脅時產生的自身相對優勢問題。
機器人認同威脅導致的這些結果也有一定的實踐意義。機器人滲入職場對人們的工作、資源等造成的現實威脅或許很難避免,但機器人對于人之為人的獨特性造成的認同威脅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例如如今很多機器人都被設計為具有擬人化的特征,很多研究也發現機器人擬人化有積極影響,如擬人化的機器人更受人們信賴(Rehm &Krogsager,2013)、能夠得到更多表揚和更少懲罰(Bartneck et al.,2007)等。然而,機器人更高程度的擬人化同時也會使人類知覺到更嚴重的威脅,尤其是其能力高于人類時(Yogeeswaran et al.,2016)。本研究的發現進一步探討了人類感知到機器人威脅,尤其是感知到機器人的認同威脅可能會導致的人際關系負面后果,即職場物化。那么既然機器人過于像人會對人類造成認同威脅,且這種威脅會產生消極影響,那么在對機器人的設計中就必須把握好擬人化的尺度,以預防其消極后果的產生。
盡管本文通過一系列研究對感知機器人威脅影響職場物化的現象、心理機制和邊界條件進行了探討,但研究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局限性,有待在后續研究中進行改善和提升。首先職場物化的方向有待拓展,本文主要探討的是平行職場物化,即同事之間的職場物化,但其實職場物化的方向還可能是下行(如領導對員工;Gruenfeld et al.,2008;Landau et al.,2012)和上行(如員工對領導;Inesi et al.,2014),不同的物化方向可能會帶來控制感的差異,從而影響職場物化的結果。其次,研究的生態效度仍有提升空間,盡管本文的8 個子研究盡量增加了被試群體來源的多樣性,如不僅涵蓋大學生被試,還有從網絡平臺上招募的來自全國各地的被試,并且也有真正在機器人工廠工作的一線工作者,但是之后的研究可以更多地涵蓋不同行業的可能接觸到機器人的工作者,對本文的研究結果進行重復驗證。此外本文主要采用了問卷研究和網絡實驗,并且對職場物化的測量也采用了自我報告的方式,沒有對被試的真實行為進行觀察記錄,未來可以通過現場實驗等方法,讓被試與真實的機器人現場互動從而產生感知威脅,在更加真實的社會情境中觀察被試的真實行為。在實驗設計的細節方面,文中2.3 等研究中所使用的寫作任務對照組的指導語在情緒屬性上較為積極,這可能會對研究結果產生一定影響,在未來研究中應盡量避免,代之以更加中性的指導語。
6 結論
本研究結論如下:第一,感知機器人威脅會增加職場物化,并且感知機器人認同威脅的影響更強;第二,控制感在感知機器人威脅(主要是認同威脅)影響職場物化中起中介作用;第三,補償控制的另外三種策略,即加強個人能動性、支持外部能動性以及肯定特定結構,能夠調節感知機器人威脅對職場物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