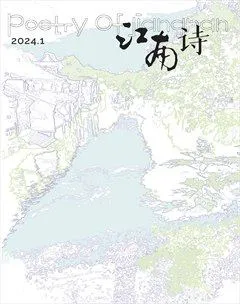人間草木(六首)
冬 樹
車窗里閃過一排排樹,
寒冬赤裸的樹。
裸樹,是樹的抽象形式,
是冥想的樹向天籟傾倚的身姿。
枯枝敗葉,果實無存
匆匆一瞥認不出都是些什么樹。
憑著高矮,粗細,曲直
我們可以說
這一棵與那一棵種屬不同,
風霜雨露,這一株與那一株
在不同時點承受過不同的悲歡。
這些迅急倒向田埂倒向池塘的樹
似乎要去和影子一起安息。
當我們回頭去看,它們
又齊刷刷從泥土和水泊中立起,
壓根不拖泥帶水。
沿途數不清有多少寒枝搖顫
將落日這只朱紅的鳥,
從危巢拋往下一個危巢。
數不清有多少無名枯樹退離藍幕,
無牽無掛,一身傲骨
撲撲飛出了我們的視線,
數也數不清的英拔的天使。
梅林報春
如果寂靜沉降為斜坡上的一種
景觀,聲音就無法遮掩它的假象。
那些低微的,孱細的,悄悄
匯聚于某個時刻,遲早會將沸點擊穿!
閉上眼聽!成千上萬朵梅花
競相吐蕊,從這急匆匆的窸窣里
可以想見它們的凜然、踴躍
與一往無前;可以想見緊抓樹枝的
腳爪,奮力張嘴時喉嚨里
腫脹的扁桃體。仿佛在同一情緒中
達成默契,孤獨在稠密膠質中
迅速化為孤傲;仿佛螢蟲
主動投身于集會,抱團取暖,
在交頭接耳時傳遞著烏托邦的風。
共鳴與顫動,在斜坡上
搓出一片紅紗。成群結隊,梅花
壓低嗓音。它們已無須動員,只等天空
給出信號,就會紛紛跳下枝頭
與盛大而動蕩的花期同歸
于盡,給春天留下一片廢墟
和從寂靜中擠出的幾聲唏噓。
雛菊告白
如此露骨的表白,從清晨的窗臺躍來
羞紅晨曦,和云帳里迷離的眉梢
如此纖小的身體,弱不禁風的身體
對著天空燃起火苗,甚至不惜燙傷自己
必然有個不眠之夜。輾轉起伏
一個清冷的夜被翻卷成狂熱之夜
它從這夜的濃郁中擠出甜漿
在夢的隱秘邊緣摩擦閃電的形象
愛過,低語過,也祈禱過。
即使根莖動搖過,鋸齒狀的葉子疼痛過
哭泣過,又在輕霧中梳洗過
破曉的時刻,接著是揭曉的時刻
如此直率的凝望:雛菊睜開眼睛
將那道躲讓不及的光拽進來
如此潑辣的綻放:雛菊吐出芳心
讓溫暖的繡花針直刺進來
金絲桃的刺繡課
用你金色的絲線,繡黃蝶歇在指尖
繡光滑的翅膀和毛茸茸的觸角。
用你的金線,繡爬上沙灘的海星
繡棘皮上的紋路和臂尾發光的眼睛。
用金線,繡蓬松而搖曳的火,
再繡薄燈籠紙,繡房檐上的琉璃鳳凰。
繡個金絲雀兒,繡個多嘴的黃鶯兒
左邊繡煙霞,右邊繡暈染的黃昏。
再繡柚子樹、橙子樹、橘子樹
用輕細的線繡沉甸甸的東西。
用金線,繡夜市上的一盞盞燈,
直到繡出人間煙火,繡出人山與人海。
用你的金線,繡值得深描的過客
繡出良善和堅韌,以及難得的歡喜
用你金色的絲線,繡出這個世界
該有的樣子。縫補后煥亮的樣子。
苦苣菜之歌
矮小的一叢,藏在江堤的石縫中:
葉掌皸裂,托著兩個暗黃
花球;憔瘦的果莢有六七顆。
探頭探腦的苦苣菜,莫非也知道
寒冬將盡,接下來的日子
興許是有盼頭的日子?
舉目望去,滑入江底的斜坡
幾乎寸草不生。曾經的蘆葦地
只剩下焚燒后的黑茬,
還有一大片焦土。仿佛這里
剛結束硝煙彌漫的戰役,
許多生命的煙燼被風掃進了江心。
如劫后余生的士兵,苦苣菜
鉆出防空洞,朝天空揮舞
滿是塵垢的迷彩。
歡樂與苦澀,興奮與疲乏
一道涌上花喉。這細挑的莖管
能支撐多少沉沉時日?
眼下尚是枯水季節。青綠的江流
也在蓄精養銳。陽光在江面
劃出園圃,播撒銀色的種子——
三月,千樹梨花將登陸對岸的沙洲。
那里也是苦苣的沃土,
是一茬茬鄉親扎根續命的地方。
冬日的牽牛花
立冬過后,初夏種的牽牛花
就來到了彌留之際——
她枯黃的藤蔓上
還有縮作一團的葉子簌簌落下,
像蟬翼被風從梯子上吹走,
回到歌聲飛翔的起點。
從泥土中,也許還有些微
環繞著夢田中心的意志
從暗道中升起,將一顆晶亮的淚珠
送往頂點——
沿著身體里那條蜿蜒的路:
一長段干涸的河床,苦難
斑駁的灘涂;兩三處紅顏舊址——
哦,愛情,紅唇碰過的淺紫色酒杯。
必須把怕黑的萌芽
一寸一寸舉起來,抵抗
回憶下墜的力,必須把命運的琴弦
虛弱而溫柔地
交付給最高處的殘綠——
縱然氣若游絲
也要伸出失去血色的手,去夠一夠
那高貴的輕盈。
作者簡介:亦來,原名曾巍。詩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訪問學者。華中師范大學學報副主編,編審。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生導師。著有《亦來詩選》《希爾維婭·普拉斯詩歌批評本》。曾受荷蘭阿姆斯特丹詩歌與實驗中心、中美詩歌詩學協會邀請赴荷蘭阿姆斯特丹、美國洛杉磯朗誦,有詩歌譯介到美國、法國、荷蘭與阿根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