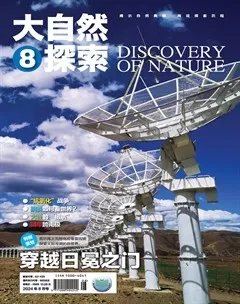大豆的“祖宗”
營養豐富的大豆(俗稱黃豆)是重要的食材,其種子發芽后就是豆芽,豆莢快成熟時可以摘下成為毛豆。大豆經過烹飪或加工就能變成多款佳肴或調味品,用其做成的豆腐更是口感最接近肉類的植物蛋白。
其實,我們餐桌上的大豆并不是一出生就長成這樣的,豆粒也遠沒有這么大、這么飽滿,口感也沒有現在美味。這就要說到大豆的“祖宗”——野大豆了。
野大豆≠野生大豆
野大豆與野生大豆并不一樣。野大豆是豆科大豆屬的一個獨立種,俗稱烏豆、勞豆或山黃豆,其豆粒比綠豆還要小,成熟后呈灰褐色,活像老鼠的眼睛,因此也俗稱為老鼠眼。

野大豆是一年生纏繞草本,植株纖細,全株被灰褐色硬毛,花呈淺紫色或近白色,葉片有三小葉,果莢長圓形。野大豆是地地道道的中國產物,古人稱之為“菽”,是五谷之一。早在五千多年前,我國古人就開始采集、食用并馴化這種植物了。《詩經》中記載:“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可見這種豆子在古代并不是什么高端食材。
我國古人對野大豆不斷進行馴化和選育,才有了我們今天熟知的大豆。據記載,到了商朝前后,人工種植的大豆籽粒明顯變大,華夏大地對大豆的馴化接近完成。之后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更加充分地利用這種馴化后的豆子,使其在飲食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相傳,西漢淮南王劉安在煉丹過程中,無意間將鹵水滴入豆漿中,遂誕生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豆腐。在肉類匱乏的年代,豆腐的發明在推動大豆的栽培和普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為何為國家二級保護植物?

《漢書·五行志》中寫道:“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雖然我國古人采食野大豆,但也因野大豆這種植物對重要糧食作物的侵害深感困擾。這是因為野大豆繁殖能力極強,其豆莢成熟后會炸裂,將里面的種子彈射出兩到五米遠。因此,如果你在野外見到野大豆,那常常是一大片。
既然野大豆的繁殖能力很強,在我國多個省份的野外都很常見,那為何將其列為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呢?

要知道,豆科大豆屬下的植物我國只有五個種,基因相對單一。如果某種基因對災害沒有抵抗力,那么擁有該基因的全部種都沒有抵抗力。野大豆是大豆馴化培育的前身,它有著卓越的基因多樣性,包括抗病、抗蟲、抗倒伏、抗鹽堿等眾多優良基因,以及可能有很多未發現的優良基因。如果大豆或其他栽培種遭受某種難以對付的病蟲害,育種專家便可以利用野大豆的這些優良基因進行改良。因此,雖然野大豆在野外比較常見,它卻如同綠化帶常見的銀杏一樣,是國家二級保護植物。相比其他國家二級保護植物,野大豆所要保護的不是它的數量,而是它的基因多樣性,保護野大豆也就是保護大豆和很多栽培種。

珍貴的種質資源
我國是大豆消費大國。雖然大豆原產于我國,但我國的大豆市場卻大量依賴進口。19 世紀初,美國引進了我國馴化后的大豆小量試種。隨著其種植技術的不斷改進及農業補貼的實施,在20 世紀中期,大豆在美國已經達到規模化種植。
然而,在20 世紀末,由于大豆孢囊線蟲病大規模爆發,美國的大豆產業幾乎崩潰。就在此時,大豆的“祖宗” ——野大豆,再次發揮了其關鍵作用。
育種專家利用野大豆這個原始種培育出了一種抗大豆孢囊線蟲病的新品種。以此為基礎,美國的孟山都公司又相繼培育出了多款抗病蟲、高產、高出油率的轉基因大豆。由此,美國的大豆育種及轉基因大豆技術享譽全世界。

盡管美國的大豆育種技術和種植規模已居全球之首,但我們依然不能忽視我國作為大豆原產國的獨特優勢,即豐富的野大豆種質資源。野大豆的基因多樣性非常豐富,其內包含的抗病、抗蟲、抗倒伏、抗鹽堿等優良基因是無可替代的寶貴財富。我國的育種專家要做的,就是把這些優良基因整合到同一株大豆上,培育出多種高產、抗病性強、出油率更高、易于收割和管理的優質大豆。要實現這些可能性并打破大豆育種技術的瓶頸,就必須重視并保護好大豆的“祖宗”——野大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