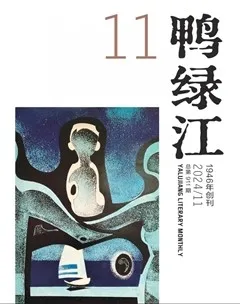將至
一
離別,容易成為兩個人的終點。轉身即天涯,甚至陰陽兩隔。想要再見,就只能在回憶里了。那時才知道,以前在一起有多重要。
其中最理想的,莫過于終點足夠遙遠,任兩人咋走,也到不了那里。可惜那樣的好事,在妻身上,我都沒能看到。要知道,我可是天天都在祝福妻的。
七歲時,妻去給一個長輩拜年。人小,背了一把面、一塊枕頭粑。在那里,妻待了三天。那家小孩兒多,大家聚在一起,能玩出花樣兒來。臨走,長輩給了兩角壓歲錢,還叫下次再去。妻一直記得,那是一張白皙善良的臉。
來年再去,還是玩三天。出發時的樣子,都是好看的,不會輕易改變。
堅持到初中,學業忙起來,妻才沒去了。起初的意思,也是想暫停一下,攢點兒力氣。
哪知再見,已在長輩八十歲以后。家族里有規矩,逢五給她做生。隔五年,妻和她見一面。她的愿望是活到一百歲。好像多年前的那條路又接上了,終點呢,也像是還在前面。那時妻已工作多年,卻還像小時一樣,提上幾樣小禮物就去了。到了,也沒意識到只是待了個把小時。坐在對面的她,正忙著打麻將。在妻離開的那段空白歲月里,她學會了麻將。天天都打,一年下來,輸贏有一兩千塊。臨近終點,她的臉上有著清晰可見的皺紋和黑斑。妻看了,也沒感覺有啥不妥。
的確,如果要比路的長度,妻和她之間的,算是很長的了。
于是,又想起年齡更大的奶奶。換一條更長的路,問題會不會更嚴重一些?你看,從妻牙牙學語、跟著奶奶一床睡算起,都過去五十多年了……那是不是容易讓妻誤會,天真地以為可以永遠走下去?
去世前幾天,奶奶在大姑家團年。滿桌的好菜,缺少胃口的她都沒咋動筷子。妻也顧不上她,扭過頭和人說話去了。很快便說好,正月初二是去小姑那里,初八到我家,中間幾天也安排上了。在妻的印象里,奶奶跟著跑來跑去,應該沒啥問題。直到奶奶閉著眼睛,躺在冰冷的門板上,妻才發現,那么遠的終點竟然都已到了。
終于,跪下的妻,低了頭,彎著腰,把自己變成一個問號。幾年后,在父親面前,我也那樣做了。連接起來,像是在相互詢問。所以,好歹我也要說上幾句,就當是回答或者傾訴。
二
和妻相比,我走的路不大一樣。或者說,運氣差了一些。沒有那樣長壽的長輩不說,還老是在告別。那些年,村子里窮,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留下我一個人,心不在焉地讀書。校門外江水如鏡,照見的全是我的憂傷。
從一開始,我就擔心他們一去不返,把一個個終點硬塞給我。我才十多歲,就算比妻當年大上一點兒,也不可能拒絕得過來。不過也說明,我和妻好像可以同病相憐。
我叫他們老表或者表叔。好多時候是喊兄弟。記得有一次,是和其中一個在田里插秧。他來借路費,碰上秧沒插完,就挽起褲腿下田幫忙。
周圍的田里,已經綠油油一片。我家的,還像灰白的傷口。他嘆口氣,要我別種田了。好像還沒出發,他就知道在遠處沒人干那個。聽他那樣說,我更憂愁了。秧插到一半,大路上走來幾個年輕人,提著一臺錄音機,放著《瀟灑走一回》,還有別的什么歌曲。我忍不住抬頭去看。他馬上表示要從云南提一臺回來。在越來越局促的水田里,我馬上就相信了。我和他之間的那條路,沒有一個好的開頭。
后來,他再沒來過。據說偶爾回村,也是找我不在的時候。我打聽過他好幾次,想當面把終點還給他。至于那點兒錢,已經不值錢了。他還不還,都沒關系。
直到現在,想起那臺沒出現的錄音機,我都還在遺憾。或許,真的有一首重要的歌曲,被我永遠地錯過了。
還有一次是在橋邊。另一個朋友要去廣東,我泡了兩碗茶給他送行。記得那天是在刮風,茶店周圍的竹林嘩嘩作響,加入了我們的談話,也定下調子:細碎、跳躍、糾纏。臨走,他說,到廣東就不興喝茶,要改喝啤酒了。我問店老板有沒有,店老板搖搖頭。當時就感覺,終點是捧在他的手上,我沒接,他也沒放下。
年底他回來,我請他喝啤酒。在村里,那是浪費,比老白干貴多了。一瓶見底,他說,喝慣紅酒,喝不下了。我賠著笑臉,又灌了他兩瓶。熱鬧中,尷尬也明顯起來,雙方的力道都在加強。隱隱地,我有了不好的預感。
隔年春節,聽說他回來,我準備了一桌菜:父親養的豬,母親喂的雞,我去塘里捉的魚。到飯點兒,他來電話,說臨時有事兒。掛斷手機,一陣倦意襲來,我坐著半天沒動。堅持或抗爭的結果,還是他放下終點走了。對我,對一條路,一定要那么狠心嗎?
該說說去云南學泥水匠的那個了。一直以來,那是個笨人。手慢,不會說話,沒啥朋友。我去送他,也缺乏像樣的理由。車啟動,卻聽他大聲說,以后想修房子,就包在他身上。我懷疑,那是他第一次承諾和別人一起走。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接下來的情況是,學了三年,他都不會砌磚,只能糊糊外墻。在工地,那是粗活兒,含金量低,收入屬于底層。就那樣,糊得還不咋樣,不是厚薄不均,就是干濕有問題,常常需要返工。逼得急了,他會哼上幾句:“黃鱔黃,黃鱔死了肚皮黃,泥鰍見了哭一場,雖然不是親兄弟,一同滾過爛泥塘。”不知是從哪里學來的。
那年聚會,又聽他唱起來。連唱兩遍,悲情四溢。我也聽出來了,他是在正式告別。忍不住問了問情況。回答說有些年是在福建扛包,有些年去了新疆摘棉,一個地方不要他了,就去下一個。果然,他想和我走的那條路,早就不通了。哪怕,像那條泥鰍一樣,我哭了一場。
搞得好多時候,我都在抱怨:太倒霉了,走的全是短路。乍一聽,也像是在吹捧自己,好像把長一點兒的路都讓給妻了。
三
還以為,也就那樣了,自己會拒絕下去。
也不能怪我太自不量力。那以后的我,的確也沒閑著。十八歲時,我去一個悶熱的城市念大學,遇到一百多位同學。在數量上,一下就超過了外出打工的他們。有一晚,看到山下的萬家燈火,發現還有好多陌生人躲在燈后面。世界太大了,自己得抓緊。
下山后,在天橋上,果然碰見一個黑胖子。他挎著帆布包,在賣盜版書。主要有三大品種:言情、武俠、警匪。隔得老遠,就笑著遞本過來。一年后,他娶了個二婚的胖女子。又一年,生了個胖小子。再看到他,我也笑起來。他的一家,太好認了。
在學校后門,還有個白帽子。賣的鹵肉時咸時淡,但人眉目如畫,跟電影院門口賣湯圓的像是親姐妹。問了幾次,又說對方不是。不管是不是,我都能認得她倆。
小巷里,我也去了,又碰上幾個。臺球室、包子鋪、涼面攤兒……在哪里,和他們都能見上面。記得肥腸店里的那個,一頭長發。如果不是城市總在下著大雨,給她一把油紙傘,她就成丁香姑娘了……
我是這樣想的,要走就走個痛快。反正離別的日子早定了,不就是我離開城市的那一天嗎?到時,終點塞過來了多少,我就拒絕多少。畢竟,那是我的態度和尊嚴。
喝完幾臺酒,聊過幾次天兒,那個日子如期而至。我跳上車,快速把城市拋在身后。一度認為,自己的背影,展現了個不錯的拒絕姿勢。
后來翻檢行囊,才發現可能不是那么一回事兒。一是終點有多少,沒個準數;二是拒絕過的好像沒以前多了。總感覺,自己是說了大話。
再后來,是去另一座城市生活。前后工作過兩個單位,一共結識了四五百個同事。三十年間,教了近兩千個學生。到外面,還和好些人來往密切。微信興起后,又果斷加入了十多個群。
回頭去看,那樣做,更像是在掩蓋自己的不自信。想在與數量的對抗中,擁有更多的那一天。然后趁他們不注意,重新來過。
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幫了自己的倒忙。
四
明白一些,好像是在五十歲以后。
那年,妻有了白發——先在兩鬢,接著是頭頂。一起出現的,還有皺紋。和世上所有的妻一樣,她開始準備和我告別的樣子。作為丈夫,我得出面拒絕,不然就太不合格了。
我想,至少自己該是這樣:幾天吃不下飯,幾晚睡不著覺。如果不行,就再痛苦一些。好容易才同走一條路,有可能和她走的一樣長短,無論如何,都要把那個名叫衰老的終點往后推一推。
我那樣想,自然是以為自己還可以。或者說,還不知道在那么多的那一天里,在我身上發生了什么。
好在那一次,我的運氣不錯。像是在往回走,妻竟然復制了以前的姿勢——小鳥依人般趴在我的腿上。腰腿不好的她都那樣了,我還能說啥呢。
的確,多好的機會啊,那些亮晶晶的白發就在眼前。只等我的痛苦一到,它們便會全軍覆沒。但關鍵時候,我卻用起了指頭——拇指和食指。是不是,它倆合作已久?記得在我小時,它倆曾在一起幫我撿起地上的東西:奶奶的針、母親的紐扣、父親的煙頭。上學后,又替我握著筆。到后來,是數清我掙的每一分錢……作為動作,可謂經典。果然,只是微動一下,我就順利地拔掉了一根,輕輕地放在妻的手心里。
那一刻,小鳥般的妻幻化成一面鏡子,照出我的偽劣。偷梁換柱,我在干啥?
很快發現,那還只是開頭,更多的替代品正在趕來。比如已經到了的那幾瓶染發劑,就可以明目張膽地用來作假。如果不成功,還有幾套質量成疑的化妝品可用。甚至那臺遲遲沒有進行的美容手術,其實也是出發了的……幾乎沒費啥力氣,我就拿出了它們。
像是約好似的,母親也來告別。多一雙眼睛,也許會把我看得清楚一些。那時,一輛車剛撞飛了她。出院后,她有時清醒,有時糊涂,斷斷續續喊著我的名字。你是某某某嗎,她問,好像怕我變成了別人。臨近終點,她也就剩下那點兒緊張了。按理,我多年來積攢的憤怒、煩躁、焦慮,正好可以派上用場。再不拿出來,就晚了。
可是,并沒有。以致在母親那里,我看見自己長了一副稀釋或冷卻后的樣子。具體表現是,每天拿出兩片降壓藥、六顆腦心通。碰上她的膽囊炎犯了,再加點兒利膽片。我的動作很熟練,像是彩排過一樣。
一次,出了點兒問題。她把藥含在嘴里,假裝咽下去了。被發現后,趕緊猛吞幾下,張開嘴給我看。
那是她難得的一次抗議。好像可以證明,我是在妥協或者投降。也不知道,是從啥時開始的。
五
時不時,我會胡思亂想,那些痛苦是不是讓自己藏起來了?莫非真要等到和自己告別時,才會拿出來?在這方面,我一直想找點兒證據。
比如我喜歡打牌。常常是中午十二點一過,電話就來了。趕緊起身,拿起錢和鑰匙出門。一同離家的,還有那個清清爽爽的另一個我。另一個我想到湖邊走一走,聞聞花香,看看飛鳥。湖里的荇菜長得正好,適合另一個我站在旁邊吟上幾句古詩。那個時候,我很想聽見自己朝另一個我大叫一聲:別走。然后對另一個我說,你走了我咋辦?再讓我把牌打下去,時間就沒了,錢也輸光了。后果那么嚴重,我得好好猶豫和掙扎一番。
最好還能舉起刀子,作勢要砍斷幾根手指,雖然那樣的姿勢顯得夸張了一些。結果是我想多了,除了關門聲,啥也沒有。
像是補充后的事實,我還愛喝酒。每次體檢拍片,醫生都說是脂肪肝,讓戒酒。起初幾天,另一個我果然出現了,一頓能老老實實吃完一小碗飯。不到一周,飯菜開始無味起來。一上桌,就有點兒坐立不安。再加把勁兒,也許就成功拿到證據了。
不過,每次都差一點兒。很快,我就又能端起酒杯。在喝的過程中,我會反復出現在兩條路上。一條是我走過去,等著醫生的下一次警告;一條是趁著酒勁兒,到往事那里發一會兒呆——好像有時是想起一個少婦,眼睛大大的,穿著旗袍,流水一般,曲折地流過;有時想起一個姑娘,瞇著眼,河風撩起她的頭發,像一段慌張的文字。我讀兩句,跑到遠處,看看沒事,又沖回來,再讀幾句……不停地,我讓自己遇上另一個我。那一天,還和從前一樣多。
只是,在我回過神來后,另一個我便遠去了。腳步匆匆,每次也就停留了幾分鐘。我已越來越沒信心,想坦白啥也沒藏,承認自己早就是個窮光蛋。
如果是這樣,再窮上二十幾年,我就到了父親去世的年齡。倒是不太大,還沒到省里的平均數,也是一條短路。記得,生命的最后兩天,父親坐在椅上,閉著眼睛,不發一言。小姑來,他也不理。食量奇大的他,徹底關閉了通向食物的大門,開始和塵世的自己告別。那天,大約凌晨四點鐘,他逝去。其時,弟弟在十米之外酣睡。而我,是在千里之外。看他的遺容——瘦削、平靜。死亡,也許替他隱瞞了什么。
幾年前的情形,大致如此。是在白天,奶奶從鎮上抓藥回來,想躺一會兒。隔著一堵墻,妻弟一家圍在一起吃飯。也就十幾分鐘,借著墻的掩護,奶奶離開了。妻弟的說法是,她回去了。近百年的時光,她就像來家里走了趟親戚。
說不清是引領還是誤導,父親和奶奶看起來不像是富裕的樣子。其他的人,又是啥樣的呢?
所以,還應發生一件事:越過時空,我想走近那個夜晚的父親。在他面前,最后一次,再試試自己是啥反應。還要問問,在最后一刻,他究竟有沒有痛苦可言。他貧困的家、傷病滿身的老妻、幾個不爭氣的子女……尤其是一輩子不如意的他自己,他還在拒絕嗎?
真的,我很想知道。因為,那可能就是我的未來。至于奶奶那里,還是妻去為好。會不會走的路不大一樣的我們,問的是一個相同的問題呢?
六
一口氣說了這么多,該打住了。或者說,我已經借話語掩飾和解釋了太多,在多年的刪減后,竟然假裝豐滿了一些。
那就趁熱打鐵,干脆再想象一下:在每一條路的盡頭,一定都會站著一個痛苦的我……
是的,為妻,為其他人,我也只能這樣了。
作者簡介gt;gt;gt;gt;
豆春明,四川眉山人。文字散見于《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散文》《散文百家》《四川文學》《福建文學》等刊。曾獲《散文百家》首屆全國征文獎、四川散文獎。
[責任編輯 劉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