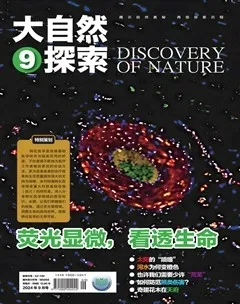奇趣花木在天府
珙桐
綠色“大熊貓”“,飛”過(guò)冰河時(shí)期的“白鴿”
每當(dāng)春天來(lái)臨,白色的珙桐花朵隨風(fēng)舞動(dòng),仿佛成群的鴿子在樹(shù)冠上竊竊私語(yǔ),珙桐也因此得名“鴿子樹(shù)”。早在200萬(wàn)年至300萬(wàn)年前,珙桐就已經(jīng)在地球上安家,現(xiàn)在多生長(zhǎng)在海拔1500~2200米的濕潤(rùn)地帶。
每年的4~5月,是珙桐掛滿“鴿子”的時(shí)節(jié),顏色從初開(kāi)的綠,慢慢變成凋落的白。但珙桐的花并不是我們所見(jiàn)到的白色的“鴿子”,而是中間紫色的“花心”。成熟的珙桐種子種皮厚且堅(jiān)硬,且休眠期長(zhǎng)。埋在土壤中的珙桐種子要2~3年才會(huì)發(fā)芽,可大部分的種子還沒(méi)等到合適的發(fā)芽時(shí)間就已經(jīng)腐爛掉了。即使部分種子在突破重重困難后生根發(fā)芽,但是由于剛萌發(fā)的種子不耐潮濕,過(guò)于潮濕的環(huán)境會(huì)加速新芽的腐爛,也會(huì)導(dǎo)致新芽死亡。珙桐啊,你要長(zhǎng)大真是太難了!


欒樹(shù)
會(huì)變色,還會(huì)“下雨”的樹(shù)
這類(lèi)能“下雨”的樹(shù)叫欒樹(shù),屬于無(wú)患子科欒屬的落葉喬木。欒樹(shù)開(kāi)出的花朵為聚傘形圓錐花序,初開(kāi)時(shí)為黃色,花瓣掉落后,花朵苞片膨大,會(huì)撐起一個(gè)個(gè)像小燈籠的果實(shí)“保護(hù)罩”。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這些苞片由粉紅色慢慢變?yōu)榈凵罱K變?yōu)楹稚@也是我們會(huì)看到欒樹(shù)開(kāi)花不止一色的原因。
一棵樹(shù),居然會(huì)“下雨”,這說(shuō)起來(lái)估計(jì)沒(méi)幾個(gè)人會(huì)相信。但夏天經(jīng)常把車(chē)停在欒樹(shù)下的人,肯定深有體會(huì),因?yàn)椴欢啻笠粫?huì)兒,車(chē)玻璃上多半就會(huì)出現(xiàn)黏糊糊的東西;從樹(shù)下路過(guò),明明晴空萬(wàn)里,可就是感覺(jué)有水滴在身上。欒樹(shù)為什么會(huì)“下雨”?這是因?yàn)樗麻L(zhǎng)出來(lái)的葉片容易被蚜蟲(chóng)盯上,成為蚜蟲(chóng)家族的棲息和繁殖地。大量蚜蟲(chóng)在痛飲了欒樹(shù)美味的樹(shù)汁后,會(huì)排出大量黏稠液體。

銀杏
守護(hù)成都千年,為何卻成了瀕危植物

銀杏,作為成都的市樹(shù),早已融入了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幾乎隨處可見(jiàn)。盡管銀杏在成都如此常見(jiàn),但野生銀杏的數(shù)量卻不容樂(lè)觀,已被列為瀕危植物。在許多野生銀杏的周?chē)呀?jīng)十余年不見(jiàn)天然更新的幼樹(shù)。為什么野生銀杏會(huì)陷入瀕危的境地呢?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diǎn):一是基因多樣性低,幾乎所有現(xiàn)存銀杏都來(lái)自同一母本,通過(guò)無(wú)性繁殖(如扦插)而來(lái),它們的基因其實(shí)都是相同或相似的,對(duì)病蟲(chóng)害抵抗力很弱;二是由于與銀杏共生的動(dòng)物大都已經(jīng)消失,其種子難以依靠這些動(dòng)物傳播;三是銀杏種子的發(fā)芽需要光照,而母株繁茂的枝葉恰巧會(huì)遮擋陽(yáng)光,會(huì)影響后代萌發(fā)。換句話說(shuō),一旦當(dāng)下的銀杏種群遭遇某種針對(duì)性強(qiáng)的病害,那么,能夠存活下來(lái)的銀杏可能少之又少。
銀杏最早出現(xiàn)于3.45億年前,是銀杏綱植物在地球上現(xiàn)存的唯一品種。因此銀杏也被看作是“活化石”“植物界的大熊貓”。位于成都青城山天師洞的樹(shù)齡1800多年的銀杏,以及位于成都市百花潭公園內(nèi)樹(shù)齡1300多年的銀杏,已陪伴了成都上千年。


刺梨
第三代水果,“維C寶庫(kù)”
刺梨是我國(guó)西南地區(qū)的特有野生植物,川西地區(qū)也有分布。刺梨屬于第三代水果,維生素C含量是蘋(píng)果的46~53倍,是獼猴桃的14~17倍,是水果中貨真價(jià)實(shí)的“維C寶庫(kù)”。
什么是第三代水果?第三代水果也被稱(chēng)為3G水果,這類(lèi)水果主要指的是那些自然生長(zhǎng)于偏遠(yuǎn)荒山與林地、尚未被充分商業(yè)化、保持野生狀態(tài)的植物果實(shí),以及一些近年來(lái)新發(fā)掘的優(yōu)質(zhì)和特色水果。這些野生水果的品種繁多,涵蓋了如余甘子、刺梨、沙棘、桑葚、鈣果(即歐李)、越桔、樹(shù)莓、香榧、野山葡萄、酸棗、黑莓、野薔薇等,它們不僅保持著原始的生態(tài)特性,還具有獨(dú)特的風(fēng)味與營(yíng)養(yǎng)價(jià)值,正逐漸被人們所認(rèn)識(shí)和珍視。
山槐
吹不散的“蒲公英”
那是合歡樹(shù)嗎?是!好像又不是!為什么會(huì)這樣說(shuō)呢,因?yàn)楹蠚g樹(shù)和山槐都同屬于豆科合歡屬這個(gè)大家族,又都是落葉喬木,開(kāi)花時(shí)期、二者的花型,甚至是葉片都幾乎一樣,不仔細(xì)分辨很容易把它倆混淆。看花色是最簡(jiǎn)單的區(qū)分方式:山槐只有白色、黃色兩種,而合歡花有粉紅色、白色、黃色、紅色、藍(lán)色、紫色、紫褐色等花色,其中以粉紅色最為常見(jiàn)。另外,山槐雖然屬于豆科家族,但它的葉子不會(huì)像合歡那樣晚上閉合起來(lái),反而是時(shí)時(shí)刻刻都大大咧咧展開(kāi)著,一副無(wú)所畏懼的樣子,這也是它們之間重要的區(qū)別之一。


泡桐
能被輕易扛起來(lái)的樹(shù)
泡桐,一類(lèi)人們耳熟能詳?shù)闹参铩W鳛樯L(zhǎng)極快、適應(yīng)力極強(qiáng)的樹(shù)種,短短幾十年時(shí)間,泡桐樹(shù)就成了成都房前屋后遮蔭的首選樹(shù)木。
泡桐被稱(chēng)為“輕”樹(shù),它究竟為什么會(huì)這么輕呢?
我們都知道樹(shù)木是由韌皮部、木質(zhì)部和髓心等部分組成。泡桐之所以輕,是因?yàn)樗撬偕尽S捎诳焖俚纳L(zhǎng)方式,泡桐樹(shù)的髓心、木質(zhì)部會(huì)隨著生長(zhǎng)而出現(xiàn)不均勻生長(zhǎng)的情況 (出現(xiàn)較大間隙), 這會(huì)給昆蟲(chóng)、真菌等生物提供更多入侵的機(jī)會(huì),導(dǎo)致空心。中間變空,樹(shù)也就輕了。
藍(lán)花楹
藍(lán)紫色的夢(mèng)幻點(diǎn)亮初夏的成都
初夏的成都,一些大街小巷被一抹一抹夢(mèng)幻的藍(lán)紫色裝點(diǎn)。藍(lán)花楹這種原產(chǎn)于南美洲的異域花卉,以一種獨(dú)特的色澤和優(yōu)雅的姿態(tài),迅速吸引市民與游客的目光。“成都什么時(shí)候有了這么多藍(lán)花楹”,成為不少市民時(shí)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
藍(lán)花楹適宜在陽(yáng)光充足且溫暖的地方生長(zhǎng)。以前,我們很少見(jiàn)到成都的藍(lán)花楹開(kāi)花。但近年來(lái),成都園林工作人員對(duì)其品種進(jìn)行了選育與優(yōu)化,讓藍(lán)花楹對(duì)成都的氣候表現(xiàn)出較好的適應(yīng)性,藍(lán)花楹變得隨處可見(jiàn),并且也愛(ài)開(kāi)花了。


芙蓉花
“變臉小能手”
成都又名“蓉城”,這個(gè)充滿詩(shī)意的名字,源自于美麗的芙蓉花。五代時(shí)后蜀皇帝孟昶為美化城市和取悅他喜愛(ài)芙蓉花的妃子花蕊夫人,下令在成都城內(nèi)外廣植芙蓉花,“蓉城”因此而得名。千百年來(lái),芙蓉花遍植城市大街小巷,深受市民喜愛(ài)。作為成都市的市花,芙蓉花也成為與這座城市相依相伴的文化符號(hào)。
不僅如此,芙蓉花還是一位“變臉小能手”。芙蓉花朝開(kāi)暮謝,有的品種一天可以變換3種甚至更多的顏色。早晨初開(kāi)時(shí),花朵在原花青素的作用下顯現(xiàn)為白色;到了中午氣溫逐漸升高,原花青素在酸性條件下逐漸轉(zhuǎn)化為花青素,芙蓉花的花色逐漸由白色變?yōu)樘壹t色;到了傍晚時(shí)分,花青素含量進(jìn)一步增多,花朵又由桃紅色變成深紅色。
大百合
大百合可不是野百合
我們常見(jiàn)的百合莖高不過(guò)1米,花兒也只有幾朵。但在成都某些地區(qū)的厚樸樹(shù)下,卻生長(zhǎng)著一種百合,不但莖可長(zhǎng)至2米高,而且單株花朵可多達(dá)20朵。當(dāng)它們?cè)谝巴獬善_(kāi)放時(shí),放眼望去,蔚為壯觀。它,就是百合科中“鶴立雞群”的大百合屬植物——大百合。
大百合會(huì)在每年12月至次年1月休眠。等到春天來(lái)臨,氣溫回升后,地下的鱗莖就會(huì)開(kāi)始萌發(fā),葉片舒展,花莖漸漸伸長(zhǎng),直至6月上旬至下旬的絢爛花期。同時(shí),在老鱗莖周?chē)置劝l(fā)出數(shù)個(gè)小芽繼續(xù)長(zhǎng)大成苗。6月下旬至12月上旬為果實(shí)發(fā)育和枯黃期,果實(shí)不斷膨大并發(fā)育成熟,同時(shí)肥厚的肉質(zhì)葉柄的養(yǎng)分逐漸被耗盡,逐漸萎縮腐爛。種球則在地下開(kāi)始休眠,靜待來(lái)年春天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