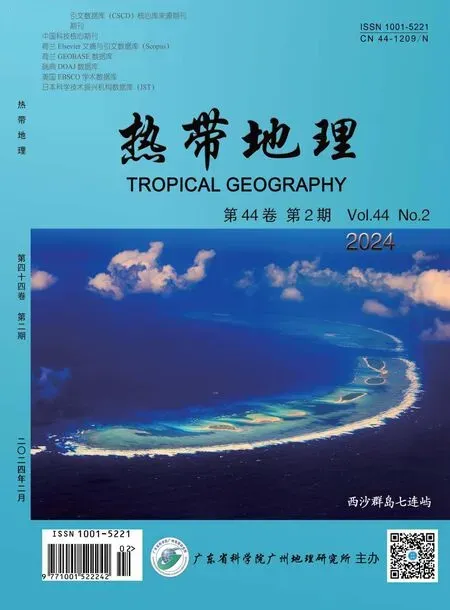基于生態本底-格局-潛力框架的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分區研究
——以粵港澳大灣區為例
張 偉,龍 鬧,李盛港,王 龍
(1.北京工業大學 城市建設學部,北京 100124;2.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廣州 510060;3.廣州市資源規劃和海洋科技協同創新中心,廣州 510060;4.廣東省城市感知與監測預警企業重點實驗室,廣州 510060)
指數級增長的人類活動深刻影響了全球范圍內的氣候變化與生態系統(Rockstr?m et al., 2009)。人類城市、村莊與工業區對森林、河流、濕地等典型生態系統的威脅與侵占,導致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削弱等問題,同時退化的生態系統進一步限制人類社會的發展(修晨 等,2020)。據統計,全球75%的千萬人口規模城市與超60%的經濟總量分布在100 km范圍的海岸帶,沿海人口密度約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灣區具有人口密集、經濟發達、城市化程度高等特點,高強度的人類活動與生態系統的矛盾凸顯(IPCC Working Group II, 2007)。因此,對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系統開展修復,恢復其重要生態服務功能,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
生態修復已成為全球共識(Suding et al.,2015)。國內外經過多年的探索實踐,形成針對不同自然要素的生態修復理論與技術。國外總結了諸如森林(Lamb et al., 2005; Wilson et al., 2015)、河流(Virgilio et al., 2011; Grizzetti et al., 2019)、濕地(Vito et al., 2018; Stephen et al., 2018)等典型生態系統的修復案例;中國在河流(董哲仁 等,2009)、礦山(張鴻齡 等,2012)、湖泊(秦伯強,2007)等生態區域的專項修復中積累了豐富的理論與實踐經驗。然而,著眼于單要素的局部整治修復對生態系統的整體性考慮不足(王軍 等,2020),生態修復需立足系統的整體性來深入思考局部與整體的內在聯系。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提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體”理念,強調生態修復要按照生態系統的整體性和系統性,從單點、單要素、單過程的修復轉向全域、全要素、全過程的協同治理(彭建等,2019)。
生態修復分區是科學開展生態修復的前提(田美榮 等,2017),其基于生態區劃演化而來,較為完整的生態區劃實踐可以追溯到貝利于1976 年(Bailey, 2009)提出的美國生態區劃(Ecoreg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國自20 世紀末以來逐步開展了生態區劃(劉國華 等,1998;傅伯杰 等,2001)、生態功能區劃(賈良清 等,2005)等研究,并將其拓展到空間規劃領域(汪勁柏 等,2008)。新時代生態文明與國土空間規劃語境下,生態修復理應擺脫傳統單要素、局部區域的路徑依賴,以生態修復分區的視角統籌協調各類要素的綜合修復(馬世發 等,2021)。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分區的現行技術方案包括生態安全格局構建(倪慶琳 等,2020)、生態系統服務供需分析(謝余初 等,2020)等,長期以來,修復分區研究從風險區識別的角度將自然生態系統作為本底,人類社會系統被視為本底的脅迫與風險。然而,生態修復既是一個自然過程,也是一個投入產出的經濟過程(Lv, 2011)。區域經濟博弈為生態修復帶來又一維度上的發展潛力,然而區域的社會經濟屬性在生態修復評估框架中仍未被系統性地采用(James et al., 2010; Wortley et al., 2013)。不同地理區位、自然條件的國土空間,在生態修復中存在經濟投入、政策支持等差異,社會經濟與自然資源的時空匹配成為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布局的核心(王晨旭 等,2021),生態修復分區需將人類社會系統帶來的空間修復潛力納入既有的理論、技術架構中,并思考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的沖突、協調與融合的問題,在考慮區域自然稟賦的前提下,結合經濟、政策支持,實現生態修復分區理論完善、技術方案優化,以提升生態修復實踐的成效。
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大灣區”)擁有全國超十分之一的經濟總量,經濟預期增速位于全球前列。在高速城市化的驅動下,大灣區建設用地不斷擴張,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矛盾突出。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保護生態列為發展的基本原則,要求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構建生態廊道和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提升生態系統質量和穩定性(中共中央,國務院,2019)。為此,本文以大灣區為例,在生態系統服務評價、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基礎上,嘗試將生態恢復潛力、修復效率納入研究范疇,建構了生態本底-格局-潛力評估框架進行生態修復分區,通過生態優先修復區的識別實現修復效率的提升。以期為大灣區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工作提供理論與技術支撐。
1 研究區概況
大灣區位于廣東省東南部(21o25'-24°30' N、111°12'-115°35' E),總面積約56 000 km2,由廣東省9 市與香港、澳門2 個特別行政區組成。截至2020 年末,總人口超8 600 萬人,GDP 逾11 萬 億元,以約0.6%的國土面積創造了超10%的生產總值(孫殿超 等,2022),是中國人口最密集、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也是繼紐約、舊金山和日本東京灣后的世界第四大灣區,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大局中占重要地位。誠然,大灣區經濟在過去40多年取得飛速發展,但也陷入嚴重的生態赤字中,生態壓力日益增大,區域空間發展面臨制約,大灣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關系(謝高地 等,2019)。因此,對其開展生態修復研究對維持大灣區在全球區域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數據涵蓋地理信息數據、氣象數據、土壤數據、社會經濟數據等(表1)。其中,遙感數據包括大灣區2010、2020 年2 期土地覆蓋數據、DEM 數據、NDVI數據(Yang et al., 2019),根據DEM數據進行水文分析得到流域數據;氣象數據為年均降雨柵格數據,根據年降雨量計算得到降雨侵蝕力因子;土壤數據來自世界土壤數據庫,依據沙含量(SAND)、粉砂含量(SILT)、黏粒含量(CLAY)以及有機碳含量(OC)計算得到土壤可蝕性因子;社會經濟數據分為夜間燈光數據與市縣經濟數據,市縣經濟數據主要統計市、縣GDP、節能環保支出等。

表1 生態系統服務與修復潛力評價數據說明Table 1 Descrip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 and restoration potential evaluation data
2.2 研究方法
建構生態本底、生態安全格局與生態修復潛力3個維度的技術框架(圖1),以鄉鎮為基本單元劃定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分區。首先,在生態本底維度對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進行評估,通過現狀服務水平與發展趨勢初判生態修復分區類型;其次,在生態安全格局維度構建生態網絡,借助復雜網絡理論分析網絡特征,修正不同分區類型的重要性級別;最后,在潛力維度評估各單元的生態修復潛力,得到生態修復近期應重點關注與考慮的區域類型。

圖1 生態修復分區劃定技術框架Fig.1 Technical framework for zoning ecological restoration
2.2.1 生態本底-生態系統服務評估 生態本底指修復工程實施前的區域生態系統平均狀況及變化趨勢(邵全琴 等,2016)。已有研究表明,生態系統服務水平與生態本底狀況呈正相關(彭建 等,2017a;趙文禎 等,2020),本研究通過生態系統服務綜合水平表征區域生態本底。
生態系統服務是自然生態系統自循環或與人類社會系統互動過程中,對人類社會系統直接或間接的貢獻,對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經濟發展起至關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最簡單的包括食物、燃料和材料的供應,也包括更基本的如土壤形成、水的控制和凈化,以及無形的舒適感、娛樂和美學價值(Hester and Harrison, 2010)。本文選取水源涵養、固碳、生境質量、土壤保持、游憩5種生態系統服務進行評估(表2),將結果歸一化后等權疊加,根據現狀水平與變化趨勢得到生態本底評價。

表2 生態系統服務評估方法Table 2 Method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assessment
2.2.2 生態安全格局-生態網絡構建與分析 生態安全格局的構建能提升對區域生態過程的調控能力,進而保障生態系統運行效率(彭建 等,2017b)。近年來,“源地識別-阻力面構建-廊道生成”已成為生態安全格局構建的邏輯范式(Peng et al., 2019)。源地是國土空間生態安全的核心區域,本研究將生態本底評估結果經篩選后作為源地;生態廊道是自然生態系統物質與能量流動的連通性通道,這些通道一般選擇遷徙阻力最小的方向,即最小阻力面(MCR)進行擴散、集結,進而形成生態網絡。本研究基于土地覆蓋數據,參考相關文獻(Christopher et al., 2009;王玉瑩 等,2019)對不同地類分別賦以初始阻力值(表3),并采用夜間燈光數據對其進行修正,得到綜合阻力面,計算方法為:

表3 土地覆蓋類型的初始阻力值Table 3 Initial resistance value of land cover type
式中:MCRa為柵格a修正后的綜合阻力值;TLIa為柵格a的燈光指數;TLIA為柵格a對應的地類A的平均燈光指數;Ra為柵格a的初始阻力值(王玉瑩 等,2019)。
基于生態源地和MCR,經過Linkage Mapper計算得到生態廊道,形成生態網絡。生態網絡是具有復雜網絡結構的網絡體系,生態網絡空間結構的維持構建區域生態安全格局的重要保障。生態網絡結構魯棒性能反映在遭受外界干擾或破壞時,網絡結構對于破壞的抵御能力與結構的恢復能力(Yu et al., 2018),其又分別被稱為網絡結構的連接魯棒性與恢復魯棒性(杜巍 等,2010),其中,連接魯棒性是網絡節點受擊后,剩余的節點間仍能保持連通的能力。通過連接魯棒性可以很好地對網絡結構進行優化(于強 等,2018)。連接魯棒性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R為連接魯棒性;N為初始網絡節點規模;Nr為去除的網絡節點數量;C為節點被去除后網絡中最大連通子圖中的節點數量 (于強 等,2018)。
2.2.3 生態修復潛力-自然恢復力與經濟政策助力耦合 恢復生態學理論是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的重要理論基礎之一,其不但強調通過工程和其他措施進行恢復(任海 等,2004),更強調生態系統的“自恢復”(曹宇 等,2019)。本研究將流域自然地理單元的自然恢復力與區縣行政單元的經濟政策助力相結合,表征生態修復潛力。其中,流域作為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自然地理單元,適用于進行自然恢復力評價。生態系統的自我恢復力通過景觀生態學中的景觀格局指標表征(王晨旭 等,2021),選取最大斑塊指數(LPI)、斑塊密度(PD)、連通性指數(CONNECT)、聚集指數(AI),以流域為單元進行等權疊加,并經過區縣行政單元的NDVI修正,表征自然恢復潛力。計算方法為:
式中:NPi為自然恢復潛力; LSII為流域單元i的景觀格局指數;NDVIi為柵格i所在縣域的植被覆蓋度;NDVII為單元i所在流域的植被覆蓋度。
生態經濟學的語境下,自然與人類系統的關系可用熱力學第二定律解釋,其中人類系統的經濟活動被視為一個耗散過程。隨著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生態退化速率加速,以增長為導向的全球發展范式下,自然和人類系統的可持續性相悖(Rees,2003)。人類系統必須努力與自然系統達成一種穩定狀態,而并非永久增長。這樣的“穩定狀態”意味著數量上的增長將被質量的提升取代(Herman,1991)。中國經濟已由增長為導向的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而環境保護、人與自然協調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保障(任保平 等,2018)。在此背景下,中央與地方政府在節能環保上的財政投入力度不斷加大、支出結構趨于完善(徐順青 等,2018),節能環保支出可以表征地方政府對生態環境安全的重視程度(王婭 等,2018)。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節能環保支出在一定程度上對生態環境治理有正向作用(張欣怡,2015)。環保支出占比更高的地區,其獲得政策支持的力度更大(丹宇卓等,2020)。因此,本研究核算2020 年縣區政府的GDP與節能環保支出比表征經濟政策助力,結合自然恢復力評價結果進行疊加評價,得到生態修復潛力分區。
3 結果與分析
3.1 生態本底
大灣區2期生態系統服務的空間分布格局存在顯著差異,圖2顯示,大灣區生態系統服務水平下降明顯,區域異質化程度漸深,呈現高度集聚的空間形態。根據冷熱點空間分布顯示(圖3),冷點代表的低值區主要位于大灣區核心地帶,包括廣州南部、佛山、中山以及東莞,且呈退化程度加重、不斷向往擴散的趨勢;熱點高值區主要位于西北部的肇慶、廣州北部、惠州東部、北部以及江門外圍地區。

圖2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本底分析Fig.2 Ecological background analysi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圖3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本底聚類分析Fig.3 Ecological background cluster analysis of th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全局與局部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表4)顯示,全局莫蘭指數(Global Moran'sI) 均為正相關,2010和2020年2期的指數分別為0.77和0.63,表明全局仍呈現高度正集聚,但高水平區聚集態勢逐漸破碎;2 期生態本底高-高集聚指數為24.62%和22.21%,下降2.41%;低-低集聚指數為37%和41.04%,上升4.04%;反映高值區集聚區域面積減少,表現在大灣區西南部江門市熱點區域的急劇減少;低值區集聚程度進一步加劇,表現在冷點區域自廣佛區域向中山、珠海蔓延;低-高、高-低異常點位占比下降,表明在低值區擴張過程中,其鄰近的高值區區域被迅速同化,高低值相鄰區域減少;與此相對應的,高值區中的部分低值區域得到恢復。

表4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系統服務聚類分析結果Table 4 Results of ecosystem services cluster analysis of the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3.2 生態安全格局
3.2.1 生態網絡 按照“源地識別-阻力面構建-廊道生成”的邏輯范式判別生態廊道。首先,將國家公園等重要生態區域納入源地考慮范圍,并將2010和2020年2期生態本底水平按4級自然斷點法進行等級劃分,選擇穩定在第一等級且面積>500 hm2的區域識別為源地;其次,通過土地利用覆蓋數據與夜間燈光數據修正得到綜合阻力面;最后,利用Linkage Mapper判別生態廊道。
經統計,生態源地共44塊,總面積870 527.07 km2,空間分布特征明顯(圖4)。其中,大灣區西北部地區生態源地大面積連片分布;東部地區源地呈塊狀分布,個別源地被高度城市化的建成區所包圍;西南部呈點狀零星分布。識別出生態廊道共88條,總長度2 324.53 km,平均長度26.42 km。東部與西南部之間的廊道路徑最長,長達117.84 km,其面臨的人類活動影響風險較大。從全局上看,源地與廊道分布有明顯的區域特征,西北部、東北部與西南部3個區域子網絡共同構成大灣區生態網絡。各個子網絡內部的能量流動、廊道寬度遠大于子網絡之間;東北部源地與西北部、西南部源地間的網絡聯系較差,存在一定的割裂風險。在區域內部,西北部地區源地密集,廊道平均長度為14 km,遠低于區域平均水平,其之間的物質循環、能量流動頻繁、密切,網絡結構穩定;東部源地與南部的零星生態源地廊道路徑較長,平均為104.16 km,聯系較為薄弱;西南地區源地呈環形分布于江門外圍,廊道主要分布于市域南部。

圖4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網絡Fig.4 Ecological network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3.2.2 網絡連接魯棒性 通過復雜網絡理論將源地識別為節點,廊道判別為邊,統計網絡特征。基于Python 語言模擬隨機和重點風險2 種情景,隨機情景下,隨機去除某一節點的同時移除與其相關的邊;重點風險情景下,按順序移除網絡中心度最大的點。網絡模擬打擊可以識別關鍵節點與關鍵邊,并計算得到網絡結構震蕩、崩潰閾值,作為分區修正的依據。圖5顯示,隨著攻擊規模的增加,網絡的連接能力逐漸下降,重點風險情景下網絡崩潰的閾值更低。當節點受擊數達到11 和13 時,重點風險情景下網絡的連接魯棒性(R值)出現劇烈震蕩,R值分別為0.73 和0.35;第22 次攻擊后R值低于0.1,此時網絡連通性極差,網絡結構崩潰。而隨機情景下,網絡R值下降速率較重點風險情景趨緩,震蕩閾值出現在受擊節點數13,直到去除節點數為22時,R值仍為0.45。

圖5 連接魯棒性模擬結果Fig.5 Connection robustness simulation results
3.3 生態修復潛力
大灣區存在“一國兩制、三關四核”的制度、社會、經濟空間異質性(張福磊,2019),各市的生態、經濟基礎,城市職能,所面臨的競爭壓力與實施的發展政策各有差異,因此,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方向各有側重,對生態保護的經濟支出水平不一。分區生態修復潛力結果表明(圖6),自然恢復力高值區主要位于肇慶,低值區位于廣州、佛山、中山及東莞;經濟政策助力高值區主要位于香港、廣州市東北部、肇慶及珠海南部,節能環保支出占比達到經濟總量的3%左右;低值區位于廣州市中部及南部、惠州市中部,節能環保支出占比不足萬分之一。總體上,自然恢復力與生態保護政策支持區域存在一定的空間錯配現象。

圖6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修復潛力分區Fig.6 Zoning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otential i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3.4 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分區
3.4.1 生態修復分區初判 基于生態本底-格局-潛力框架,參考相關研究(丹宇卓 等,2020;周汝波 等,2023),將大灣區生態修復分區初判為生態維持區、修復區、提升區與保護區4類(表5)。初判分區結果(圖7)顯示,生態保護區數量與面積分別占22.3%和44.5%,主要位于肇慶、廣州北部、惠州東部與北部,少量位于江門南部;生態維持區數量和面積分別占27.1%和7.7%,呈高度集聚狀態,主要分布在廣深核心城區范圍,以及佛山、中山、珠海、東莞、惠州城區;生態修復區數量和面積分別占37.3%和35.9%,分布于維持區與保護區的過度地帶;提升區數量和面積分別占13.3%和11.9%,部分提升區零星分布于維持區之間,是供給城市生態系統服務的關鍵地帶。

圖7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修復分區初判Fig.7 First judgment on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zon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表5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修復分區初判邏輯Table 5 Initial judgment logic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zoning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3.4.2 生態修復分區修正 根據生態安全格局與生態修復潛力分析結果對生態修復分區進行修正。首先,根據連接魯棒性分析結果,將生態保護區劃分為一級、二級與三級,一級和二級保護區是在遭受到惡意攻擊、隨機攻擊后,仍能使生態網絡維持較好連通功能的生態保護區集合,按照惡意打擊情景下生態網絡震蕩、崩潰的閾值進行劃分,其余則劃分為三級保護區。其中,一級保護區的聯系廊道所穿越的生態修復區、提升區,修正為一級生態修復區、提升區;其他廊道所穿越的修正為二級修復區、提升區;其余為三級。其次,在潛力維度評估各單元的自然恢復力水平(N),通過量化經濟政策助力(E)對自然恢復力進行修正,得到各單元的生態修復潛力評價結果,以此識別生態修復工作的經濟投入重點區域、實施成效性價比較高的區域。一級生態修復區中,優先修復區(N 前50%、E 前50%)是生態本底優越,自然恢復力強并得到政策重視,有較高環保經費投入的區域;協同修復區(N前50%、E后50%)是自然恢復力強,生態修復項目實施性價比較高,但目前投入經費不足的區域。修正分區結果如圖8所示。

圖8 粵港澳大灣區生態修復分區Fig.8 Ecological Restoration Zone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生態保護區中,一級區共58個,主要分布于大灣區北部,位于肇慶、惠州東部、江門南部與廣州北部,這些區域是大灣區生態安全格局的底線區域;二級區共37個;主要分布于大灣區西北部與東北部,是區域內重要的生態源地,對維系生態格局的穩定起重要作用;三級區共51個,散落分布于大灣區外圍,對生態網絡的連通性與復雜性提升作用顯著。
生態修復區中,一級區共64個,其中優先修復區28個,協同修復區8個(表6),主要分布于佛山西部、廣州南部與北部,以及惠州、東莞與深圳3市相鄰區域,這些區域處在高度城市化區域外圍,承擔向城市內部供給各類生態系統服務的功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二級區共38個,主要分布于廣佛莞3市與肇慶、江門、惠州接壤地帶,作為都市圈與自然地區的過度地帶,承擔著作為生態屏障的重要作用;三級區共161 個,主要分布于廣佛珠莞4市內部及其城市核心區外圍地帶,這些區域深受人類活動的影響,同時為城市內部生態系統的穩定提供大量生態系統服務,生態價值較大。
生態提升區中,一級區共26個,主要分布于肇慶、惠州南部,多數與一級生態保護區接壤,生態本底優越、提升潛力大;二級區共10個,主要分布于肇慶、惠州、深圳市境內,這些區域是生態保護區之間能量流動、物質循環的介質區,承擔大量的生態流動;三級區共51個,主要分布于廣佛珠莞4市外圍地帶,少數位于江門、肇慶市內部,這些區域生態本底良好,是區域生態網絡結構優化、提升的理想備選區。
4 討論
目前針對大灣區的生態修復分區研究中,多以生態系統服務供需視角,抑或是基于生態安全格局理論進行(馬世發 等,2021;周汝波 等,2023)。其中,生態系統服務多借助InVEST 等模型工具,對供給、調節、支持與文化4類服務進行分析,能比較好地量化生態系統對人類的貢獻;生態安全格局構建以“源地識別—阻力面構建—廊道生成”作為主流邏輯范式,通過特定的景觀斑塊、生態廊道以及兩者共同構成的景觀網絡結構,實現區域生態系統局部空間與整體結構的保護。以生態系統服務供給、生態安全格局分析等作為切入點確是行之有效的技術方案,但這些研究本質上是從風險區識別的角度進行分區劃定,然而,生態修復是人類社會的產物,是一個投入產出的經濟過程。修復分區的研究除了需要精準識別國土空間中的生態風險區域外,同樣應該考慮如何評價區域生態保護政策與經濟差異,因地制宜地開展生態修復,有針對性地提高環境保護資金投入效率和生態保護成效,這也是未來國土空間生態修復研究的重點之一。因此,本研究構建了基于生態本底-格局-潛力的技術框架,在現行技術范式的基礎上,將社會經濟與自然資源的時空匹配納入考慮,通過識別優先修復區與協同修復區,以期提升生態修復政策實施效率,對現有范式進行補充與完善。
針對本研究得到的分區類型提出差異化的規劃管制策略。生態維持區主要為高度城市化的建成區,其生態修復策略應以綜合改善為主,促進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生態保護區是區域重要的生態源地區域,對維系生態格局的穩定起重要作用,應以保護為主,減少人工介入,加大政策管制力度;生態提升區是生態保護區之間能量流動、物質循環的介質區,承擔大量的生態流動,是區域生態網絡結構優化的理想備選區,應通過多樣化、持續的生態維育措施為主,以強化區域生態網絡的冗余度;生態修復區分布于深受人類活動的影響的區域,此中,優先修復區是擁有較高的自然恢復力與政策扶持的地區,應當以實施長期、漸進式的修復工程為主;協同修復區擁有較高的自然恢復力,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應當協同上級政府或區域聯合治理,提高對生態保護、修復的經濟投入;其他低自然恢復力地區應側重于生態系統重構,采取人工重建的工程措施進行生態系統恢復。
此外,雖然本研究以現行的生態系統服務、生態安全格局理論架構為基礎,從人地耦合的視角綜合考慮自然生態系統的自然恢復力,以及表征區域生態保護政策差異性的環境保護經濟投入,為生態修復分區研究提供新的角度,但依然存在以下難點:1)以行政區作為生態修復分區單元雖然便于分區成果的應用與管理,同時能比較準確地獲得環境保護經濟投入數據,但相對于自然地理單元如流域等,其未能很好地反映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在未來應因地制宜綜合考慮自然地理單元與行政單元的優勢,探究兩者相結合的分區模式;2)受限于數據的尺度與可獲性,爬取區縣的節能環保大類支出,表征生態修復潛力的經濟維度,在量化表達生態保護、修復的政策助力上仍有不足,未來應從更為具體的生態修復規劃、實施項目的經濟投入數據,生態補償以及上級政府的財政轉移支付數據進行修復潛力的綜合厘定。
5 結論
本研究基于多源數據與相關生態評價分析方法,評估大灣區水源涵養、固碳、生境質量、土壤保持與游憩5種生態系統服務水平,同時通過生態網絡構建,并將生態恢復潛力、修復效率納入考慮,劃定大灣區國土空間生態修復分區,并針對各分區的自然與經濟屬性提出差異化的保護修復策略,主要結論如下:
1)受城市化導致的土地利用變化影響,大灣區2010年與2020年2期生態系統服務水平的空間分布格局存在顯著差異。十年間,生態系統服務水平下降明顯,區域異質化程度漸深,呈現高度集聚的空間形態。低值區主要位于大灣區核心地帶,包括廣州南部、佛山、中山以及東莞,且呈環狀不斷向往擴散的趨勢,退化程度加重;高值區主要位于西北部的肇慶、廣州北部、惠州東部、北部以及江門外圍地區。
2)源地與廊道分布有明顯的區域特征,西北部、東北部與西南部3個區域子網絡共同構成大灣區生態網絡。各個子網絡內部的能量流動、廊道寬度遠大于子網絡之間;東北部源地與西北部、西南部源地間的網絡聯系較差,存在一定的割裂風險。在網絡魯棒性模擬中,重點風險情景下網絡崩潰的閾值為22次,較隨機情景更低。
3)自然恢復力良好與保護政策支持強的地區存在空間錯配。以鄉鎮為單元進行生態修復分區,生態維持區占總面積的7.7%,應以綜合改善為主,促進經濟與生態的可持續;生態保護區面積占44.5%,作為生態安全的底線區域,應以保護為主,加大政策管制力度;生態提升區面積占11.9%,應通過多樣化、持續的維育措施為主,以強化區域生態網絡的冗余度;生態修復區面積占35.9%,此中,優先修復區是擁有較高的自然恢復力與政策扶持的地區,應以實施長期、漸進式的修復工程為主;協同修復區擁有較高的自然恢復力,但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應當協同上級政府或區域聯合治理,提升區域整體修復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