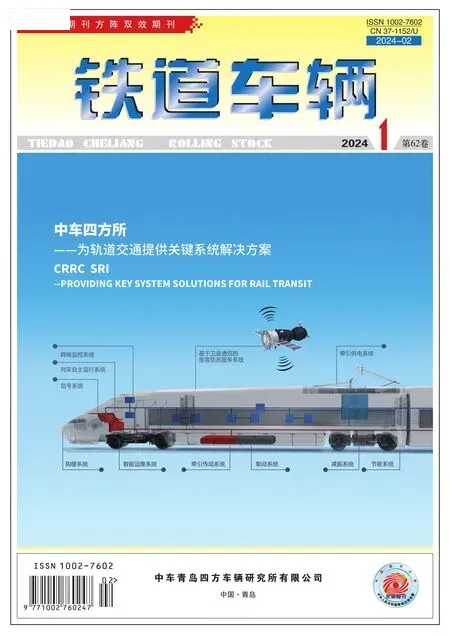氣動載荷對高速列車車體強度的影響研究
馮 振,李明理,張璟鑫
(中車青島四方機車車輛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中心,山東 青島 266111)
列車在高速運行時,會帶動列車周圍的空氣隨之運動,形成一種特定的非定常流場,通常稱之為“列車風”[1]。列車風致使列車附近環境空氣壓力波動,并引起強烈的空氣流動。兩列高速運行的列車會車時,在交會的瞬間,空氣擾動會猛烈加劇,形成一種瞬態壓力沖擊波,尤其是在列車的頭部或尾部交會時,會引起該列車交會側側墻表面的壓力突變[2],即在約幾十秒內出現正負壓力波動,該壓力波動可能會導致車廂產生較大變形、列車瞬態橫擺過大等,嚴重影響行車安全和乘客乘坐舒適性[3-4]。我國對這一空氣動力學問題相當重視,將列車會車過程中壓力波動的考核定為列車運行安全評估的重要項點之一,并在高速列車的研發過程中將壓力波動幅值作為車體外形設計的主要考量指標。隨著列車運行速度的提高,高速列車氣動載荷對車體結構強度的影響越來越顯著,但其是否達到我們所關心的比率,是必須研究的問題。目前國內研究僅限于研究會車過程中車體壓力分布和氣動作用力變化,并未深入將氣動載荷施加到車體上對車體進行強度評估,也未對氣動載荷的加載方式有所討論。本文以高速列車明線會車壓力波動為載荷輸入源,將車體特定測點瞬態壓力波時間積分轉化為車體側墻表面的多工況載荷,依次加載各工況模擬整個交會過程的氣動載荷,并討論了其對車體結構強度的影響。
1 車體有限元模型建立
該車體由底架、側墻、車頂和端墻組成,車體采用車輛全長的大型中空擠壓鋁合金型材焊接而成。相較于車體縱向和橫向尺寸,型材板厚尺寸很小,符合薄板理論的要求,可以忽略沿厚度方向的應力變化。
本文采用有限元分析軟件中的殼單元對車體進行有限元分析。參照車體的實際結構選擇合適的單元尺寸,對車體局部位置進行人工網格控制,使整個模型具有較好的網格精度。遵循有限元分析精度和求解經濟性相協調的原則,通過有限元網格的收斂性檢查,最終確定了車體有限元模型,如圖1所示,車體有限元模型共包含155 226個單元、116 021個節點。

圖1 車體有限元模型
2 氣動載荷工況確定
2.1 車體瞬態氣動載荷
高速列車交會分為明線會車和隧道會車2種情況。相較于明線會車,隧道交會的壓力波動更為劇烈,隧道交會壓力波動受列車運行速度、隧道長度、隧道橫斷面尺寸、列車交會位置距隧道出入口距離等因素影響,波形復雜多變。相比之下,明線會車壓力波波形更加典型,故本文以明線會車為例,提出了一種氣動載荷的加載方式,實際工程需考慮隧道會車壓力波動并為之展開深入研究。
本文以高速列車明線等速會車壓力波動為載荷輸入源,交會側的典型壓力波[5]如圖2所示。

圖2 明線會車交會側典型壓力波波形圖
對于非交會側,由于高速列車在空曠地帶交會,非交會側的氣動載荷波動變化很小,對車體結構強度貢獻較小[6],本文不予考慮,重點考慮交會側的壓力波動。同時,根據實車試驗數據和模擬仿真數據[7]可知,車體側墻同一縱向位置處的測點壓力波動幅值隨測點高度的降低而增大,原因在于測點越接近地面,交會時該區域空氣受擾動越劇烈;但幅值變化不大,故本文取車體同一縱向位置處壓力幅值最大值代表該縱向位置的壓力幅值,即模擬最惡劣的狀況。此時,交會過程即可看成一條垂向壓力波線縱向掃掠過車體側墻表面。
2.2 氣動載荷時間積分轉化
模擬仿真數據和實車試驗得到的是車體特定測點的瞬態壓強,研究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影響首先需將該瞬態壓強轉化為整個側墻表面上的載荷,在此對該瞬態壓強采用時間積分的方法。壓力波動數據參考數值模擬分析的300 km/h等速交會數據[8],為能完整地表達列車交會過程中氣動載荷對車體結構的影響,同時考慮計算機的計算能力和計算時間,取氣動載荷波動較為劇烈的頭波部分作為載荷輸入,如圖3所示。計算區域時間步長劃分越精細越接近瞬態載荷作用,但同時也意味著計算量的增加。列車交會時正負壓力波動約為0.18 s,綜合考慮結果精確性及計算經濟性,將該區域分為10個時間步長,每個時間步長間隔為0.018 s,如圖4所示。

圖3 應力波動計算區域

圖4 計算區域時間步長圖
列車以300 km/h等速交會,在每個時間步長內,該壓力波掃掠過的距離為:
(1)
確定每個時間步長壓力波掃掠過的距離為分區長度,該車體長24.168 m,故將車體部分劃分8個分區,分區1至分區7的縱向長度為3 m,分區8的縱向長度為3.168 m,如圖5所示。

圖5 氣動載荷車體分區圖
每個時間步長壓力波掃掠過的距離s對應車體上1個分區,瞬態壓強與該分區平均壓強關系如下式:

(2)

將s=vt代入式(2)得:
(3)
式中:v為列車運行速度,t為時間步長。
求得分區平均壓強為 :
(4)
由式(4)可以發現,分區平均壓強數值等于瞬態壓力波時間積分與時間步長的比值,對10個時間步長進行時間積分,求得10個時間步長平均壓強,如表1所示。

表1 壓力波各時間步長平均壓強 Pa
2.3 確定氣動載荷工況
第一時間步長壓力波到達車體分區1時記為第一工況,此時壓力波剛到達車體側表面;第十時間步長壓力波到達車體分區8記為最后1個工況,此時壓力波已經掃掠過整個車體側墻。共有17個工況,每個工況下8個分區壓強如表2所示,其中壓強值為正表示壓力垂直側墻表面指向車體內部,壓強值為負表示壓力垂直側墻表面指向車體外部。

表2 氣動載荷工況列表 Pa
上述17個工況按順序加載即代表壓力波掃掠過車體側墻的整個過程。加載時,對于車門和車窗處載荷,考慮到實際情況,根據其面積和不同工況下該分區的壓強,分別計算出車門和每個車窗上承受的壓力,將該壓力對應加載到車體有限元模型車門邊框和車窗邊框上的節點上,即門窗上的力均勻分散到門框和窗框上。
3 氣動載荷計算結果分析
3.1 車體“關注點”當量應力
為了研究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的影響,增加1個垂向靜載工況(不加載氣動載荷,僅有垂向載荷),并在車體上選取12個“關注點”,對比氣動載荷加載前后這些“關注點”當量應力的變化,“關注點”具體位置為:點1、點2分別為1位端和2位端的空氣彈簧位置處;點3、點4為底架集中設備懸掛處;點5為車門上邊角位置處;點6至點12分布在車窗窗角位置處。
未加載氣動載荷,即在垂向靜載工況下,上述“關注點”當量應力如圖6所示。以氣動載荷工況8為例,該工況下“關注點”當量應力如圖7所示。

圖6 垂向靜載工況“關注點”當量應力

圖7 工況8“關注點”當量應力
為了更直觀地對比研究氣動載荷對車體結構強度的影響,將各“關注點”在不同工況下(工況18垂向靜載工況)的當量應力做成柱狀圖,以“關注點”5和“關注點”8為例,其各工況下當量應力柱狀圖如圖8和圖9所示。對比這2個“關注點”數據圖發現,受氣動載荷影響,這2個“關注點”當量應力幅值分別為10 MPa和15 MPa左右,可見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的影響是相當顯著的。

圖8 “關注點”5各工況應力柱狀圖

圖9 “關注點”8各工況應力柱狀圖
3.2 氣動載荷強度貢獻率
評估車體強度時相關文獻將氣動載荷與其他載荷疊加組合[9-10],未量化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的影響。為定量研究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的影響,在此我們定義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貢獻率δ,計算公式如下:
(5)
式中:σ為未加載氣動載荷,即垂向靜載工況作用下“關注點”當量應力;σmax為加載氣動載荷各工況下該“關注點”最大當量應力。
通過δ值反映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的影響,其結果數據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相比于車體底架,氣動載荷對側墻影響更大,主要體現為對車體門角及窗角處強度貢獻率較大,其中對于車體門角和第三車窗窗角處影響最大,強度貢獻率分別達到了24.10%和37.30%。原因在于車門和車窗上的氣動載荷作用到車門和車窗邊框上時,受氣動載荷影響大。

表3 氣動載荷對車體底架“關注點”強度貢獻率
4 結論
本文以某動車組車體為研究對象,參照其模擬仿真的300 km/h明線等速交會車體測點壓力波數據,首次對氣動載荷加載方式進行了討論,并在車體上選擇“關注點”,通過對比氣動載荷加載前后“關注點”當量應力分析了計算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的影響,主要得出以下結論:
(1) 提出了一種列車氣動載荷加載方法,即將車體測點的瞬態壓強通過時間積分轉化為車體整個側墻上的氣動載荷,從而使瞬態過程轉化為多工況來模擬會車過程中的氣動載荷作用。
(2) 相比于車體底架,氣動載荷對車體側墻影響更大,主要體現為側墻車門、車窗角及車頂設備安置處,最大強度貢獻率達到了37.30%,出現在第三車窗窗角處;氣動載荷對車體強度影響十分顯著,在車體強度評估過程中考慮氣動載荷是相當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