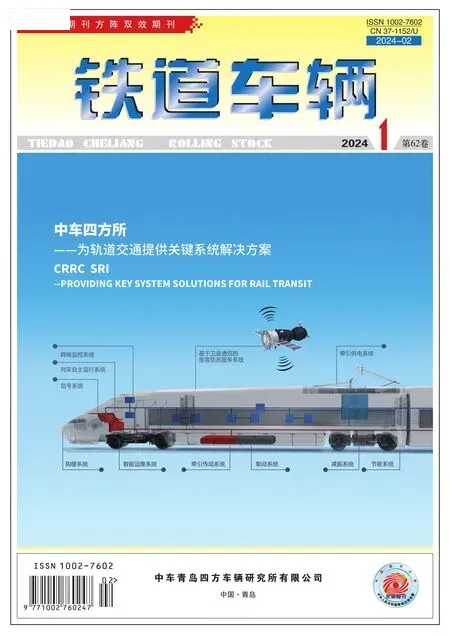某型高鐵踏面廓形輪軌接觸特性的對比分析
王興遠,沈 鋼,董強強,毛 鑫
(1.同濟大學 鐵道與城市軌道交通研究院,上海 201804;2.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動車段,上海 201812)
輪軌系統是鐵路交通運輸的核心,列車的啟動、運行和制動都需要依靠輪軌力實現[1],因此輪軌的接觸特性會影響列車的動力學性能、安全性能及經濟效益[2]。車輪踏面出現問題會導致輪軌接觸特性惡化,主要解決方案為鏇輪或換輪。在輪對日常維護中,車輪踏面探傷設備一旦探測到有裂紋存在便需要進行鏇輪。我國某型高速動車組在實際運用中,車輛運行20~25萬km時就需要鏇輪,部分車輪踏面甚至出現了嚴重的內部裂紋擴展,深度一般為8~10 mm。為消除疲勞裂紋,鏇輪深度高達10 mm,因為踏面的最大鏇輪量僅30 mm左右,新輪鏇修2~3次就需要更換。因此每年對于輪對踏面維護的投入很多,大大增加了高速鐵路的運營成本。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對該型動車組踏面[3](以下簡稱“現用踏面”)的輪軌接觸特性進行深入研究。
1 計算現用踏面輪軌接觸點
輪軌接觸點的位置對于車輛的動力學性能及車輪的使用壽命具有重要影響,若輪軌接觸點分布位置過于集中,車輪磨耗趨于集中,會加快其滾動接觸疲勞;若輪軌接觸點分布位置過于分散,又會影響車輛的動力學性能,甚至影響車輛運行安全[4]。因此首先計算現用踏面與我國高速鐵路主要使用的60軌和60N軌[5]的幾何接觸分布特性。
計算結果如圖1所示,現用踏面與2種鋼軌的零位接觸點偏向鋼軌內側約6~7 mm,輪對橫移量±4 mm范圍內的軌面接觸點偏移僅2~3 mm,按接觸斑半軸7.5~10 mm計算,光帶的寬度為17~23 mm。

圖1 現用踏面與60軌、60N軌的接觸點
2 計算現用踏面輪軌接觸應力
輪軌滾動接觸應力是輪軌接觸破壞的主要原因,而最大接觸應力是輪軌破壞的決定性因素[6]。為進一步驗證現用踏面與2種鋼軌的接觸是否存在應力集中,采用有限元軟件Abaqus建立輪軌接觸模型[7],如圖2所示。

圖2 輪軌接觸模型
考慮實際輪軌接觸區域僅存在于接觸斑處,且輪對僅有車體載荷垂向向下,因此建立半輪對模型,半徑為460 mm。三維鋼軌實體由其二維廓形拉伸而成,同樣考慮輪軌接觸斑,建立鋼軌長度為80 mm,鋼軌底面全約束,鋼軌縱向兩端面自由度被約束。在劃分網格時對輪對中部接觸扇形區域進行網格細化,輪對的載荷及約束通過耦合輪對中心點的方式施加,考慮該型動車組的軸重為17 t,因此施加的載荷為85 000 N。
首先,對現用踏面分別與2種鋼軌在零位時的接觸應力進行計算,應力云圖如圖3所示。

圖3 零位時現用踏面輪軌接觸應力云圖
由圖3可知,當處于零位時,現用踏面與2種鋼軌的最大接觸應力在1 000 MPa左右,且最大應力區域為點狀,容易產生應力集中。
隨后對輪對在-10~10 mm橫移量下,分別對踏面與60軌、60N鋼軌的接觸應力進行計算,整理數據繪制最大輪軌接觸應力與橫移量關系如圖4所示。

圖4 現用踏面與60軌、60N軌在不同橫移量下的最大輪軌接觸應力
由圖4可知,現用踏面與2種鋼軌的最大輪軌接觸應力一般在1 000 MPa左右,特別是在滾動圓附近,最大輪軌接觸應力一般高于1 000 MPa。如此高的接觸應力且滾動圓附近存在應力集中,極易出現疲勞裂紋。
3 W01GT3型踏面廓形介紹
針對某型動車組現用踏面輪軌接觸出現的問題,本文介紹了一種W01GT3型踏面,此踏面廓形由同濟大學沈鋼等根據實測鋼軌平均典型廓形的高鐵踏面設計而來[8]。圖5為W01GT3型踏面與現用踏面的外形對比圖,以踏面名義滾動圓處為共同原點建立坐標系,可見2種廓形由輪緣頂至橫坐標為-54.2~+4.6 mm區段幾乎一樣。如圖6所示,在-54.2~+4.6 mm區段的法向差異均值為0.042 9 mm,方差為0.127 0 mm,并可見是波動的。圖7為+4.6~+64.2 mm區段的法向差異,可見在+4.6 mm處有一明顯的傾斜,然后是一個等高抬升,數值在0.9 mm左右。

圖5 W01GT3型踏面與現用踏面廓形對比

圖6 -54.2~+4.6 mm區段的法向差異

圖7 +4.6~+64.2 mm區段的法向差異
4 W01GT3型踏面輪軌接觸點計算
圖8為W01GT3型踏面分別與60軌、60N軌的輪軌接觸點分布,軌底坡為1∶40,軌距為1 435 mm。可見,接觸點零位在鋼軌軌頂中部,當橫移量在±4 mm范圍內時,軌頂接觸點偏移量在10 mm左右,優于同等橫移量下現用踏面的2~3 mm。仍按接觸斑半軸為7.5~10 mm計算,光帶寬度應該為25~30 mm,同樣優于同等橫移量下現用踏面的17~23 mm。

圖8 W01GT3型踏面與60軌、60N軌的輪軌接觸點
5 2種踏面輪軌接觸應力對比
采用前述同樣的方法在Abaqus軟件中建立踏面為W01GT3型半輪對模型,對踏面分別與2種鋼軌在零位時的接觸應力進行計算,應力云圖如圖9所示。

圖9 零位時W01GT3型踏面輪軌接觸應力云圖
W01GT3型踏面與2種鋼軌的最大接觸應力為500 MPa,僅為現用踏面最大接觸應力的一半,最大應力區域為條狀或兩點,應力水平較小且沒有出現應力集中現象。
隨后對輪對在-10~10 mm橫移量下,分別對踏面與60軌、60N軌的接觸應力進行計算,整理數據繪制最大輪軌接觸應力與輪對橫移量關系,如圖10所示。為方便對比,圖10中同時繪制了現用踏面的計算結果。

圖10 最大輪軌接觸應力與輪對橫移量的關系
由圖10可得:
(1) 當鋼軌為60N軌時,輪對橫移量由-10~10 mm變化過程中,現用踏面最大輪軌接觸應力在1 000 MPa左右,變化幅度不大;W01GT3型踏面在名義滾動圓及左側接觸時,最大應力約為500 MPa,當輪對向兩側移動時,輪軌接觸應力逐漸變大,且當輪對橫移量為負即輪緣貼近鋼軌時的接觸應力,要比輪對向右橫移即輪緣遠離鋼軌時的接觸應力大。
(2) 當鋼軌為60軌時,輪對橫移量由-10~10 mm變化過程中,現用踏面的最大輪軌接觸應力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W01GT3型踏面則在名義滾動圓附近的最大接觸應力最小,向兩端移動后接觸應力增大。當輪對橫移量為負時,接觸應力變化較大,但仍低于現用踏面接觸應力。
(3) 無論是60軌還是60N軌,W01GT3型踏面在輪緣貼近鋼軌時的輪軌接觸應力大于輪緣遠離鋼軌時的輪軌接觸應力;W01GT3型踏面與鋼軌的最大接觸應力均小于現用踏面,特別是在名義滾動圓附近,W01GT3型踏面的最大接觸應力僅為現用踏面的一半。分析原因認為:W01GT3型踏面輪軌接觸面積明顯大于現用踏面,導致同樣的載荷下W01GT3型踏面的接觸應力比現用踏面小。
6 基于Fatigue的疲勞裂紋萌生壽命對比
根據以上應力計算結果,將零位時有限元模型及計算結果導入疲勞分析軟件MSC.Fatigue,計算直線工況下的疲勞裂紋萌生壽命[9]。設置載荷縮放因子為1,即保持Abaqus里的載荷設置,載荷譜時間歷程如圖11所示。設置材料屬性為楊氏模量2.07×105MPa,抗拉強度895 MPa,滿足鐵路車輪用鋼材料分析要求[10],分析結果如圖12所示。因W01GT3型踏面與60N軌的接觸部分云圖為細長狀,為方便觀察,圖12(d)所示接觸部分云圖的縱向長度與實際長度比例為3∶1。

圖11 載荷譜時間歷程

圖12 疲勞裂紋萌生壽命云圖
根據計算結果,直線工況下,現用踏面與60軌匹配的疲勞裂紋萌生壽命為1.27×106次循環,大約為3 671 km;與60N軌匹配時為1.76×106次循環,約為5 086 km。W01GT3型踏面與60軌匹配的疲勞裂紋萌生壽命為1.10×107次循環,與60N軌匹配時為1.01×107次循環,約為27 000 km。可知,現用踏面的云圖呈塊狀,W01GT3型踏面的云圖呈長條狀,分別與其應力云圖結果一致。直線工況下,W01GT3型踏面的疲勞裂紋萌生壽命遠高于現用踏面,具有優良的疲勞性能。
7 總結
我國某型高速動車組現用踏面與60軌、60N軌的輪軌接觸應力較大,且存在應力集中現象。相比于現用踏面,W01GT3型踏面能夠改善輪軌接觸點分布,降低應力集中,提升疲勞裂紋萌生壽命。針對此型高鐵輪對踏面鏇修維護時,建議改變原有策略,將廓形模板定義與W01GT3型踏面相近,以提高疲勞壽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