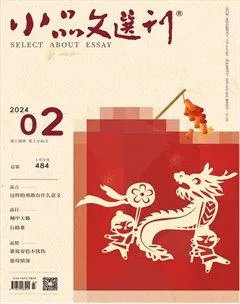婚姻的真相
波伏娃
從傳統說來,社會賦予女人的命運是婚姻。大部分女人今日仍然是已婚的、結過婚的、準備結婚或者因沒有結婚而苦惱。
獨身女人的定義由婚姻而來,不論她是受挫折的、反抗過的,甚或對這種制度毫不在乎。
女性狀況在經濟上的演變,正在動搖婚姻制度,婚姻變成通過兩個自主的個體自由贊同的結合;配偶的締約是個人的,也是相互的;對雙方來說,通奸是對婚姻的違約,離婚可以由雙方在同等條件下達成。
女人不再受到生育職能的限制,這種職能失去了大部分自然奴役的性質,它呈現為一種自愿承受的負擔;而且它與生產勞動同化了,因為在許多情況下,懷孕所要求的休息時間里,國家或雇主必須給母親支付薪金。
然而,我們生活的時代,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來,仍然是一個過渡時期。只有一部分婦女參加生產,甚至她們也屬于古老的結構、古老的價值依然殘存的社會。現代婚姻只能根據它延續的過去來理解。
婚姻對于男人和女人,向來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兩性彼此必不可少,但這種需要從未曾在他們之間產生相互性;女人從來不構成一個與男性在平等基礎上進行交換和訂立契約的等級。
在社會上,男人是一個自主的完整的個體;他首先被看做生產者,他生存的正當性通過他給群體提供的勞動來證實;我們已經看到,女人受制于生育和家務的角色不能給她保證同等的地位的原因。
當然,男性需要她,對于大多數男人來說,將某些苦活推給妻子是有利的;男人希望有穩定的性生活,希望有后代,而且社會也要求他為延續它作出貢獻。
少女的選擇自由一向是十分有限的;而獨身——除了它具有神圣性質的特殊情況——使她降低到寄生者和賤民的地位;結婚是她唯一的謀生手段和使她的生存獲得社會認可的唯一方式。婚姻被以雙重名義強加給她:她應該為共同體生孩子。
少女就是這樣顯得絕對被動,她出嫁,在婚姻中被父母獻出去。男孩子則是結婚,娶妻。他們在婚姻中尋找自己生存的擴大和確認,而不是尋找生存的權利本身,這是他們自由承擔的一項義務。
因此,他們能夠權衡利弊,像古希臘和中世紀的諷刺作家所做的那樣;對他們來說,這只是一種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命運。他們可以選擇獨身的寂寞,有些男人很晚結婚或者不結婚。
而在剛結婚的頭幾年,妻子往往妄想以為丈夫和兒女是缺少不了她的,她全心全意地崇拜丈夫,毫不保留地愛他。
不久,她漸漸明白,丈夫沒有她也可過活,兒女們遲早要問心無愧地離開她。家不再能填補她的空虛,她發覺自己很孤單、很氣餒,也不知該拿自己怎么辦才好。
和家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以及過慣了的生活,也許可以令她心安理得,但卻不能拯救她。誠實的女作家們都承認了“三十歲女人”心中的憂郁,凱瑟琳·曼斯菲爾德、多羅西·帕克、弗吉尼亞·伍爾芙等女作家筆下的女主角們,都有此共同感悟。
在剛結婚和剛做母親的時候,她們都快樂地吟誦著。但不久都表現了某種苦惱。在法國,三十歲以下已婚婦女的自殺率比未婚女子的自殺率低,但三十歲以上已婚婦女的自殺率便比未婚女子的自殺率高,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
婚姻的悲劇不是它沒有保證女子幸福——幸福原不是能保證的——而是它摧毀了她,叫她去做千篇一律、重復不休的工作。
女子頭二十年的生活,是異常豐富的;她發現了世界、發現了自己的命運。二十歲左右,她成為一家的女主人,永遠被束縛在一個男人身上,手里抱著小孩,她的生活差不多就此結束。真正的活動,真正的工作,是她丈夫的特權;她只有一些有時令人厭倦卻從不使人滿足的瑣事。她的順從和專一,雖然得到贊美,但忙著“照顧兩個人的生活”,對她的確沒有好處。忘掉自己固然很好,但也要知道到底為誰,為什么。
最糟的是,她的熱心似乎往往令人討厭和起反感,丈夫把她的熱心當做一種暴虐而想逃避,然而他卻是那個強迫妻子把獻身家庭當做至高無上的生存意義的人。娶了她后,他強迫她將全部獻給他,但他并沒有接受相對的義務,即全盤接受這個禮物以及所有的后果。
丈夫的言行不一致,使妻子蒙受不幸,然而他還要抱怨他才是這不幸之下的犧牲者。如同要求她在性行為上既熱情又冷靜一樣,他要求她專心從一但不要帶累他;他希望她給他一個安定的家,而同時要讓他自由;他要她擔當枯燥的日常工作,卻不許令他覺得單調;他要她在身邊隨時待他呼喚,而又不許她催迫他;他要完全占有她,卻不肯把自己交給她;他要和她過親密的生活,但又不許她纏住他。所以,她從結婚那天開始就被欺騙了。
她這輩子是完了,她計算著受騙的程度。勞倫斯所描述的性愛關系大體是正確的。兩個人若為了互相彌補缺陷才結合,則注定是要受折磨的。婚姻是要聯合兩個完整的獨立個體,不是一個附和,不是一個退路,不是一則逃避或一項彌補。
易卜生的“娜拉”明白這一點,她決定在做一個賢妻良母之前,要先做一個完整的人。夫妻不應被看成一個單位,一個與外界隔絕的細胞,每一個人都應該是社會的一部分,可以獨立自由發展。然后同樣能適應社會的兩個人,才能大大方方地聯合,男女的結合才能建立于互相認清對方的自由之上。
選自《第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