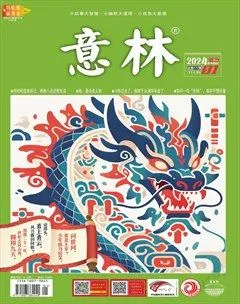貼一身五湖四海的膘
陳曉卿

立秋那天,同事們?nèi)氯鲁匝蛉猓N秋膘嘛,于是一起到了不遠(yuǎn)的靛廠路,那兒有家小飯館,賣單縣羊肉湯的。
滾燙的奶白色羊湯端上來(lái),緊接著是一筐噴香的山東燒餅,貌似很溫暖的樣子。這時(shí),兩位西北的同事,一位寧夏的,一位新疆的,卻異口同聲地跳起來(lái)說(shuō):“這羊肉怎么這么膻!”另一位河南籍同事則很無(wú)辜地問(wèn):“那個(gè),羊肉要是不膻怎么吃啊?”一頓飯,一個(gè)中原人和兩個(gè)西北人陷入了水深火熱的爭(zhēng)論。最后,他們把期待的臉轉(zhuǎn)向了我,希望我充當(dāng)這個(gè)“味道仲裁委員”的角色。我把羊湯喝完,微笑著說(shuō):“你們說(shuō)的都有道理……”結(jié)果,被雙方辯友同時(shí)鄙視了。
就像那句流行過(guò)的話,“每人心中都有一個(gè)……”,關(guān)于“最好的羊肉”,每個(gè)地方的人更有屬于自己的判斷——就說(shuō)那倆西北同事,也都各自鄙薄過(guò)對(duì)方的羊肉。寧夏的說(shuō):“新疆的羊肉還是做得粗,少這么一丁點(diǎn)鮮嫩的勁兒。”而新疆的說(shuō):“寧夏不行,全中國(guó)只有新疆的羊肉是最純凈的。”說(shuō)這話時(shí),我正和他在新疆出差,他問(wèn)我:“你不覺(jué)得這羊肉是甜的嗎?”我笑笑,差點(diǎn)兒說(shuō):“確實(shí),簡(jiǎn)直就像哈密瓜一樣……”
中國(guó)地方大,北到阿勒泰,南到三亞,都有吃羊肉的習(xí)慣。牛肉嫌粗,豬肉嫌濁,魚肉嫌淡,羊肉既細(xì)嫩又鮮美,粉羊肉者因此甚眾。北方吃綿羊,南方吃山羊,味道上有差異,再加上羊吃的食物不同,或青草,或麩料,同樣的品種,羊肉味道也有區(qū)別。我老家吃的羊,是頂風(fēng)膻三里地的那種,所以剛到北京,遇到不膻的口外羊,還真不怎么習(xí)慣。但是,這也練就了我對(duì)口外關(guān)內(nèi)的羊一視同仁的熱愛(ài),加上我的工作性質(zhì)是滿世界亂跑,所以,我能像灰太狼一樣非常愉快地面對(duì)喜羊羊美羊羊暖羊羊沸羊羊……不管是喀什烤羊腿、西安水盆羊肉、吳忠冷手抓、西寧開(kāi)鍋肉,還是遵義羊肉粉、海口東山羊、寧波白切羊肉、梅州羊肉邊爐,我都一概……哦天哪!我差點(diǎn)兒用“視同己出”這樣的詞兒,來(lái)表達(dá)對(duì)它們同樣的喜歡程度。
好友楊二是桂林人,是個(gè)京派涮羊肉愛(ài)好者。為此他做過(guò)一件事:有年春節(jié)回桂林,穿著羽絨衣的他去白塔寺打包了十幾斤羊肉片、若干袋調(diào)料和一箱小二鍋頭。而千里之外的桂林,飯店里早就支好了桌子,湯鍋已經(jīng)加了好幾遍水……這些食物經(jīng)過(guò)了若干小時(shí)的鐵路顛簸,出現(xiàn)在桂林充滿期待的親友面前的時(shí)候,羊肉片已經(jīng)蔫頭耷腦。穿著跨欄背心的各位急不可待地把肉丟進(jìn)了湯鍋。但不到十分鐘,就有喝著二鍋頭的兄弟說(shuō):“再加一份黃燜雞好不好?”顯然,他們覺(jué)得北京的羊肉太素,那天的羊肉也剩了大半。
老楊的失敗經(jīng)歷告訴我們,羊肉好比種子,到了一個(gè)地方,就應(yīng)該和當(dāng)?shù)氐娜嗣窠Y(jié)合起來(lái)生根開(kāi)花。就像桂林,也有非常好的羊肉料理方法:羊肉去毛,帶皮切塊,先用茶油旺火爆炒,再加沙姜、紫蘇、陳皮,文火干燜,出鍋前加進(jìn)青蒜、腐乳,用干鍋待客,蘸蒜蓉辣椒醬吃。這種方法燒制的羊肉濃香多汁,口感筋道,尤其冬天食用,超級(jí)下酒啊,幾杯三花酒落肚,我甚至能從中吃出些……甜味來(lái)。
美食家殳俏翻譯過(guò)一本書,叫《帶著鮭魚去旅行》。作者為了從斯德哥爾摩帶回一條三文魚,恨不得背上冰箱,遭老罪了!而在中國(guó)旅行,如果您恰好是個(gè)羊肉愛(ài)好者的話,只需要帶一副裝羊肉的胃和一根寬容的口條,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