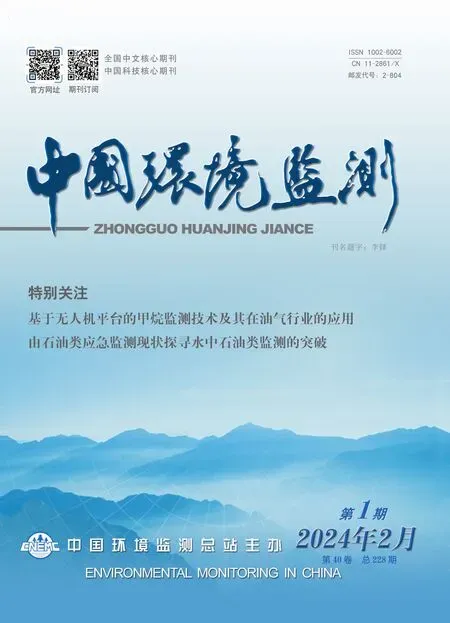雷州半島地下水水質空間分布特征及鐵、錳、pH超標的水文地球化學成因探析
王 亞,曹小芳,葉 珊,周永章,張 珂,陳炳輝,沈文杰,梁 浩,曹英杰,李增權
1.中山大學a.地球科學與工程學院;b.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廣東 廣州 510275
2.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珠海),廣東 珠海 519082
3.廣東省地質過程與礦產資源探查重點實驗室,廣東 廣州 510275
4.廣東省生態環境監測中心,廣東 廣州 510380
5.廣東省湛江生態環境監測中心站,廣東 湛江 524000
地下水總量約占地球總水量的0.61%,是河流、湖泊等地表水總量的將近70倍[1],因此,地下水是地球淡水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地下水在我國供水體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據統計,2021年,地下水供水量約占我國總供水量的14.5%[2]。我國北方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供水水源中,地下水占90%左右[3]。盡管南方地區降雨量大,地表水資源更為豐富,但是仍有一些城市,如粵西濱海城市湛江,因地表水資源有限,將地下水作為重要的飲用水源或后備飲用水源。
與地表水相比,地下水在含水層與隔水層等的調節作用下,時空分布相對更加均勻,這為人類獲取和利用水資源提供了諸多方便。此外,由于地層的過濾作用,地下水水質相對不容易受到地表污染物的影響,常常能保持良好的狀態,從而使地下水被作為重要的飲用水源[4-6]。盡管具有相對優勢,我國地下水資源利用與保護仍充滿復雜性和挑戰性。以湛江為例,研究人員在多年調查監測過程中發現,該區域地下水存在較突出的pH、鐵(Fe)和錳(Mn)等指標超標的情況。據文獻記載,該區域地下水pH有時可低至4以下[7],酸化顯著,而Fe和Mn含量相對于國家飲用水標準限值而言,可高至幾十倍甚至數百倍[8]。雷州半島地區在中、晚更新世經歷了多次間歇性的火山噴發,形成了較為復雜的水文地質條件,使得對該地區地下水水質超標問題的科學認識和有效管控成為難題。
當前所處的“十四五”時期是我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關鍵時期。地下水污染管控與治理是我國國家戰略規劃與行動方案的重要內容,也是各省級及地市級生態環境部門重點關注的核心工作[9-10]。為初步評估湛江地下水pH、Fe和Mn顯著超標的原因,本研究以2009—2017年在湛江市主城區及其周邊地區開展的地下水基礎環境狀況調查項目獲得的數據資料為基礎,分析該區域地下水環境質量時空特征,并結合該區域地質地層與水文地質條件,揭示出可能誘發水質超標的地球化學因素,以期為明晰湛江市區多年來一直面臨的地下水Fe、Mn和pH超標問題指明方向,并為對該問題的有效管控提供科學指導與依據。湛江作為以地下水為重要飲用水源或后備飲用水源的濱海城市,長期存在地下水Fe、Mn超標問題,因此,在該區域開展相關研究不僅對于解決該地區地下水水質問題具有重要意義,也可為我國其他存在類似地下水水質問題的城市和地區提供借鑒。
1 研究區域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區地質與水文地質概況
雷州半島地處我國大陸最南端,介于南海和北部灣之間,是我國三大半島之一。該地區屬于典型的亞熱帶、熱帶季風氣候,多年平均氣溫在23 ℃左右,年平均降雨量為1 300~1 700 mm,降水時空分布表現為由東向西漸減且多集中在5—9月[11]。由于蒸發量較大,當地容易發生干旱,導致區內地表水資源相對短缺。當地地表徑流大多是源近流短的小溪流,呈樹枝狀,由中部向東、南、西三面分流入海。該區域地形地貌較復雜,總體地勢呈南北高、中間低,囊括了火山地形、侵蝕堆積地形、侵蝕剝蝕地形和海成地形等[12]。
雷州半島屬雷瓊東西向喜馬拉雅沉降帶的中段和北段,經歷了加里東期、海西-印支期、燕山期和喜馬拉雅期4個構造階段[12]。當地堆積的新生代地層自下而上依次為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基底為白堊系、元古系[13]。在巖性上,由于地殼運動速度不均勻,北部沉降幅度較南部大,北部沉積了較厚的粗碎屑,富水性強,而南部則以厚度較薄的黏土沉積物為主,富水性弱[14]。在中、晚更新世,區內經歷多次間歇性火山噴發,使得沉積的松散砂和泥質巖互層中常常可見覆蓋于其上或夾于其間的基性火山巖[14]。由此,松散巖類和火山巖類的孔隙發育形成了含水層。區內中南部地下水以火山巖孔洞溶隙水和松散巖類孔隙水為主,北部則以呈條狀或零星狀分布的基巖裂隙溶隙水和碳酸鹽巖類溶隙溶洞水為主。依據陳紅宏[15]對雷州半島水文地質條件的分析結果,根據含水層埋藏深度與隔水層分布,雷州半島地區松散巖類孔隙水自上而下大體可分為4個含水層組,包括第一含水層(即潛水含水層,為淺層水)、第二含水層(即第一承壓含水層,為中層水)、第三含水層(即第二承壓含水層,為深層水)和第四含水層(即第三承壓含水層,為超深層水)。第一含水層的埋深小于30 m,在研究區的西北部主要為北海組砂礫石層,在東北部、中部和南部部分地區為湛江組砂層,在部分海岸帶和島嶼地區的砂堤砂地中還分布有細中砂層。第二含水層廣泛分布于整個雷州半島地區,與上部潛水含水層之間往往有2~25 m厚的黏性土相隔,與下部深層承壓水之間往往有3~70 m厚的粉砂質黏土相隔,埋深在30~200 m之間。第二含水層在研究區北部主要由湛江組組成,在南部由湛江組下部和下洋組上段組成。含水層巖性自北向南由粗變細,北部以粗砂、礫石為主,南部由含礫粗砂、中砂、細砂組成。該層含水豐富,是本區主要的含水層,也是進行地下水開采的主要層位。第三含水層的埋深在200~500 m之間,幾乎分布于全區,其厚度在西北角由于基巖隆起而變薄。第三含水層在研究區北部主要由下洋組上段組成,在南部由下洋組下段組成,含水層巖性主要為粗、中、細砂巖。由于第三含水層埋深大、壓密性較好,其富水性和補給條件均比中層略差。第四含水層的埋藏深度超過500 m,主要為中新世潿洲組松散至半固結孔隙承壓水。
1.2 研究區地下水開發利用概況
雷州半島地區的地下水開發利用程度在廣東省三大平原區最高[16]。當地淺層地下水開采條件較好,但單井水量不大,因而一直未作為集中供水水源,主要用作小型分散式農業灌溉水源。中、深層承壓含水層是雷州半島的主要含水層,也是目前進行地下水開采的主要層位。湛江市區是雷州半島地下水開采量最大的地區,重點水源地為赤坎、霞山、坡頭、東海島、太平、鋪仔、南山島、硇洲島等8處[16]。在1995年以前,該區域的地下水開采量逐年增大,中心區地下水水位不斷下降;1996年后,隨著湛江市加強地下水開采管理,地下水開采量有所降低,局部中、深層承壓水降落漏斗中心區水位也開始出現回升;自2000年起,漏斗中心區水位再次逐年下降,同時出現了地面沉降現象,主要發生在位于區域地下水降落漏斗中心的霞山和赤坎兩地[15]。雷州半島地下水監測站網始建于20世紀60年代,井位多集中于湛江市區。至“十三五”收官,湛江市共設置了15個國家級地下水環境質量監測點,用于開展地下水環境質量長期監測。
1.3 數據來源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湛江市原環境保護局在2013—2017年間開展的湛江市地下水基礎環境狀況調查項目。相關資料及圖集[17-19]所含數據對應的年份為2009—2017年,共計9年。該調查項目在湛江市范圍內開展了水文地質鉆探、水文地質試驗和地下水采樣測試等工作,鉆探井位數為104口,含水層取樣深度為3~92 m,共計取得地下水樣品102組,井點分布如圖1所示。

圖1 雷州半島地下水監測點位分布
各井點的取樣層位如表1所示。地下水樣品的采集、保存及運輸過程嚴格按照《地下水環境監測技術規范》(HJ/T 164—2004)[20]的要求執行。該項目共分析測試了包括主要陰陽離子、多種重金屬、硬度等在內的40余項水質物理與化學指標,測試方法和質量控制措施均按照國家和行業相關標準的要求執行。其中,鐵離子(Fe3+)和總Fe采用硫氰酸鹽分光光度法(DZ/T 0064.24—1993)進行測定,亞鐵離子(Fe2+)采用二氮雜菲分光光度法(DZ/T 0064.23—1993)進行測定,Mn采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法(DZ/T 0064.22—1993)進行測定,pH利用數據型筆式測量儀(意大利哈納,HI9125)進行測定。

表1 各監測點采樣層位統計結果
為對超標指標進行評估,本研究按照我國《地下水質量標準》(GB/T 14848—2017),對超標顯著的Fe、Mn和pH開展了單指標評價和綜合評價。具體的評價方法在相關文獻[21]中已有詳細描述,此處不再贅述。在進行多參數統計分析時,主要用SPSS統計軟件[22]分析了地下水物理、化學參數之間的皮爾遜相關系數,為解析超標成因奠定基礎。
2 結果與討論
2.1 區域地下水水質評價結果及水質時空分布特征
在所有開展測試分析的地下水指標中,以pH、Fe(本研究分為Fe2+和Fe3+)和Mn的超標問題最為突出。這些指標超標的問題由來已久。從湛江地下水相關文獻可知,早在1993年就已有針對這方面問題的記載[23]。為清晰認識研究區地下水超標問題,本研究參照GB/T 14848—2017,對具有地下水質量分類(Ⅰ~Ⅴ類)賦值的3個水質指標(pH、Fe、Mn)進行水質評價。水質評價方法包括單指標評價法和綜合評價法。在單指標評價中,按指標值所在的限值范圍確定地下水質量類別,當與指標限值相同時,從優不從劣,評價結果見表2。在綜合評價中,按單指標評價結果最差的類別確定地下水質量類別。所有水質監測點的評價結果如下:Ⅰ類點1個,Ⅱ類點0個,Ⅲ類點1個,Ⅳ類點53個,Ⅴ類點47個。當監測結果劣于地下水Ⅲ類限值(該限值與最新的國家飲用水標準限值[24]一致)時,評價為超標。從以上結果可知,研究區地下水水質以Ⅳ~Ⅴ類為主,總體較差,具體見表2。

表2 雷州半島地下水水質單指標評價結果
為分析Fe、Mn、pH單指標評價結果及綜合評價結果在空間上的分布特征,本研究按指標分類結果,把不同類型的點在空間上做投影,結果如圖2所示。從空間分布來看,Fe濃度Ⅳ類水井點廣泛分布在研究區的各個部分,表明地下水Fe超標在空間上對于整個研究區來說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Ⅴ類水井點主要分布在湛江市主城區(霞山區和赤坎區)和吳川市;不超標井點絕大部分位于雷州市[圖2(a)]。Mn濃度Ⅳ類水和不超標井點在整個區域內的分布都比較均勻,且沒有明顯的側重區域;Ⅴ類水井點極少,集中分布于霞山區和雷州市[圖2(b)]。pH超標和未超標井點表現為各自集群分布,湛江市區(霞山區和麻章區)和雷州市都出現了pH顯著超標的情況[圖2(c)]。總體而言,研究區Ⅳ~Ⅴ類地下水的存在非常普遍,整體水質較差,Ⅴ類水主要分布在雷州半島的中部、東部和北部[圖2(d)]。

圖2 地下水樣品Fe、Mn、pH單指標評價結果及綜合評價結果的分級空間分布
依據本研究所掌握的地下水資料,監測井的建設年份集中在2013年、2015年、2017年,數量分別為13、57、27口。針對這部分監測井,初步開展了時間序列對比分析,結果見圖3。初步對比結果顯示,無論是Fe3+、Fe2+、Mn還是pH,2015年和2017年平均值都較2013年有顯著改善。考慮到不同年份的監測井的空間位置不同,所采集樣品的含水層性質也不盡相同,無法直接推導得出研究區地下水水質隨時間的推移有所改善的結論。本研究后續將結合含水層性質分析結果,對水質在時間上呈現上述變化趨勢的原因作進一步討論。

圖3 研究區典型年份地下水Fe、Mn濃度和pH對比
2.2 區域地下水水質超標概況
該區域地下水樣品pH及Fe3+、Fe2+、Mn濃度與國家飲用水標準限值[24]的對比如圖4所示。從圖4可見,研究區絕大部分地下水樣品都存在較顯著的Fe、Mn和pH超標問題。在調查所涵蓋的102組地下水樣品中,Fe3+、Fe2+、Mn、pH的超標率分別為75%、43%、65%、54%。與Fe、Mn濃度顯著高于飲用水標準限值不同,研究區樣品pH超標主要表現為低于飲用水標準最低限值(6.5),而高于飲用水標準上限(8.5)的情況則幾乎沒有。

圖4 地下水樣品Fe、Mn濃度及pH與國家飲用水標準限值的對比
2.3 水質超標與周邊污染源的關聯性分析
地下水水質超標與周邊污染源之間的聯系值得重視。根據湛江市“雙源”(集中式地下水型飲用水源和地下水污染源)調查結果,湛江市區及周邊城鎮的典型污染源包括3個垃圾填埋場、5個工業園和4個加油站,其空間分布如圖2所示。從圖2可以看出,研究區地下水水質普遍較差,遠離污染源的很多水井仍會出現較為顯著的水質超標現象[圖2(d)];在部分污染源附近,水質較好與較差水井并存[圖2(a)和圖2(b)];部分垃圾填埋場、加油站、工業園所在區域的地下水pH并未超標[圖2(c)];為數不多的幾個Fe含量未超標的水井甚至與加油站相鄰[圖2(a)];4個工業園和1個垃圾填埋場附近的地下水的Mn含量均未超標[圖2(a)]。因此,主要污染源與地下水Fe、Mn、pH超標問題不存在必然的聯系。
2.4 水質超標與含水層性質的關聯性分析
氧化還原條件是決定含水層中的地球化學過程的關鍵因素[25],而含水層氧化還原條件又與其埋深密切相關[26]。結合本研究獲得的含水層資料與研究區水文地質特點,按埋深將含水層分為3類,分別為深度小于等于30 m的淺層含水層、深度介于30~200 m之間的中層含水層、同一口井中同時混入了淺層地下水和中層地下水的混合含水層。分析3類含水層中Fe3+、Fe2+、Mn以及pH的分布特征,以解析地下水超標問題與含水層性質之間的關聯性,分析結果如圖5所示。

圖5 淺層含水層、中層含水層和混合含水層的Fe2+、Fe3+、Mn濃度及pH
在所有開展檢測的地下水樣品中,Fe2+的濃度范圍為0.01~149.39 mg/L,平均濃度為3.80 mg/L;Fe3+的濃度范圍為0.00~24.35 mg/L,平均濃度為1.64 mg/L。分層來看,Fe2+濃度在淺層為0.03~5.90 mg/L,平均濃度為0.84 mg/L;在中層為0.01~149.39 mg/L,平均濃度為9.28 mg/L;在混合層為0.02~17.86 mg/L,平均濃度為1.62 mg/L。上述結果表明,Fe2+超標問題在中層最突出,其次是在混合層,在淺層則相對弱很多。其中,Fe2+最高濃度出現在中層,見圖5(b)。Fe3+的濃度分布情況與Fe2+有所不同,其在淺層為0.11~5.23 mg/L,平均濃度為1.18 mg/L;在中層為0.26~24.35 mg/L,平均濃度為2.76 mg/L;在混合層為0.00~8.14 mg/L,平均濃度為0.95 mg/L。這表明Fe3+超標問題在各個深度的含水層中均比較顯著。此外,Fe3+最高濃度同樣出現在中層,見圖5(e)。總體而言,Fe超標問題在中層和混合層地下水中比在淺層地下水中更為顯著,Fe2+超標問題相對于Fe3+更為突出。
Mn的濃度分布如圖5(g)~圖5(i)所示。Mn的濃度范圍在淺層為0.03~3.29 mg/L,平均濃度為0.42 mg/L;在中層為0.01~5.06 mg/L,平均濃度為0.48 mg/L;在混合層為0.01~2.26 mg/L,平均濃度為0.26 mg/L。其中,檢測到的最高濃度出現在中層,見圖5(h)。總體而言,Mn超標問題在各含水層中均存在,但超標倍數相對于Fe較低。
各含水層地下水pH的分布情況如圖5(j)~圖5(l)所示。淺層地下水的pH范圍為5.21~8.04,平均值為6.55;中層地下水的pH范圍為3.60~8.14,平均值為6.60;混合層地下水的pH范圍為3.85~8.19,平均值為6.19。這表明混合層地下水的pH過低問題最為顯著,見圖5(l)。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在淺層地下水中,僅有一個樣品的pH低于5.5,其余樣品的pH均在6.5附近,因而對于淺層地下水來說,pH過低可能是偶發性的;在混合層和中層地下水中,pH過低的現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混合層,有約10個點位的pH低于4,見圖5(l)。
由上述對比可知,Fe超標的顯著程度排序為中層含水層>混合含水層>淺層含水層,Mn超標的顯著程度排序為中層含水層>淺層含水層>混合含水層,pH超標的顯著程度排序為混合含水層>淺層含水層>中層含水層。因此,Fe和Mn兩個指標的超標問題在中層含水層最為突出,而pH過低的問題則在混合含水層最顯著。根據含水層巖性,進一步分析了超標與不超標站點地下水的水化學類型,結果如圖6所示。分析結果顯示,Fe2+、Fe3+、Mn、pH超標和未超標地下水的水化學類型無明顯區別,并且不同巖性含水層地下水的水化學類型也基本相似,多為Na-Ca-Mg-HCO3-Cl型,見圖6。

圖6 Fe2+、Fe3+、Mn、pH超標和不超標地下水樣品的水化學類型對比
由雷州半島地質與水文地質背景可知,該區域的地殼運動、構造活動以及多期次火山噴發活動使得其含水層的結構十分復雜,且含水層巖性具有較大的空間變異性[27]。含水層的巖性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水-巖交互作用的類型,對地下水水質具有重要影響[28]。因此,探討含水層巖性與Fe、Mn、pH之間的關系,是解析這些指標超標機制的重要基礎。根據收集到的地下水資料,可將含水層從巖性上粗分為3類,即松散巖類含水層、基巖裂隙溶隙含水層、松散巖類與基巖裂隙溶隙交互含水層。3種含水層地下水的Fe3+、Fe2+、Mn以及pH情況如圖7所示。

圖7 松散巖類含水層、基巖裂隙溶隙含水層和交互含水層Fe2+、Fe3+、Mn濃度以及pH
從結果可見,3類不同巖性的含水層均存在Fe、Mn和pH超標問題,但超標程度各異。松散巖類含水層的超標問題最為顯著,其中:Fe2+含量最高值接近150 mg/L,約是國家飲用水標準限值(0.3 mg/L)的500倍,見圖7(a);Fe3+超標問題也十分突出,最高濃度值為24 mg/L;大部分樣品的pH都低于6.5,不少井點甚至低于4。基巖裂隙溶隙含水層Fe超標問題并不顯著,但是Fe3+的超標情況要比Fe2+突出[圖7(b)和圖7(e)],說明該含水層可能受氧化環境影響較大。基巖裂隙溶隙含水層幾乎不存在Mn超標問題,僅有一口井的Mn濃度達到了飲用水標準限值(0.1 mg/L),見圖7(h)。此外,該含水層pH均在正常范圍內(6.5~8.5),見圖7(k)。交互含水層超標情況同樣不如松散巖類含水層突出,其中Fe2+濃度均在1.5 mg/L以下,而Fe3+濃度在12 mg/L以下,見圖7(c)和圖7(f)。相對較高的Fe3+濃度表明交互含水層有較好的氧化條件。氧化條件的形成可能與交互含水層特殊的結構相關,即火山噴發形式的玄武巖貫穿松散沉積砂層,使巖石與砂層的接觸界面成為近地表與下部含水層的直接溝通通道,有利于地表氧化性物質的進入。交互含水層存在pH低于6.5的現象,但此類井點的占比并不大,且最低pH仍高于6,見圖7(l)。
從上述分析可見,Fe、Mn超標問題在松散巖類含水層中更為突出,pH顯著酸化也出現在這一含水層。通過對比超標和不超標地下水樣品所處的松散沉積含水層層位可看出,超標和不超標點位的鉆孔深度都在40~60 m之間,但不超標點位的巖性包括細砂和中砂,而超標點位的巖性僅為中砂,初步表明超標問題與地質地層相關。湛江市松散巖類沉積地層由老至新主要包括潿洲組、湛江組和北海組等[29]。據文獻描述,湛江組和北海組地層中均存在鐵錳礦物[13,30]。湛江組巖性以黏土層、亞黏土層、雜色砂層、砂礫層及礫石層為主,其中夾鐵質膠結層主要分布在湛江市平嶺地表[31]。北海組平行不整合于湛江組之上,底部以風化鐵質薄層為標志,下部為黃色至黃褐色含礫砂質黏土,中上部為黃色砂質黏土[32],主要分布于雷州半島北部[31]。潿洲組是一層淺綠灰色砂質泥巖,局部夾細砂巖,部分地區含有黃鐵礦[31]。因此,在今后的進一步研究中,應注重對這3個地層開展地球化學分析,以解析超標問題的地球化學形成機制。
綜上,pH、Fe、Mn超標主要與雷州半島的地層特性相關,與該區域主要污染源沒有明顯關聯。此外,從時間上看,根據黃宇萍等[33]的研究,該區域地下水pH、Fe、Mn超標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已有記載,說明當地地下水超標問題在該區域大規模城市化和工業化之前就已經存在。因此,該超標問題與自然地質背景存在較大關聯,與人為排污無明顯關系。加強對雷州半島區域含水層自然背景條件的關注,進一步解析超標物質釋放機制,是科學認識和管控該區域水質超標問題的關鍵。
2.5 不同含水層水質的多參數相關關系分析
由于污染源與超標因子之間的關系仍需進一步探討,本節主要針對含水層的地球化學性質進行綜合分析。Fe、Mn、pH在不同深度含水層的超標程度顯著不同,表明這些指標與各含水層的氧化還原條件、地層巖性等水文地球化學特征密切相關。為進一步解析含水層內部的水文地球化學過程,本研究按淺層、中層、混合層3類含水層,對地下水樣品的主要陰陽離子、各形態無機氮、多種重金屬等24項物理和化學指標進行了多變量皮爾遜相關關系分析,分析結果見圖8~圖10。

圖8 雷州半島淺層地下水水質多參數皮爾遜相關關系分析結果



圖9 雷州半島中層地下水水質多參數皮爾遜相關關系分析結果


圖10 雷州半島混合層地下水水質多參數皮爾遜相關關系分析結果

2.6 地下水水質隨時間變化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造成湛江地下水Fe、Mn和pH超標的關鍵層位是位于中層的松散沉積含水層。對2.1節中的2013年、2015年和2017年地下水樣品進行層位統計分析,結果見表3。由表3可知,中層地下水樣品在2013年樣品中的占比近70%,而在2015年和2017年樣品中的占比均不超過四分之一。如前文所述,中層含水層是Fe、Mn超標最為突出的含水層,其樣品占比高必然導致平均濃度偏高。這也就說明,此3年分析結果的差異主要是由取樣深度的差異引起的,其對比結果不能反映水質隨時間的變化趨勢。因此,如要獲得雷州半島地下水水質在時間上的變化信息,需要在固定含水層開展長期監測。

表3 湛江市2013年、2015年及2017年不同深度地下水樣品的占比統計結果
3 主要結論與建議
通過對雷州半島2009—2017年102個監測點位地下水環境測試數據與含水層取水深度、巖性、地質地層等多方面因素進行關聯分析,初步獲得了以下幾點主要認知:
1)在雷州半島地區地下水樣品中,Fe3+、Fe2+、Mn、pH的超標率分別為75%、43%、65%、54%,超標率高。同時,各點位地下水質量評價結果顯示,Ⅰ類點1個,Ⅱ類點0個,Ⅲ類點1個,Ⅳ類點53個,Ⅴ類點47個。總體而言,超標情況需引起重視,Ⅳ~Ⅴ類水的存在非常普遍,其中最差的Ⅴ類水主要分布在雷州半島的中部、東部和北部。建議今后進一步健全雷州半島地下水監測與綜合評價分析體系,加強對降雨、地表水、土壤水、人工抽水等自然或人為因素與地下水超標問題的關聯分析,以準確理解造成地下水水質超標的原因,從而為地下水型飲用水源水質超標問題管控提供科學依據。
2)從含水層埋深來看,Fe和Mn超標倍數較大的地下水樣品集中來源于中層含水層,pH超標率較大的地下水樣品集中來源于混合含水層。結合含水層巖性來看,松散沉積含水層的Fe、Mn和pH超標問題最為突出,而基巖裂隙溶隙含水層以及交互含水層的超標問題則相對較輕。在中層含水層,Fe和Mn具有同源性,且表現出非常一致的水文地球化學行為特征。這種特征在混合含水層出現弱化,推測可能是受到了淺層地下水的影響。建議今后在建設地下水取水井時,應避開造成水質超標的關鍵層位,同時做好隔水和止水工作,保護取水層不受超標層位地下水的影響。
3)位于中層的松散沉積含水層是研究雷州半島地區Fe、Mn和pH超標機理的關鍵層位,應予以重點關注,進一步加強研究。湛江組和北海組兩個相鄰的地層均含有較為豐富的鐵錳質礦物或結核,建議結合湛江地區松散沉積地層的特點,加強對這兩個地層的地球化學分析,并有針對性地完善地下水水質監測網,以更好地解析造成水質超標的地球化學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