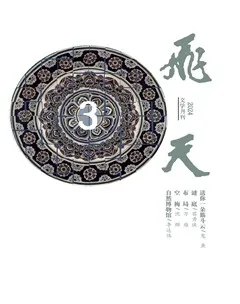月光曲(外二題)
馮淵
我穿著深咖啡色西服,打著紅色領帶,沿著田埂,走向浮在稻田上方的一所小學。
我要去上一節語文課。師范最后一年,我在這所小學實習,帶教老師說這節課該講《月光曲》了。我提前讀過一遍課文,這篇課文我小時候沒學過,但我覺得應該能上好。
一群十二三歲的孩子,看著新來的、臨時的老師,充滿了好奇。
我用普通話充滿感情地朗誦課文,眼前出現了大海、月光、盲女孩、皮鞋匠……
抑揚頓挫的朗誦,溫情脈脈的分析,一些我平時不善于言說的語詞、句子,也隨著課文描寫的情境流瀉出來,在這間四壁透風的教室里沉浮。那些陌生的語言、聲音,漫過學生身邊,他們因陌生而好奇,又因驚喜而雀躍。大家不熟悉,同學們都羞于流露出強烈的情感,無論是對這些語詞的歡喜,還是對普通話感到的新鮮,都被限制在小小的空間里,積蓄著,連空氣都稠了,密實了。
水稻田邊的池塘里,涼風掀起厚實的菱葉,露出鮮紅的菱角,蹲在水邊就能摘到這些果實,小心掰開菱角,就會看到潔白光潤的菱角肉。那是大地上能尋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甜蜜的東西,脆、嫩,瞬間消失于齒牙。
這些聲音,這個故事,這節課,很快都會隨著下課鈴聲消失。但現在正上著課,老師和學生都在這虛構的、帶著甜味的故事里沉醉。
不少孩子兩眸炯炯,盯著我手中的書,看聲音怎么從我的身體里發出,在下午光線暗淡的教室里回蕩。一時間,我覺得自己就是貝多芬,正在彈奏一支曲子,那個可愛的盲妹妹,那個樸實勤勞的哥哥,就在我們身邊。
這是農歷十月,小陽春的尾巴。晚稻的穗子低垂下去,紅芋圓滾滾,要鼓出地面。農人在做收割、開挖前的準備。
男人在家磨鐮刀、牙鋤。女人穿著膠底回力鞋去拔稗子,稻田里水已經干了,但還是潮潤的。姑娘在紅芋地里,將紅芋秧翻到一邊,有的直接用刀割掉,露出光光的凸起的土埂,那下面埋伏著紅芋的千軍萬馬。到時要用牙鋤開挖,尖銳鋒利的牙鋤直直劃過,紅芋哪經得起,不小心劈裂的紅芋,淡黃的心無遮無攔裸露在風中。還沒出土就受到這樣的傷害,這是它們的宿命。
教室里,學生眼前是大海、月色,是異國他鄉,是幾百年前的“故”事,再窮的人家也有鋼琴,也有對音樂的憧憬,和被音樂打動的幸福。
教室外,稻田等待收割,紅芋等待開挖,淡青色的炊煙在村子里飄蕩。人們要準備足夠的糧食,度過即將降臨的寒冷冬天和來年的春荒。除了上學的孩子,所有的人都在為這些事操心。老人也不閑著,搓草繩、打草鞋,掃干凈場院,地上總有落葉,落葉一片都不會浪費,送到灶間,一堆落葉能煮熟一吊罐豬食。
下課鈴終于響了,就像脆生生的菱角終于吃完。孩子們有一點依戀,但他們很快醒過來,那都是外國的事,不存在的故事。放學了,回家了,他們要回到那個點亮燈火的、充滿稻草和豬糞雞糞氣味的院落,還算寬敞但永遠不會有鋼琴的家。也沒有幾本書,但月光一樣會從窗戶里照進來,陪伴他們入睡。會不會有孩子睡前想起《月光曲》的故事呢?
我隨著孩子們走出教室,這節課永遠結束了,不會有第二節了。我明天就會離開村子,回到我讀書的城市。
那會兒,我隨著孩子們回我的村莊,在村小學之外的一個高地上,比他們的家更遠一些。
村口喇叭在播放晚間新聞。胡開明率老年人長跑隊一行10人,赴美國圣迭戈市參加世界老年人馬拉松賽。胡開明是誰?圣迭戈在哪里?沒有人關心這些,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啊。那些事,那些人,一定很了不起,不然,喇叭里怎么會播報?那些陌生的城市發生了多少事,我一無所知,孩子們更是一無所知。村子里的人知道的事,我也知之不多。我突然陷入一種恐慌,這多少沖淡了剛才講述貝多芬故事時產生的一丁點優越感。我回到孩子們的隊伍里。
我們走在田埂上,說著閑話,用方言。過了兩三個水塘,孩子們散到各自的村落,黑漆門樓的,往東去;周家嘴的,往北去。我要往南走,穿過前面叫堰邊的村子。
我身邊還剩下兩三個孩子。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穿著黑燈芯絨上衣,眉清目秀。我隨口問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檀滿鳳。
檀滿鳳?你是不是有個姐姐叫檀曉鳳?
老師怎么知道我姐姐的名字?
我有個同學,是堰邊的,就叫這個名字。你是堰邊的,你是老小對不對?
老師和我姐姐是同學?檀滿鳳仰頭看著我,不能相信。
是五年級的同學。
我現在也五年級了。檀滿鳳說。
我說起五年級仿佛是幾十年前的舊事,其實不過五六年時間。
我是從另一所村小轉學過來的,和檀曉鳳同學一年,沒說過一句話。那都是小時候的事了,現在我長大了。我無端生出一種親切感來,仿佛萬里歸來,與所有陌生的故鄉人都成了親人。
我突然想跟著檀滿鳳一起去她家,看看她的姐姐、我的老同學檀曉鳳。剛才在課堂上分享的那些陌生人突然走到一起的親切、心靈在一瞬間變得親密的故事感染了自己。過去的隔膜,隨著時間的流逝自動消解了。
檀滿鳳很高興,她將我視作尊貴的客人。老師,到我家去吧,我姐姐肯定會很開心的,你們這么多年沒見過面。
女人將稻田中的稗子拔下來扔在田埂上。我們踩著那些已經結籽的稗子,毫不吝惜。它結的籽太小了,碾米時會混在稻子里,煮成飯吃起來像砂礫,所以,人們要提前從稻田里祛除它。稗子和稻子都是禾本科,命運如此不同。
我四下里看,希望在曠野里看到檀曉鳳。
檀曉鳳的長相我已經記不太清,我是班里年齡最小的,她今年應該十七八歲了吧。十一二歲到十七八歲的女孩,變化太大了。我來不及思考為何要去見她,只是憑著上完課后難以平復的心情,想去打開那扇月光鋪滿的房子。貝多芬在盲女和她的哥哥不知不覺的時候,彈奏一曲,翩然而去,留下兄妹倆在月光里發呆。這太令人神往了。我紅色的領帶在晚風里飄起來。
這些年我讀過很多詩歌、散文,接觸到許多鋒利的語言,尖銳的詩句,這座江南小城是李白寫“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的地方,站在古城墻的黃昏里,我手中漫卷著盧梭、歌德、托馬斯·曼,滿腦子都是結結實實的不著邊際的想象。我只想去見一個陌生而又熟悉的人。她一定跟《月光曲》里的那個盲女一樣善良,她一定也有許多話要跟我說,她看過的電影,遇到的新鮮的人和事,她有飄逸的長發,明亮的眸子,清潔的面龐,整齊的衣飾。
田野里都是我不熟悉的人,天光暗了下來,沒有發現檀曉鳳的身影。
檀滿鳳嘰嘰喳喳跟我說話,她很快和我熟絡起來,她想知道我讀的書,她跟我說她的老師上課的情景。如果不是剛才這節課,我們走在田野上,就是了無關系的陌生人。人和人的相遇是多么奇特呀,很短、很短的時間,就像認識了很久、很久。我想認識許多可愛的人,我想和他們分享自己的歡欣。一些歡喜、一些暮色里淡淡的憂愁籠罩著我。中間隔著五六年光景,突然見面,會說什么呢?而且我這樣突然的造訪,短短的時間,壓縮了太多的話語和心情。我能說什么呢?我會像在課堂上講話那樣自如、自在嗎?我想象著和檀曉鳳多年之后重逢的驚喜。她會睜大了眼睛盯著我看,跟我說許多話嗎?
我的心里充滿了千言萬語,言說的沖動壓倒了一切,風有點冷了,身體毫無知覺。
穿過一塊水塘,走過一片小小的竹林。檀滿鳳跳著說,這就是我家啦。
四間磚瓦房寬敞挺拔,比貝多芬看到的茅屋好多了。門口堆著割下來的紅芋秧,葵花稈支架上橫著一根竹竿,我知道那是晾衣服的,天色晚了,衣服收進家里,只剩下空蕩蕩的竹竿。
一個女孩子,手臂上搭著晾曬好的衣服正往屋里走,留給我的是一個黑色的背影。女孩子的衣服有些皺縮,褲腿上還有泥點,她穿的黃色回力鞋。鞋幫上都是泥,黑色的、黃色的泥。
檀滿鳳大聲說,姐,你看,誰來了?
女孩子轉過身來,沒有看妹妹,甚至也沒有看我。一臉漠然。
我趕緊說,檀曉鳳,我是永紅,你的同學呀。
我不認識你。她將衣服攏了攏,繼續往房里走。
我跟過去,說,我是你清華小學五年級同學馮永紅。
檀曉鳳慢慢回過頭來,聲音不大,但很清晰很堅定,我不認識你。
領帶將剛剛長出的青春痘映紅了。我趕緊跟檀滿鳳說,我走了,你回家寫作業吧。
那是1984年的11月29日,星期四,閏十月初七。村子里還沒有通電,家家戶戶都還在用煤油燈,一到夜晚,四野都沉浸在一片黑暗中。我得趕在天完全黑下來之前,步行回到我那個高地上的村子里。
初七的新月升上來,淡淡的月光灑在一大片廣袤的稻田上空。十六歲的我,繼續走在田埂上。一條不知從哪里跑來的小黑狗,突然沖過來,碰了碰我的腳跟,然后嗖地一聲,像箭一樣,消失在曠野里。
有風過耳
千畝牡丹園,姚黃魏紫,風從低處吹來,萬朵鮮艷的花朵,幾十萬片花瓣在風中微微顫抖,這是雄風。
河灘,狗牙根草,草間上有亮閃閃的水珠,風從高天吹來,輕輕掠過低伏在地上的草葉,這是雌風。
風在曠野里,橫掃千軍,葉落花飛,那是風的事。
人在曠野里,風吹過面頰,才感受到風真的來了。
流汗時,風從兩腋鉆進來,從皮膚表面輕輕劃過,冰涼的蛇,調皮地四處游走。
結冰時,風在鴨絨羊毛和棉花包裹的身體外,左沖右突,找不到入口,呼嘯而去。
我從未看到過風,但我看到墻上爬山虎的葉子一片一片掙扎著,最后飄在我的腳邊。
我聽見了風,在竹葉和桂花之間,送來瀟瀟的聲響,以及甜膩的香味。
在封閉的書房里,我有四壁的書。書櫥、書,散發著一股說不清的酸味,是紙張和陳年木頭的氣味。我走出來,在院子里,想握一下風的手。
我走到田野里,風,帶著稻花的香味。正是金秋時節。
慢慢走在田埂上,很難感覺到風的存在。只有余威尚在的陽光,直晃眼。
在車上就不一樣。從車窗里伸出手,風就來了,貼近你,貼緊你,在手掌里沖撞、摩挲、激蕩,你會感覺到空虛的掌中有一個飽滿的實體,圓潤、充實、彈性十足。
第一次在掌心握住風是中考那年。一輛解放牌大卡車開進校園,要將我們接到十公里外更大的鎮上去考試。
男生女生簇擁在一起。爬到車廂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先上的,要拉后來的一把。我們三年同學,男生和女生從未有一句話交流。這時,個頭大的男生,要伸出手,拉住女生的手,一把將女生拽上來。
沒有人起哄,女生也沒有臉紅。我那時個頭小,站在敞篷車廂的前排,手抓住護欄,目不斜視。等車子開動時,風就來了。速度讓風聚集起力量來,撲在臉上,是楊柳梢拂面,不,風比樹梢溫柔多了;像雪花落在臉上,不,雪花砭人肌骨,此時的風是柔和的,這是七月中旬一個陰雨天的黃昏,風還有一些涼意。
我聽任風吹著我的臉、眼睛、頭發。耳朵也被風吹得更貼近腦袋了,呼呼呼的風聲,三過耳門而不入,它很快吹到我的后腦勺了,然后,落到后排同學的身上去了。
風將我的胸膛都吹空了,我像一只廢棄的櫥柜,四壁空空,在風里隨著解放牌大卡車奔跑。
還有一點微弱的雨絲,一點涼潤的南風,我在風里微笑著,風就從我的唇齒之間吹到我身體里面去了。
我正大口呼吸著風的時候,突然發現身邊站著的是一個女孩子,我知道她的名字叫江婉玲。我沒有跟她說過一句話,甚至沒有看清過她的長相。女生大多低著腦袋進出教室,大多沉默寡言。現在她跟我站一排,手抓著車廂前面的欄桿,她看著前方,眼神炯炯。我想自己的眼神大概也是這樣癡迷。汽車從我們平時步行的沙土上飛速前行,我們高高在上,看到田間的稻子飛快后退,看到地面走動的人,一個個退出視野,汽車太快了,那些田埂上的稻子和農人,一瞬間就被拋到腦后。
這是從未有過的體驗。風,從四面八方撲過來,裹挾著我,很快,我就能飛起來了。
我的臉上癢絲絲的。不是那沖刷式的風,是另一種觸碰。細弱游絲,又有強烈的質感,在我的兩腮、脖頸之間溫和地拂過去,纏繞起來,又被風很快吹散。是柳葉,還是稻葉,不,比那要細太多了,若有若無,若無若有,我切實地感受到這種觸碰的存在。低頭一看,是江婉玲的頭發。
我有點臉紅,我想躲開,一瞬間又動彈不得。江婉玲并不知道風將她的發絲吹到我的兩腮上,我猛地躲開會不會被她發現什么?我不敢近前,也不敢退后,呆呆地保持原來的姿勢,任由發絲糾纏、飄拂、抽打我的眼瞼、鼻尖、脖子。
這是我從未有過的體驗。田野里,風本來很小,車子快速前進加大了風量,風就把與我毫無關系的發絲吹到了我空無一物的胸膛。
我從未跟一個女生站得這么近,是搭乘汽車和車上的狂風讓我們有了這一種渺遠的接觸。我感到一點點溫和的甜蜜,同時為這一點甜蜜而感到羞恥。
我沒有往后退。后面緊挨著的是誰,我根本沒有回頭看。我不想讓任何人知道,我的兩腮此刻染上了紅暈。幸虧,涼風勁吹,在安撫我微微發燙的兩頰。
風在那一刻特別寶貴。很多時候,風從我身邊刮過去,我完全無視無覺,是微末的幾根發絲讓我的神經敏銳起來。
二十多歲,和一個我感到重要的人走在一起,月亮高掛天空,冷風嗖嗖。讀過他的著述,了解文字中他的性情,欽慕他。一次聚會,終于與他相見。臨別時他要回家,我要回賓館,有一段路同行,我主動說要送他一程。他不置可否。從人群里切分出來,剩下我們兩個,不知說什么,不得不說點什么。馬路牙子磕磕碰碰,路面高低不平。我比他年幼,想攙著他,但他并不老。我放棄了這個念頭,抬頭看高樓一角的月亮,風將空中的金屬路牌吹出了哨音,我記住了他眼角冷峻的光和嘴角堅毅的弧線,突然發現讀過的那些文字跟這個人沒有什么關系。我多么喜歡那些澄鮮的文字,而寫出文字的這個人,此刻似乎結冰了。風在耳畔吹起來,呼呼作響,我希望風更大一點,讓走在一起的人無法聽清對方的話,那樣就不必說話了。
不說話,我們走過了兩條街,最后我逃也似地作別。那以后,我再讀他的文字,記憶中被強化的風將那些鮮潤的文字吹干了。我將他的詩集拿到春風里,站在一排槐花下,新鮮的槐花落在書頁上,潔白的花瓣和漆黑的文字疊印起來,突然一陣狂野的風吹過來,花瓣和文字都被春風裹走了,上升,下墜,打了一個呼哨,旋轉著消失在槐樹外面那片淡藍色的天幕里。我捧著沒有了文字的詩集,黯然回到房間。黯然沉淀為黑色的墨汁,重新勾勒、描摹被風掠走的字跡,最后描摹出來的是洇在一起的淡淡墨痕。
我一直和他保持若即若離的聯系,可能是冬夜的風給了我一個錯覺。他堅毅的嘴角也許只是在忍受寒風,而不是不想跟我說話。如果沒有冬風,我們說不定會有一些愉快的交流呢。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與喜歡的文字相逢就夠了,真實的人,在風中還有汗味、煙味、酒味。我喜歡的文字是潔凈的,我熱愛的思想更不會散發出讓人不愉快的味道,它們無色無味,通體透亮、明凈、沒有肉身累贅。
有時候,又渴望在風里遇到一個會呼吸吐納的、真實的人。風把許多緊密的東西吹散,又將不相干的東西聚攏。風無時、無處不在,在我的肉身之外,永恒的風,一直在吹,連石頭都被吹出了縫隙。石縫也不消停,風鉆進去,堅實的石頭瞬間就恍惚起來。
今年春天,我在云南臨滄參加一項活動,被人邀請到茶舍喝茶。茶舍在湖邊,湖水掩映青山,風從水面吹來,清涼、微醺。
主人不停地敬茶。這是臨滄的名茶冰島,是“大葉種之正宗”,茶香濃郁,能清理油脂。我早起未及早餐,腹中空空。這時冰島入侵,我的胃里也掀起了一陣狂風。
有個女孩子在一旁演奏古琴,指法嫻熟中有一絲遲緩。她眼簾低垂,看上去溫柔和順,嘴角似笑非笑,似乎是對自己和順的一種嘲諷。
一曲彈罷,她也過來沖水,遞過來名字叫作“昔歸”“娜罕”“懂過”的名茶讓客人一一品償。喝慣綠茶的我,看到枯藤一樣的茶葉,聽到陌生而又新異的茶名,一時不能適應,想起龍井、碧螺春,冰島、昔歸應該是另一個世界的美吧。
女孩介紹完了,悄悄退下。主人過了一會說,她正懷著孩子,來打短工的。難怪她的步態有一點遲緩,神態有一點慵懶。
我從幾千里之外到這個小城,此后余生大概不會再來。我眼前晃動的這些人,很快就成陌路。我是被風吹過來的,很快就會被風吹走。觥籌交錯,一時間很親近;茶盞頻舉,呼吸的茶香增添了錯覺。
古琴在傳遞一種清潔的情緒,低沉、渾厚,無論演奏者懷著怎樣的心情,這些聲音經過湖水和春風的反射,最后進入我的耳朵時,是充滿情感的。我們對彼此的情況一無所知,雖然也說了不咸不淡的話,但言語都是一些陳詞濫調;樂音、旋律,卻在暗中為陌生生命的交流提供了可能。
那天的風是清軟的、柔和的,底調卻是瀾滄江渾濁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它的另一個名字——湄公河,以及發生在河畔的、被晚年杜拉斯念念不忘的往事。
沉醉在情感的大風里,靈魂會有撕裂的痛楚。輕輕走過一個地方,喝喝茶聽聽音樂,什么都不會發生。是清風還是狂飆,并不由當事人做主。
今天,風從江面吹來,我伸出頭看冉冉升起的八月十五的月亮。月亮銀亮,深邃,一如既往。
從歲月深處也有一股溫和的風吹來,我伸出手掌,想要握住那飽滿的、鼓脹的風,風沒有從指縫間漏掉一點點,它蜷縮在我的掌心,膨大起來,將我緊緊握住。對,是風握住了我的手掌,飽滿、圓滑、充盈,又細切、溫和、酥軟,這種感覺讓我突然想起江婉玲那一綹被風吹散的發絲。它破空而來,又細又軟,又油又黑。
在風里,我能看到風劃過皮膚留下的傷痕。
今夜我認識了商陸
農歷閏五月十九日晚,大半個月亮升起來,天氣炎熱,河水平靜如黑色鏡面,掩映在旱地蘆葦和青蒿叢中。
葎草、楮樹、艾葉,我都認識,輕輕打個招呼就過去了。車燈照亮一種粗壯的植物,很陌生,一嘟嚕一嘟嚕青色、紅色的花,暗夜里格外醒目。下車湊近了看,不是花,是果實,扁圓的,像荸薺、算盤珠,或者一面面比綠豆大不了多少的小鼓,簇擁在花序軸上,遠看真像是一簇簇小花。拿手機植物圖鑒一查,原來它叫“商陸”。
知曉了名字,如同突然認識了一個新的朋友,不斷在河壩上尋找,楮樹、葎草叢中,原來有這么多商陸。商陸是多年生草本,去年在泥塘河邊走來走去,我怎么完全沒看到它呢。
泥塘河過大河口,向前是臨清老屋。白天聽姐姐說過,去世的是王九金。
王九金,我記得這個名字,他比我大四五歲,我們在同一所小學讀書,他五年級,我二年級。成年之后,不在一個村,彼此不知消息。姐姐告訴我,王九金不能生育,抱養了一個女兒,視同己出。女兒長大后出去打工,認識了一個陜西男人,成家,生了倆兒子。一個兒子帶在身邊,一個兒子留在臨清老屋外公這里。不久前,女兒突然將兩個小孩的戶口都從外公這里遷走,留在老屋的孩子也偷偷抱走。王九金覺得一輩子白忙了,人家兒孫滿堂,自己膝下無人。這些零碎,跟誰說呢?
他想了又想,想不明白。他喝下一整瓶農藥,又跑到村子最偏遠的水塘投水自盡。他懷著必死的信念,終于死去了。就在昨天。
這么熱的天,一群人圍在小小的祠堂里忙活,想一想都憋屈。
通往臨清老屋的路邊,高大的白楊長在稻田埂上。附近沒有人家,蕭蕭白楊在黑夜里如靜默的老人,夏夜無風,樹巔葉片安安靜靜立著。這個小時候的玩伴,他的名字與臉龐從記憶的深海里漸漸浮起。
我沒有順著泥塘河開往臨清老屋去看看他,而選擇向右拐進347國道。我想起離泥塘河不到百里的一個同鄉詩人海子的詩句: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告訴他們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我將告訴每一個人//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其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都有名字,只是你不知道。
“和每一個親人通信”,這想法不錯,但是,跟親人說什么呢?“幸福的閃電告訴我的”,親人未必想知道。
這是詩人自殺前兩個月留下的作品。熱情、溫暖、絕望、孤獨。
347國道西邊盡頭的城市名叫德令哈。德令哈是一座平凡的小城,因海子“雨水中一座荒涼的城”而聞名于世。那里建有海子的詩歌陳列館,最近又被命名為“現代詩城”,它的哪只腳與詩歌有關呢?德令哈元代屬吐蕃,建縣不過幾十年,如果不是詩人追慕“姐姐”到西部,不是失戀痛苦爆發出這樣的詩句,德令哈,真的只是邊陲一座“荒涼的城”。
海子二十多歲失戀的痛楚被他敏銳的心靈捕捉,寫下“悲痛時握不住一顆淚滴”的詩句,被人廣為傳播,這座小城也因詩人而天下知名。王九金是海子的同齡人,說著海子一樣的方言,這個年過半百的農民沒有留下一行文字,他用決絕的死亡訴說不可承受的痛苦,但那只限于一個小小村落的人知曉。普通人不能為他的痛苦命名,他的痛苦哪怕如此慘烈真實,也很快消失在茫茫時空中。
泥塘河到大河口拐彎處,壩上有一段小小的空白。一棵大柳樹栽在河灣里,這是河壩上難得一見的高大挺拔的植物。如果爬到樹上,應能俯瞰很長一段河水。這棵突兀的樹下是干凈的黃土,沒有一株植物簇擁它。
車轉過大河口,向德令哈方向慢慢開,大柳樹在后視鏡里緩緩后退,我想起臨清老屋的另一個同學,王文錫。王文錫跟我一個年級,他常來姑姑家走親戚,他姑姑嫁在我們村,是我的鄰居。
一日雨后天晴,他站在屋檐下,透過山墻邊幾棵苦楝樹,望著南邊的天空,對我說,你看,那就是南天門。
是孫悟空的南天門嗎?
你沒看見嗎?那金色的云片旁邊有一扇門,門里射出一道光柱,那就是孫悟空的金箍棒。
楝樹正開著藍色的花,雨后苦澀的香味愈顯濃烈。我看到了云彩,也看到了太陽的光芒,我多么希望天門真的轟然洞開,但心里知道那云片不是門,那光芒也不是孫悟空的金箍棒。
你不信?不信,就看不到;聰明的人才會看到南天門。
我相信,他這樣一說,我看到的全是清清楚楚的云朵,目光恍惚,胡思亂想,都沒有了。
王文錫不屑地走開去。我與南天門失之交臂。
我們后來在不同的鎮上讀初中,初三那年,我轉學到四維山中學,坐下來回頭一看,王文錫在我后面。他微微一笑,算是對我打招呼,低下頭寫數學作業去了。
王文錫哥哥從太湖縣批發了一令白紙,他帶到學校,零售給我們做草稿紙,五分錢一張,店鋪里要賣六分。他將薄薄的白紙折疊成十六開,用胳膊輕輕壓平整。喏,五張,兩毛五,收你三毛,找五分,拿好。
一年后我們考取了不同的師范學校,畢業后分在鄉下不同的學校。我在稻田環抱的鄉村中學一邊教書一邊讀書,能找到的書十分有限。王文錫有次來找我,帶了一本花城出版社的《隨筆》雜志。我讀之忘食,世上竟有這樣的期刊。不久,王文錫再來時,帶來幾十本《隨筆》,他訂閱多年的全都給了我,我因此發現稻田之外另有天地,《散文》《讀者文摘》之外還有別樣的文字與思考。后來去南京教書,我推薦學生訂閱期刊就首選《隨筆》。我感激王文錫,他帶給我的驚喜,我也想傳遞給我的學生。
三十多年來,王文錫都待在鄉下的學校,我們的聯系只限于幾個零星片段。有了微信,我們加了好友。他告訴我,縣里的初中語文教師群將他踢出來了,我回他一個苦笑表情包。不奇怪,他常在朋友圈點評社會事件,看法尖銳,嫉惡如仇。他的文字很好,見識也遠超同儕。他也笑瞇瞇地跟同事喝酒打牌,但不能待在他們的微信群里。最近幾年,他耳聾了,我發信問候,他回信說,聾了好。
泥塘河壩上的草與花,去年蓊蓊郁郁一團,今年一團蓊蓊郁郁,時光在它們身上仿佛靜止了,實際上早已不是去年的草與花。蟲子也不是。鳴叫如昔,卻是去年蟲子的子孫了。此刻,蟲鳴唧唧,我突然心思一動,王文錫家就在附近,我可以去看看他嗎?仿佛有很多話想跟他說。又想,突然造訪,能說些什么?
王文錫十幾歲就讀到最好的文字,形成敏銳的見識,一直生活在稻田邊的學校里,在他生活的群落里落落寡合,那些尖銳的思考和感受呢,是打磨得圓潤了,還是深藏在心底?
剛才河灣里那棵大柳樹,傲岸不群,又謙卑地靠近泥塘河和稻田,一瞬間我覺得它與王文錫竟有幾分相似。王文錫不到二十歲被分配在鄉村學校里教書,如果他接受規訓,成為身邊同事的樣子,就不會有任何反省;如果年輕時出去闖蕩,見過無數陌生的人和事,他也可能會留下動人的詩句或著述。現在,他連自己當下的境況也難以準確命名,未曾言說的痛苦也是無名的。
每一座小城,每一個村莊,每一條河流,城鎮村莊所有的人,哪怕是田間河畔的荒草藤蔓,都有名字。我們憑借名字讓整個世界從陌生變得熟悉。我從灌木叢里認識了商陸,從臨清老屋認識了王九金、王文錫,從附近村莊和遠處的德令哈認識了海子。因為名字,原本稀薄的存在,緩緩從昏昧無邊的暗影中浮現、升起、定格,與他物判然區畫。我們逐漸與陌生的物與人建立聯系,然后產生喜樂和悲傷的情感,或者有幸凝成詩句,傳向遠方。
有了名字,就能被呼喊。在這個世上,被人認出,被人呼喚,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如果“姐姐”回應了海子的呼喚,詩人或許不會25歲就棄世;如果王九金被養女惦記著,他就不會服毒之后又去投水;如果王文錫身邊多一些志趣相投的讀書人,他應該不會安于聾聵。
今夜,我認識了商陸,默默呼喚著商陸的名字,懷著一種持久的、秘而不宣的悲欣。
責任編輯 維 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