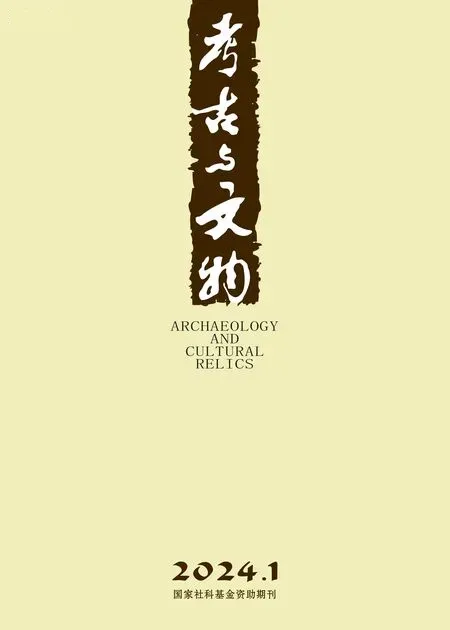《唐韋絢墓志》發微
何如月 鄧夢園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韋絢,為中唐著名文人,其所著小說《劉賓客嘉話》《戎幕閑談》各一卷流傳至今。韋絢兩《唐書》無傳,唯《新唐書·藝文志三》“小說家類”下記有韋絢《劉公嘉話錄》一卷,注云:“絢,字文明也,執誼子也,咸通義武軍節度使。”[1]從中可知韋絢字文明,為韋執誼之子,唐懿宗咸通年間曾任義武軍節度使。據兩《唐書·韋執誼傳》,韋執誼,出身京兆韋氏,長安杜陵人。唐順宗時拜相,推行新政,史稱“永貞革新”。因遭強烈反對而敗,后被貶崖州司馬,元和三年(808年)死于其地[2]。但正史有關韋執誼的記載中,均未見韋絢之名。
20世紀20年代以來,韋絢及其《劉賓客嘉話》《戎幕閑談》開始受到關注,著名學者陳寅恪、唐蘭[3]等都曾嘗試對韋絢生平進行考證,但因為材料缺乏,推論各異,存在著不少空白和疑問。
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所藏的韋絢墓志,詳細記載了韋絢的家世生平、交游仕宦、文學創作及交游往來等情況,為韋絢生平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使得以往的相關學術爭議都可迎刃而解,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因此,本文擬以韋絢墓志為主,碑史互證,對相關問題進行考辨,正誤補闕,以期對唐代文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墓志錄文
韋絢墓志,青石質,邊沿微殘,文字完好。近正方形,長76.5、寬75、厚10厘米。志蓋盝頂,頂面正中陰刻篆書“唐贈吏部尚書韋公志文之石”,邊飾團花紋,四剎有四神圖案(圖一)。志文陰刻楷書,51行,滿行52字,共計2641字(圖二)。墓志銘并序由韋絢從外甥獨孤霖撰寫,侄韋镕篆蓋,親外甥李□□書丹。為方便論述,現將志文迻錄于下:
唐故太中大夫前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吏部尚書京兆韋公墓志銘并序/
再從外甥前吏部侍郎獨孤霖撰/

圖二 韋絢墓志拓本(約1/5)
有唐乾符己亥歲十一月癸酉,舅氏賓客、尚書公薨于京師安德里第,年七十九。十二月庚寅,嗣子維嵩等以公功行洎譜傳/授霖,俾編敘志述。霖伏念公才德器望冠于外族,宜取碩學巨筆,方盡懿業,矧與霖輩匯詞識夐邁且幾,豈霖自謂雅當,/默可遽受?退念公為洛亞,霖始覲贄,實莫敢希公知。翌日賜手諭兩幅,其大略曰:此而不致遠保大,吾不信也。由是果/叨上第,履清級。及公鎮中山,復忝內廷,獲撰《金刀詔》。公于途中謂維嵩等曰:是真玉言,必吾甥所草。霖辱/公初終知己如此,而以讓自外,必為大君子之責,明矣。謹案,公諱絢,字文明,京兆杜陵人。帝高陽、殷二伯、漢丞相之后,自魏及周,/勛賢相望,布于前史。六代祖諱遵通,隋晉州刺史,封龍門縣公,始以國為房。高祖諱會,皇任太子洗馬。曾大父諱仲/昌,皇任京兆少尹。王父諱每,皇任巴州刺史,贈左散騎常侍。家載忠孝,葉傳規范,而未顯大,故流慶于后。皇考/執誼,德宗朝為翰林學士,相順宗,累拜中書侍郎,后贈太尉。殊勛異績,今為美譚;淑行大業,著于別傳。先夫/人贈□國太夫人趙郡李氏,鼎閥柔儀,九族自睦。既娠忽得神夢,公遂誕焉。公幼鐘二艱,哀毀逾于成人,有識/必知其興大也。十八,師故相鄭公余慶詩,滿歲而盡通其要。賓客劉公禹錫牧夔州,公與之故,往而依之。劉公見/所賦篇什及所傳章句,深奇之,待以殊特之禮。三年,劉公閱述作曰:可以掇高科矣。崔公郾知舉,以藝實選人,公再戰/而升第。李太尉德裕鎮滑臺,遽辟之。移鎮西川,又奏為節度巡官,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公以文學自任,無所許共,一與/公言,而敬挹加等。相國王公請為直弘文館,授涇陽縣尉。李公鎮浙西,又辟為節度推官,改監察御史里行。李公謫守宜/春,公從之不歸。盧侍郎術在湘中,慕之,請為觀察支使。初邕糾衡方厚冤死,其妻程氏訴闕獲理。程氏卒,盧公命/公志墓,公因賦《節婦詩》。劉公致書,言白少傅嘆此作若與張藉同時,未知《勤思齊詩》熟〔孰〕為優劣。予知此言甚公,/公之制作,為老輩碩德知重若此。狄公兼謨為御史中丞,非峻整不在選列,首命公即真。會涇縣有獄,公鞫之得實,/大理鄭卿復愛其推狀詳曉,及尹京兆,將奏為司錄,相國李公玨以公之才望拒之。及監祭,有二丞郎祀事不修,故公奏罰/俸。文宗知之,以問丞相曰:此誰家子,盍與美遷?即拜左補闕。莊恪薨,未立太子,公獻《宣政殿賦》以諷。/文宗舉言事之重,執筆螭頭,頗難其拜,俄以公為右史。貞元中,太尉在翰林止于一轉,咸以清秩久次為美,公繼任/之,代以為榮。未幾,召入內試,公詞翰雙逸,故中書令太原公深嘆不及。制曰:韋所試詩賦,皆極典麗,緣與李褒/私嫌不可去,故留新宜守本官,續別優獎。元老奇章公數人無不惜之,公恬然不以置意,李尚書聞之,益加愧伏。/武宗郊天,公進《瑞雪歌》,故相周公墀眾中嘆曰:昨覽瑞雪一聯,比李嶠汾陰落句,彼有慚色。轉司封員外,判考功,有書上/中下三等,皆以實課更之。裴公諗代領,初無同異,且白時宰言:公司績詳允,非所及也。又謂人曰:一官可以坐嘯矣。遷/吏部員外,政視考功,南宮益以公望推重。左仆射王公起諱之及領褒中,懇以副車為請,拜檢校兵部郎中,兼侍御史,轉秘書少監,/兼少尹中丞。居四年,戎事不嘩,府務以理。府變,改河南少尹。時李公分務相府,從其請也。李公貶潮陽,/公亦謫授明州長史,間歲移亳州別駕。守鞫郡獄,以殺人事聞,公視狀不直,諭之不聽,卒移告,不署。后詔御史再覆訊,/守竟以誣人逮,眾僚連罪,改江陵少尹。尋除衛尉少卿,轉京兆少尹,遷太府卿,賜金紫。故事,版計共一亞卿司帑,公奏請異局,/以均勞睱〔暇〕,事雖不行,其后果分為二,見公之深于事用也。遷易定節度觀察等使,兼御史大夫。中山介于鎮、魏,兵勁卒悍,/公處三歲,鄰封如一,軍士莫不畏而悅之。入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大理卿。會北司執柄與河陽護軍隙,因有兇徒誣其下二吏受旨/于護軍,謀害執柄,事下三司,竟置于法。其二吏未讞狀,懿宗御紫宸臨問,公具對,以事歸有司,則有首從,據律不當處極。/由是大忤權臣,二吏亦不免死。因移長告,將十旬,拜秘書監,尚書如故。懿宗深崇釋氏,迎佛骨尤盛,遂命百僚巡禮,公進詩/二篇,以彰君上為人祈福之意。懿宗大悅,褒付所司,錫錦彩器物名香數珠等,宣令從宰臣升望仙樓觀禮,上指問/數四,搢紳榮之。公雅不以進趣為意,多不朝請,未嘗干時相,趣權門,官俸皆為罰克而盡。改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尋得替,復檢校刑部,兼舊官,歲余復替。公文格詩調,得于天縱,奮筆盈幅,居而混成。獎誘后生,常若不逮,聞人有善,喜見于色。/非□此勇名,直體而不能自已。其與(音預)劉公講耨《嘉話錄》,敘衛公征搜撰《閑譚記》,典裁(音在)高古,大為時所傳寫。前后著雜文/近千首,皆盛行于代。先是奕世奉佛,公尤好尚,天付慧解,人莫測度,不擇經卷,向及五紀,故毀譽不可動,得喪不能撓。謂/舊宅囂憒,卜僻靜燕處,腴道胖德,永日卒歲,固非凡識之所仰景,況復則而放諸?以是伯仲六人,公履歷最清顯,/年齡最遐永。帝之臨人,豈無意乎?及微不康,逾夕而舒詳,若冥赴所期,蓋善祐也。夫人河內縣君河南元氏,故居守尚書/夏卿之外孫,故相國元公諱稹之女。女則婦儀,親戚律度,配公合美,鐘郝何足以稱?先公亡廿二年矣。五子:前下邽/縣令維嵩,前渭南縣主簿玄崇,前華陰縣尉道貞,進士光輔、夢松。一女,適進士元溫季子彥猷。維嵩非由傅訓,詩禮自得,累赴計,未遂策/名,屈聲四布。故相曹公為弘文館大學士,奪其志,授挍書郎,轉鄠縣尉。今計司裴仆射辟為潞州推官,轉監察里行。府罷久閑,/敬孝不匱。以公絕俸,乞宰外邑,今相國崔公賢而允之。玄崇等皆好學力文,宜其必紹盛德而榮達也。明年正月壬/申,祔公于縣君之塋,禮也。霖于縣君又為姨弟,內外親厚,且日與維嵩等游,故得備錄,而為銘曰:/
天若水帝,洪流遠裔。爰暨子啇,彭韋佐王。歷周越秦,益大清明。在漢方盛,扶陽知政。一經攸宜,/□學之資。獨與平氏,尹陟同貴。累代繁昌,龍門啟房。逮于圣朝,簮軒劘霄。高曾及祖,名高位下。/顯允中書,人載德輿。壽曷我促,鐘慶必復。穆穆惟公,儒林師宗。翕赩聲稱,象退坐勝。蓮幕瀛洲,/爰登暇游。繡衣皂囊,載筆含香。戎車是佐,洛雍斯亞。長府遲才,紫綬方來。油幢畫戟,□南趙北。/□無冤人,典籍用伸。青宮為客,與道消息。令初美終,保我中庸。/
侄男鄉貢進士□镕篆蓋。親外甥將仕郎右拾遺內供奉賜緋魚袋李□□書。/
二、志主韋絢
有關韋絢的文獻記載非常有限,今以韋絢墓志為主,對學者聚訟較多的韋絢名字排行、生卒年壽、婚姻狀況、宅里葬地等問題進行探討。
1.名字排行
《新唐書·藝文志》云:“絢,字文明也,執誼子也。”[4]兩《唐書·韋執誼傳》未敘韋執誼子息情況,《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韋氏龍門公房列其四子,“曙;曈,字賓之,鄭州刺史;昶,字文明;旭,字就之”[5]。四子中并無韋絢,而云韋昶字文明,陳寅恪據此認為“絢乃昶之改名”[6],韋絢與韋昶乃同一人。
2015年西安市南郊出土了《韋昶墓志》,為韋絢撰文。從墓志中“丞相有六子,公(韋昶)第二子也”,“生一子,曰均郎,甫及弱冠,號天泣血,抱官告十七通,請季父敘而銘之”之語[7],可知韋執誼共有六子,韋昶為二,韋絢最小,《韋絢墓志》亦云“伯仲六人”,與之相符。《韋昶墓志》未記韋昶之字,《韋絢墓志》則云韋絢字文明。韋昶、韋絢兄弟之排行及名字由此可以確定,《宰相世系表》所記及陳寅恪的說法也得以勘正。
綜合兩方墓志,進一步得知韋昶和韋絢乃同父異母兄弟。《韋昶墓志》云“先妣京兆杜夫人,即黃門之嫡女也”,韋昶生母為韋執誼正妻宰相杜黃裳之女杜夫人;《韋絢墓志》云“先夫人贈□國太夫人趙郡李氏,鼎閥柔儀,九族自睦,既娠忽得神夢,公遂誕焉”,韋絢乃趙郡李氏所生,為韋執誼庶子。韋執誼元和三年(808年)貶死崖州,今海南省瓊山縣尚有韋執誼與夫人合葬墓,墓前有清代所立之碑,上題“唐始祖賜進士翰林院禮部尚書延英殿丞相韋執誼文靜公杜夫人范夫人墓”[8]。從側面證明韋執誼貶謫嶺南時,杜夫人尚在世,而此時韋絢已經出生(見下文),所以其母李氏只可能為韋執誼妾室。
《韋昶墓志》載其卒于咸通四年(863年),享年七十;《韋絢墓志》云韋絢卒于乾符六年(879年),享壽七十九。推其生年,則可知韋昶比韋絢年長八歲。
2.生卒年壽
墓志發現之前,惟一可考韋絢生年的資料,是傳世的韋絢《劉賓客嘉話》自序,其文云:“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孥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年長慶元年春。”[9]學者據此推斷韋絢生年,各不相同。唐蘭以為韋絢當生于德宗貞元十六年(800年)[10],周勛初、陶敏等主張貞元十七年(801年)[11],李劍國主張貞元十二年(796年)[12],王偉推定為貞元十四年(798年)[13]。
關于韋絢卒年,諸家多無論說,惟王偉根據《唐方鎮年表》卷四載韋絢于咸通四年至七年任義武軍節度使,認為他大致卒于任上或稍后,可能死于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享年69歲[14]。
今據《韋絢墓志》,韋絢卒于乾符六年(879年),享壽79,推知其生年在德宗貞元十七年(801年),學術界爭論的韋絢生卒及年壽問題從此可以塵埃落定。
3.婚姻子息
《韋絢墓志》云:“夫人河內縣君河南元氏,故居守尚書夏卿之外孫,故相國元公諱稹之女。”元稹與白居易為生死莫逆之交,多有酬唱。白居易所撰《元稹墓志銘》曰:“(元稹)大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仆射,加賻贈焉。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裴氏,……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衛、道扶,齠齔。”[15]由此可知,元稹和早逝的前夫人韋叢所生子女,只有一女保子成人,嫁與韋絢。
大和二年(828年)白居易作《和微之詩二十三首》,其中《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韻》云“君仍畢婚娶”[16],詩中所云婚嫁,當指元稹嫁女保子于韋絢之事。因為從《元稹墓志》可知,元稹離世時其與續弦裴氏夫人所生子女年紀尚幼,成年者唯有元保子一人,可以婚配。所以韋絢與元氏成婚,是在大和二年三月底以前。
韋絢登第,亦在大和二年。《韋絢墓志》云:“崔公郾知舉,以藝實選人,公再戰而升第。”《舊唐書·崔郾傳》曰:“轉禮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掌貢士。平心閱試,賞拔藝能,所擢者無非能士。”[17]崔郾知貢舉共兩年,在文宗大和元年、二年,韋絢“再戰而升第”,故其登第應在大和二年,同年取中的還有杜牧等人[18]。
唐代科舉,一般正月考試,二月放榜。韋絢二月登第,三月完婚,堪稱古人歆羨的“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據韋絢墓志,夫人“先公亡廿二年矣”,韋絢卒于乾符六年(879年),那么韋保子去世當在大中十一年(857年)。兩人共同生活三十年,生有五子一女,即墓志所載之“前下邽縣令維嵩,前渭南縣主簿玄崇,前華陰縣尉道貞,進士光輔、夢松;一女,適進士元溫季子彥猷”。
4.宅里葬地
韋絢墓志云:“薨于京師安德里第。”韋絢離世前所居之安德里,位于唐長安朱雀門街東第二街九坊之最南,直抵外郭城之南墻,東即啟夏門。安德里在唐時為偏僻之地,居者稀少,“自興善寺以南四坊,東西盡郭,率無第宅。雖時有居者,煙火不接,耕墾種植,阡陌相連”[19]。為什么韋絢會把宅第安置在此呢?墓志有所說明:“先是奕世奉佛,公尤好尚,天付慧解,人莫測度,不擇經卷,向及五紀,故毀譽不可動,得喪不能撓。謂舊宅囂憒,卜僻靜燕處,腴道胖德,永日卒歲,固非凡識之所仰景,況復則而放諸?”原來韋絢潛心奉佛,特地放棄了原來熱鬧繁華的舊宅,專門選擇此閑僻之處靜修,優游卒歲。那么舊宅又在何處?《韋昶墓志》載其“捐館于永寧里私第”,永寧里位于長安朱雀街東第三街,皇城之東第一街,北臨親仁坊,南臨永崇坊,坊內有中書令裴炎宅、禮部尚書裴行儉宅、宰相李輔國宅、白敏中宅等,是當時達官貴人居住的繁華之地[20]。永寧里宅第,應該是韋執誼為相時所營,韋執誼貶謫崖州后,舊宅仍為其諸子所居。只不過,韋絢后來搬出永寧里,在安德里另營宅第。
按照禮制,韋絢死后應當歸葬家族墓地,即先塋、祖塋。《韋昶墓志》云“窆于先塋之西興牛村也”,此“先塋”應當就是韋絢的祖塋。韋昶墓志出土的地理位置,在今西安市長安區三府井村以南500米,高望堆村以北約400米處,這里為少陵原之地,是唐代京兆韋氏家族的主墓葬區[21]。據《舊唐書·杜黃裳傳》:“女嫁韋執誼,……及執誼譴逐,黃裳終保全之,洎死嶺表,請歸其喪,以辦喪事。”[22]韋執誼死于崖州,岳父杜黃裳曾謀劃將其歸葬,但因杜黃裳很快病死而作罷。大中四年(850年)李德裕貶謫崖州時,曾至韋執誼墓前拜謁,并寫下《祭韋相執誼文》。咸通四年(863年),韋執誼第二子韋昶離世,韋絢為其兄所寫墓志銘云:“望宅兆于舊阡,植新松于道邊。東瞻宰樹橫墓煙,四望棣華松柏連,同穴未祔墳巋然,陵平谷滿悲不宣。”細繹“東瞻宰樹”“四望棣華”之語,可知在韋昶去世時,韋執誼家族墓地就已經建好,父子兄弟各有其位。雖然韋執誼貶死海南,后來是否返葬長安,無法考證。
《韋絢墓志》云:“夫人河內縣君河南元氏,……明年正月壬申,祔公于縣君之塋,禮也。”墓志沒有明確記載韋絢死后葬所,而云祔葬于其妻元氏。元保子乃韋絢正妻,先亡,理當入葬韋氏家族墓地。韋絢有女韋道升,開成四年(839年)未及笄而殤,韋絢親自撰寫《唐故韋氏女子道升墓銘》,其中云“葬城南焦村,暱祖先之塋”。今天的長安焦村,也與韋昶墓所在的高望堆村接壤,這均能說明韋絢當時是將女兒葬入韋氏家族墓地的[23]。既然室女葬入家族墓地,那么夫人元保子死后,當然也要入葬韋氏祖塋。韋絢死后祔葬于元氏,合情合理。
盡管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收藏的《韋絢墓志》出土地不明,其夫人元氏也只有墓志蓋存留,無法確知夫婦倆葬地所在,但以現有材料及情理推測,韋絢夫婦的葬地當在長安高望堆村韋氏祖塋。
三、韋絢的文學成就
京兆韋氏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族,不僅冠冕相繼,而且才士眾多,韋絢伯父韋執中、父韋執誼等均有詩文流傳,韋絢著述今可見者僅有《劉賓客嘉話》《戎幕閑談》,大多作品無從稽考。而《韋絢墓志》記錄了韋絢的很多文學活動,全面展現了韋絢的文學創作情況,極大彌補了傳世資料之闕略。
墓志云:“公文格詩調,得于天縱,奮筆盈幅,居而混成。”韋絢文學才能的養成,有來自于家族傳統的熏陶和父親韋執誼的影響。韋執誼進士及第,二十余歲就進入翰林院任學士,常與唐德宗以詩歌唱和,李德裕稱他“文學世雄,智謀神貺”[24]。而韋絢文學成就的取得,更多則是得益于他后天的努力及與劉禹錫、李德裕等人的交游。
墓志云韋絢“前后著雜文近千首,皆盛行于代”,可知他勤于著述,文章數量驚人,流傳甚廣。志文特別記載了受到劉禹錫、白居易等人稱譽的《節婦詩》《瑞雪歌》《宣政殿賦》等詩賦,都應是他的得意之作。惜這些雜文詩賦今天均已亡失,令后人無從窺其文格詩調。
墓志又載:“其與劉公講耨《嘉話錄》,敘衛公征搜撰《閑譚記》,典裁高古,大為時所傳寫。”可見韋絢《嘉話錄》《閑譚記》在當時就已經廣為傳抄,影響極大。這兩部筆記小說,在宋代歐陽修《新唐書·藝文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中都有著錄,今天有幸流傳下來,雖非完璧,但尚能見其大概。
以往學者對韋絢《嘉話錄》及《閑譚記》成書背景的考察,多依靠其序文內容。而今韋絢墓志的披露,不僅印證了傳世文獻的某些記載,而且為我們研究韋絢與劉禹錫、李德裕之間的交往提供了更多確切詳實的資料,對深入探討兩書的成書背景及創作緣由大有幫助。
劉禹錫堪稱韋絢的引路人。劉禹錫和韋絢之父韋執誼交好,兩人在永貞年間共同從事政治變革活動,失敗后同被貶官外放。韋絢幼年喪父,四處漂泊,青年時前往夔州依附劉禹錫。《韋絢墓志》云“賓客劉公禹錫牧夔州,公與之故,往而依之。劉公見所賦篇什及所傳章句,深奇之,待以殊特之禮”,劉禹錫對故人之子特別加以照拂,賞識提攜,正因為有這樣情同父子的密切關系和數年間的朝夕相處,才有韋絢《劉賓客嘉話》的產生。
李德裕對韋絢有知遇之恩,《韋絢墓志》所云“李公以文學自任,無所許共,一與公言,而敬挹加等”,當非虛語。李德裕為著名政治家,出將入相,在平定邊患、整頓內憂方面,立下了顯赫功績。韋絢進入仕途,首先被李德裕召辟。李德裕一生,始終處在牛李朋黨和南衙北司之爭的政治漩渦之中,曾多次被排擠出朝,大和三年(829年)九月任義成軍節度使、大和四年十月任劍南西川節度使、大和八年十一月任浙西觀察使、大和九年四月任袁州刺史,即《韋絢墓志》所云“鎮滑臺”“鎮西川”“鎮浙西”“謫守宜春”者。在李德裕出任方鎮期間,韋絢都追隨左右,為其幕僚。而李德裕晚年罷相后,先為東都留守,后譴海南,韋絢亦休戚與共,未曾遠離。《韋絢墓志》云“改河南少尹,時李公分務相府,從其請也。李公貶潮陽,公亦謫授明州長史”,即可證之。總之,由《韋絢墓志》可知,韋絢仕途上的逐步升遷,與李德裕的舉薦賞拔分不開;韋絢之宦海生涯,也隨著李德裕的進退而起浮,兩人淵源深厚。《舊唐書·李德裕傳》載:“(衛公)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居臺輔,而讀書不輟……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見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錄》行于世。”[25]李德裕博覽群書,文采冠世,他每任方鎮,所辟幕僚亦多文學之士,游談宴飲,高談闊論,賓主相得。韋絢奉命記錄了當時的談話,《閑譚記》應運而生。《閑譚記》后作《戎幕閑談》,其中韋絢自序云:“贊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語古今異事。當鎮蜀時,賓佐宣吐亹亹,不知倦焉。乃謂絢曰:‘能題而紀之,亦足以資于聞見。’絢遂操觚錄之,號為《戎幕閑談》。大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巡官韋絢引。”[26]這段話正可與韋絢墓志記載互相印證。唐人段成式曾在李德裕幕府任職,撰有小說《酉陽雜俎》,其中亦載有李德裕數條語錄。由此可見,這位政治家博物好奇的個性和自由縱談的幕府風氣,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當時筆記小說的繁榮。
五、結語
韋絢墓志的發現,為研究韋絢的家族世系、生平交游、文學創作提供了可貴的第一手資料,它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當時宦官擅權、朋黨相爭、藩鎮割據的政治面貌,為研究中晚唐歷史提供了佐證。限于篇幅,本文僅探討了學術界聚訟較多的有關韋絢生平及文學創作等相關情況,而墓志詳載的仕宦履歷,對于全面考察韋絢的人生軌跡、解析紛繁復雜的政局都有極其重要的價值,筆者將另文論述,此處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