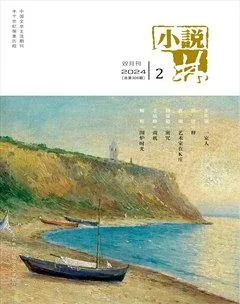蕭紅的新年
與作家相遇,最好的方式便是走入他們的文學世界。之于蕭紅,我卻有著更多的奢念。每當我走在哈爾濱中央大街,就總是覺得能夠與她不期而遇。她與蕭軍租住的商市街,如今已化身成為紅霞街,車來人往中,雖尋不見舊日蹤跡,散文集《商市街》中那些躍動的文字卻依然能把我帶回到九十年前的哈爾濱,不變的是這個城市歐式建筑帶來的氣質,尤其是在陽歷新年,當冬日黃昏的余暉落在鋪滿“面包石”的中央大街上時,沒有一個城市比這里更適合跨年。
元旦,意味著舊年的結束,新年的起始,與蕭紅所處的那個除舊布新的時代,相得益彰。蕭紅作為深受新思想影響的文學青年,她的認知和行為與其父輩早已是背道而馳。從其一生中度過的一個又一個不同尋常的新年,或可勾勒出蕭紅短暫無依的生命旅程。
元,即“首”;旦,為“日”,元旦就意味著是新一年的第一天,是歲之初,亦是月之始、時之元。而在民國之前,“元旦”就是春節。《晉書》記載:“顓帝以孟夏正月為元,其實正朔元旦之春”。
有關“元旦”的由來,有這樣一個傳說。相傳在遠古的堯舜時期,堯帝深受百姓愛戴,任人唯賢,他沒有傳位給自己不成器的兒子,而是傳給了同樣才高行潔的舜,舜如法炮制,又禪位給治水有功的禹。于是,后世百姓便將舜祭祀天地和堯的那天,當作新年第一天,是為“元旦”或“元正”,這就是遠古時期的“元旦”。此后,在夏商周,分別以正月、臘月十二月和冬月十一月初一為元旦,秦代以十月初一為元旦,直到漢武帝時,又恢復以正月初一為元旦,并延續至1911年。
1911年,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這一年的端午節,蕭紅在黑龍江省呼蘭縣出生。轉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孫中山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并于次日發出《臨時大總統改歷改元通電》:“各省都督鑒:中華民國改用陽歷,以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經由各省代表團議決,由本總統頒行。”其中,“黃帝紀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就是公元1912年1月1日。從此,中華民族迎來了第一個公歷元旦。此時的蕭紅不滿一歲,尚不知道這意味歷史的重大轉折。
1929年新年過后,蕭紅在家里的安排下,與小學教員汪恩甲訂婚。蕭紅一開始不置可否,但當她發現汪恩甲有吸大煙的惡習后,曾跟家里提出過想要退婚,遭到了拒絕,蕭紅于是萌生了追隨表哥陸哲舜到北平讀書的想法。次年,蕭紅如愿成為了北平女子師范學校附屬女子中學高一學生。
1931年的新歷1月1日,蕭紅在饑寒交迫中度過,那天北平下了雪,蕭紅打起寒顫,“開了門望一望雪天,呀!我的衣裳薄得透明了,結了冰似的。”陸家、汪家、張家三家的反對,讓倆人在北京的讀書生活愈加窘迫。無論是感情還是生活,都難再維系,陸哲舜首先敗下陣來,如此也徹底斷了蕭紅的指望。半月后,二人離開北平,返回了哈爾濱。
1932年的新年,蕭紅與汪恩甲在哈爾濱道外區十六道街的東興順旅館(今道外瑪克威商廈)度過,暫時結束了此前短暫的流浪生涯,與汪恩甲度過了一小段還算溫暖的時光。然而好景不長,5月時,因無力承擔生活費,汪恩甲以回家要錢為由,從此杳無音信。蕭紅再次陷入困頓的境地,直至蕭軍的出現。
1933年的跨年夜讓蕭紅永生難忘,那是她一生中為數不多的快樂時光。那晚,應哈爾濱左翼名士馮詠秋之約,蕭紅第四次來到了牽牛坊。那是一座獨門獨院的俄式平房,若在仲夏,院墻會爬滿盛開的牽牛花。三五成群的文藝青年,時常聚集于此,暢談古今,吟詩作對,好不熱鬧。牽牛坊其實是哈爾濱地下黨接頭的秘密聯絡點,蕭紅在這里結識了有為等共產黨人,為日后的創作積累了素材。但此時的她還沒有正式發表文學作品,成為拿稿費的職業作家,經常處于饑寒交迫的狀態,牽牛坊不僅為她提供了精神食糧,也成了她能夠飽腹的地方。前三次造訪牽牛坊,蕭紅還很拘謹,這一次“正是新年的前夜,主人約我們到他家過年。其余新識的那一群也都歡迎我們在一起玩玩”。席間,女仆拿了三角錢買回松子,供大伙兒消遣,但在蕭紅看來,實在太過浪費。“多余呀!多余呀!吃松子做什么!不要吃吧!不要吃那樣沒用的東西吧!”那一年的農歷新年,蕭紅也是在牽牛坊度過的。大家聚在一起守歲祈福,跳舞歡唱,還玩起了捉迷藏,對蕭紅來說,那的確是在一生當中都難得的歡快日子。
1935年的新年,蕭紅是與蕭軍在上海拉都路福顯坊22號的新家中度過的。那是一間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弄堂房子,毗鄰菜園和荒地。二蕭在1935年1月2日去信魯迅先生匯報了入住新居的情況,先生4日回信賀二人喬遷之喜,“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也許是因為開了個好頭,這一年,蕭紅開始在文壇風生水起,出版了她個人最為重要,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作品——《生死場》。
1937年的新年,蕭紅在日本東京的寂寥中度過。鄰居家著了一場大火,好在她是在朋友家過的夜。半月前,東京街頭就已有了新年的氛圍,每逢佳節倍思親,從異鄉到異國,新年的氣味于蕭紅而言只有無邊的寂寞而已,“人家歡歡樂樂,但是與我無關”。旅日期間,孤獨與病痛總是常伴蕭紅左右,于是她只好付諸于筆端。元旦前夕,蕭紅給蕭軍發去了新年祝福,“現在頭亦不痛,腳亦不痛,勿勞念念耳。專此,年禧。”
1938年的新年,蕭紅在武漢的住所里起得很早,雖然室外下起了雨夾雪,但生起火爐后,室內能達到15攝氏度,“杯子是溫暖的,桌面也是溫暖的,凡是我的手所接觸到的都是溫暖的。”這是位于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21號的一處寓所,二蕭與蔣錫金分住兩屋,并成為親密無間的朋友,他們經常一起吃飯,蕭軍負責買菜,蕭紅掌勺。但由于是公共廚房,蕭紅為了避免和鄰居們擠在一起,就自己在臥室搭了個爐子。《呼蘭河傳》便是在這個時期開始動筆的,由于蔣錫金時常不在家,二蕭便可分坐兩屋專事寫作。
1940年的新年,蕭紅與端木蕻良在戰火紛飛的重慶度過。在日寇的狂轟亂炸中堅持了一段時間后,二人決定離開重慶,經過一番比較,終而選擇前往香港。這一年,蕭紅接連出版文學作品,短篇小說集《狂野的呼喚》《蕭紅散文》《回憶魯迅先生》相繼問世。完稿長篇小說《馬伯樂》的第一部后,因種種原因,蕭紅轉向了《呼蘭河傳》的續寫,邊寫邊刊,載于香港《星島日報》,12月27日連載完成。這一年,蕭紅遠離戰亂,創作發表順利,與端木相處和諧,并結識了周鯨文等新朋友,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1941年的新年,蕭紅在九龍尖沙咀金巴利道納士佛臺3號二樓的一間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間里,度過了人生中最后一個歡愉的元旦。1月1日,她與端木蕻良收到了許地山夫婦寄來的自制賀年片,他們也自己做了一些賀年卡郵給朋友們。這樣的節日氛圍不久被皖南事變打破,蕭紅據此創作了短篇小說《北中國》。
蕭紅的身體健康狀況開始每況愈下,但這段時期卻是蕭紅短暫文學創作生涯中的又一個高產期,不僅有小說《小城三月》,還發表了《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九·一八”致弟弟書》。1941年11月中旬,蕭紅因肺病住進瑪麗醫院。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滯留香港的文藝界人士開始分批撤回,但所有的行動,蕭紅都因身體原因無法參加。戰亂中,蕭紅不但難以靜心養病,還要反復移挪住所。12月25日,香港淪陷,此時的蕭紅只能暫居在時代書店的書庫里。
1942年元旦前后,香港一片混沌,日軍舉行了“入城儀式”,并宣布只允許10元以下港幣流通,隨后又實行了限購政策,一個人一次只能按照規定價格購買2.5斤米麥,米鹽魚肉2錢。端木蕻良四處奔走,為蕭紅尋找醫院,終于打聽到香港最大的私立醫院——跑馬地養和醫院即將恢復開業,蕭紅于1月12日住進該院,隨后卻因誤診導致病情進一步惡化。轉院至瑪麗醫院后,又因瑪麗醫院被日軍接管,被轉送到法國醫院。此時的法國醫院由于被日軍當做軍事物資而停止供應民用,無藥可醫的蕭紅病入膏肓,于1月22日上午10時許與世長辭。
蕭紅曾撰文《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稱,“從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惡而外,還有溫暖和愛。”于是我們可以猜想兒時的蕭紅在新年里,或許會時常遭到父親的叱罵,這時候,小蕭紅便會跑到祖父的房里,“在大雪中的黃昏里,圍著暖爐,圍著祖父,聽著祖父讀著詩篇,看著祖父讀著詩篇時微紅的嘴唇”。
窗外的雪下個不停,好像是要為這個注定漂泊一生的女孩,留住這片刻的溫暖時光。
作者簡介:任詩桐,文學碩士,主任記者,黑龍江文學館館員,主要從事文學傳播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作品見于《文藝報》《中篇小說選刊》《作家文摘》《北方文學》等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