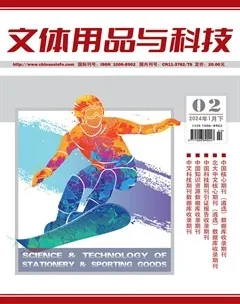新媒體語(yǔ)境下鄂溫克族狩獵體育文化傳承研究
周勇潔(哈爾濱師范大學(xué)體育科學(xué)學(xué)院 黑龍江 哈爾濱 150025)
1、古代先民體育文化溯源
1.1、勞動(dòng)生產(chǎn)體育文化
體育和勞動(dòng)生產(chǎn),二者都包含身體的活動(dòng),關(guān)于二者的關(guān)系,馬克思就曾說(shuō)過(guò):“由于勞動(dòng)要求實(shí)際動(dòng)手和自由活動(dòng),就像在農(nóng)業(yè)中那樣,這個(gè)過(guò)程同時(shí)就是身體鍛煉的過(guò)程。”由此來(lái)看,可以說(shuō)勞動(dòng)生產(chǎn)也是體育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鄂溫克族曾經(jīng)就是一個(gè)把畜牧業(yè)、漁業(yè)和狩獵作為主要?jiǎng)趧?dòng)生產(chǎn)途徑的民族,當(dāng)然生產(chǎn)方式中還包括些許林業(yè)、采集業(yè)和農(nóng)業(yè)。在捕魚(yú)狩獵和游牧的過(guò)程中,鄂溫克族先民善于總結(jié)大自然的規(guī)律,為了提高生產(chǎn)效率而發(fā)展生產(chǎn)技能,從實(shí)踐中總結(jié)規(guī)律。其中包含大量模仿生產(chǎn)活動(dòng)中需要用到的動(dòng)作或是技能,從實(shí)際出發(fā),發(fā)展其熟練程度,這些動(dòng)作技能就為鄂溫克族的民族傳統(tǒng)體育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而后通過(guò)數(shù)代人的整理和修正,逐漸發(fā)展為世代傳承的傳統(tǒng)體育項(xiàng)目。《魏書(shū)·失韋列傳》有記載:“唯食豬魚(yú),養(yǎng)牛馬,俗又無(wú)羊。夏則居城,冬逐水草,亦多貂皮。”既養(yǎng)牛馬,自然也可說(shuō)明騎馬就是鄂溫克族的日常體育活動(dòng)。《隋書(shū)·北狄列傳·室韋》中也提到“寢則屈為屋……多貂”,說(shuō)明其狩獵對(duì)象為貂,貂皮作為衣物以御寒,又有“氣候最寒,雪深沒(méi)馬……射獵為務(wù),食肉衣皮……俗皆捕貂為業(yè),冠以狐狢”,這也印證了室韋人的勞動(dòng)生產(chǎn)與騎射體育文化的密切性。
1.2、民俗娛樂(lè)體育文化
在特定的區(qū)域內(nèi),與民俗現(xiàn)象相關(guān)并且成為民族社會(huì)活動(dòng)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民俗娛樂(lè)體育。鄂溫克族人民將本民族的特殊風(fēng)俗元素融入到體育互動(dòng)中,以起到充實(shí)生活、鍛煉身體的作用,由此衍生出了一系列的體育項(xiàng)目,這些“益智有趣”的體育項(xiàng)目,也極大地豐富了鄂溫克族人民的業(yè)余文化生活。《隋書(shū)·北狄列傳·室韋》中記載:“地多積雪,懼陷坑井,騎木而行。”由此而觀,室韋受環(huán)境氣候影響為方便出行而出現(xiàn)了“騎木”這項(xiàng)體育活動(dòng),坐在木板上在雪地中滑行,這類(lèi)似于今天的冰爬犁。《新唐書(shū)·北狄列傳·室韋》記載:“婚嫁則男先傭女家三歲,而后分以產(chǎn),與婦共載,鼓舞而還。”說(shuō)明樂(lè)舞是唐代室韋人日常進(jìn)行的體育文娛活動(dòng),如嘎拉哈、鹿棋、拉棍、頸力等。其中,搶銀碗是從古老婚禮演變來(lái)的,圍獵比賽則是古代集體狩獵習(xí)俗的濃縮和再現(xiàn)。
1.3、軍事體育文化
體育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地位極為重要,現(xiàn)在軍事訓(xùn)練離不開(kāi)體育訓(xùn)練,古代冷兵器時(shí)代體育的重要性便不言而喻了。鄂溫克族的傳統(tǒng)體育中也可以看到很多軍事訓(xùn)練印記,“精騎射,善馳逐”便是古代鄂溫克族在戰(zhàn)爭(zhēng)中給人留下的印象。抗金、反清和反沙俄侵略中鄂溫克族將騎射技能融入軍事戰(zhàn)爭(zhēng),其民族頑強(qiáng)精神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騎射技能在軍事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也在之后演變?yōu)榱艘环N日常娛樂(lè)體育活動(dòng)。但是“射箭、騎馬”作為軍事體育文化確實(shí)是有跡可循的。《舊唐書(shū)·北狄列傳·室韋》記:“兵器有角弓楛矢,尤善射,時(shí)聚弋獵,事畢而散。”對(duì)兵器“楛矢”“騎射”記載這極大程度吻合騎兵作戰(zhàn)。《新唐書(shū)·北狄列傳·室韋》又有:“雖猛悍喜戰(zhàn),而卒不能為強(qiáng)國(guó)……器有角弓、楛矢,人尤善射。”騎兵作戰(zhàn)給史官留下的印象,算是對(duì)其極大程度的肯定。騎射結(jié)合軍事體育文化,將鄂溫克族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驍勇、猛悍深入人心,這也很大程度發(fā)揚(yáng)了軍事體育。
1.4、傳統(tǒng)節(jié)日體育文化
瑟賓節(jié)是鄂溫克族慶祝豐收、表達(dá)對(duì)自然的敬畏之情的重要節(jié)日。在節(jié)日中,人們會(huì)點(diǎn)燃篝火,煮熊肉、熊脖子、熊頭,圍著篝火唱歌跳舞。在這個(gè)節(jié)日中,體育文化是一個(gè)重要的組成部分,體現(xiàn)了鄂溫克族人民的勇氣、智慧和團(tuán)結(jié)精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體育活動(dòng)是“搶樞”。搶樞是鄂溫克族傳統(tǒng)的體育比賽項(xiàng)目,搶樞玩法與橄欖球接近,但對(duì)抗中融入了蒙古式摔跤,樞只能用手傳遞,不能拋、踢。這個(gè)比賽項(xiàng)目不僅考驗(yàn)選手們的速度和耐力,還需要他們具備良好的團(tuán)隊(duì)協(xié)作精神。此外,瑟賓節(jié)還包括射箭、摔跤、賽馬等體育活動(dòng)。總的來(lái)說(shuō),瑟賓節(jié)中的體育文化體現(xiàn)了鄂溫克族人民的勇氣、智慧和團(tuán)結(jié)精神,展示了鄂溫克族獨(dú)特的文化魅力。
2、近代多元體育文化影響
受限于氣候,在清初以前東北一直是一個(gè)地廣人稀的地方,雖然歷史上有過(guò)幾次向東北移民的高潮,但是這并沒(méi)有影響到東北社會(huì),外來(lái)人口一直處于一個(gè)較小的比重,在東北地區(qū)活躍的仍然是原生少數(shù)民族。鄂溫克族作為北方原生民族一直是以狩獵經(jīng)濟(jì)為主的,在清朝末期開(kāi)禁以后才流入大量外來(lái)人口,至此漢族移民與其民族文化的到來(lái),開(kāi)始對(duì)東北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產(chǎn)生了不小的影響。
外來(lái)民族的到來(lái),與原生民族開(kāi)始頻繁接觸。原生民族的服飾文化逐漸發(fā)生變化,曾經(jīng)食肉寢皮的狩獵、游牧民族在了解了棉衣的實(shí)用與美觀之后也開(kāi)始習(xí)慣了穿棉布衣服。清朝末年,用獸皮做衣服的鄂溫克族也開(kāi)使習(xí)慣穿布料做的衣服。原生民族開(kāi)始接觸到耐用舒適的布衣,其傳統(tǒng)的獸皮、魚(yú)皮服飾文化也開(kāi)始沒(méi)落,這對(duì)其狩獵體育文化存在一定程度沖擊。
隨著與漢人經(jīng)濟(jì)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信仰薩滿(mǎn)教的人也越來(lái)越少,特別是長(zhǎng)期和關(guān)內(nèi)漢人生活雜居的鄂溫克族人,被漢族同化之后便開(kāi)始將薩滿(mǎn)教遺忘,以至于清代統(tǒng)治者推行薩滿(mǎn)教也未能起到效果。
3、現(xiàn)代民族共同體體育文化形成
1946 年底,察巴奇開(kāi)始土改工作,南部村莊開(kāi)始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北部山村保留狩獵生產(chǎn)。新中國(guó)成立之初,鄂溫克族農(nóng)民的農(nóng)業(yè)技能很低,合作社的漢族農(nóng)民教鄂溫克族農(nóng)民選種、施肥、播種、涉水、收割,提高了鄂溫克族農(nóng)民的農(nóng)業(yè)技能。1955年,鄂溫克族、達(dá)斡爾族、鄂倫春族、漢族等各族人民在三個(gè)互助組的基礎(chǔ)上成立了初級(jí)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共有17 戶(hù),其中鄂溫克族13 戶(hù)、達(dá)斡爾族2 戶(hù)、漢族2 戶(hù)。1956 年,在此基礎(chǔ)上又?jǐn)U大了21 戶(hù),成為高級(jí)農(nóng)業(yè)合作社。農(nóng)業(yè)合作社按照各自的專(zhuān)業(yè)分工,從事種地、狩獵、采集等生產(chǎn)活動(dòng)。然而,由于糧食產(chǎn)量低,農(nóng)業(yè)只是一種輔助經(jīng)濟(jì),鄉(xiāng)鎮(zhèn)的主要經(jīng)濟(jì)是狩獵經(jīng)濟(jì)。
在長(zhǎng)期的狩獵生產(chǎn)中,察巴奇的鄂溫克人形成了以狩獵生產(chǎn)為中心的民族文化。鄂溫克人離不開(kāi)森林,森林是他們生命的源泉。他們對(duì)自然資源有合理的獲取,認(rèn)為狩獵是為了獲得溫飽,絕不能濫殺,形成了簡(jiǎn)單可持續(xù)的狩獵理念。鄂溫克人的生產(chǎn)方式轉(zhuǎn)變后,狩獵生產(chǎn)被農(nóng)牧水產(chǎn)取代,狩獵方法和技能無(wú)法繼續(xù)傳承,傳統(tǒng)體育文化傳承出現(xiàn)斷層現(xiàn)象。
4、新媒體語(yǔ)境下鄂溫克族狩獵體育文化的傳承困境
新媒體是依托網(wǎng)絡(luò)信息技術(shù)發(fā)展的媒體播放形式,通過(guò)互聯(lián)網(wǎng)、電腦、手機(jī)等接收信息,包括網(wǎng)站、論壇、微信、微博、視頻平臺(tái)等。由于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和電子信息技術(shù)的廣泛應(yīng)用,傳統(tǒng)媒體存在空間局限性和時(shí)效差異性問(wèn)題。隨著科技進(jìn)步和時(shí)代發(fā)展,新媒體通過(guò)數(shù)字、網(wǎng)絡(luò)和移動(dòng)技術(shù)傳播,不受時(shí)間和空間限制,成為人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新媒體語(yǔ)境下,鄂溫克族狩獵體育文化傳承發(fā)展面臨以下困境。
4.1、傳承文化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沖擊
鄂溫克族有自己的語(yǔ)言但沒(méi)有文字,知識(shí)文化技能都是通過(guò)口耳相傳的方式在家庭和部落之間傳承。狩獵文化作為一種生活技能,其目的是為了提高生產(chǎn),當(dāng)遇到外來(lái)生產(chǎn)效率更高的生產(chǎn)技能,鄂溫克族內(nèi)的狩獵文化傳承便會(huì)受到?jīng)_擊。清末年間接觸到漢人制作的更加精致耐用的棉衣、布衣,鄂溫克族與狩獵文化相關(guān)的魚(yú)皮、獸皮服飾文化就開(kāi)始沒(méi)落。境外的鄂溫克族(埃文基)在蘇聯(lián)集體化的引導(dǎo)下,原有的獵人、狩獵文化傳承人也轉(zhuǎn)型成為國(guó)有單位的鹿飼養(yǎng)者。作為一種娛樂(lè)體育文化,是為了充實(shí)生活滿(mǎn)足精神需求。但是在生產(chǎn)資料較為豐富,娛樂(lè)方式多樣化的現(xiàn)代社會(huì),傳統(tǒng)的娛樂(lè)方式缺乏競(jìng)爭(zhēng)力。人們更愿意通過(guò)手機(jī)、電腦在社交媒體短視頻平臺(tái)上發(fā)布、了解新奇的事物。但是鄂溫克族的狩獵體育文化并沒(méi)有在新媒體平臺(tái)上輸出有效內(nèi)容。在抖音短視頻平臺(tái)搜索“狩獵”的檢索結(jié)果都是電影解說(shuō),并沒(méi)有出現(xiàn)與鄂溫克族相關(guān)的檢索內(nèi)容。鄂溫克族的狩獵體育文化在大眾視野已經(jīng)淡化。
4.2、傳承手段單一
在現(xiàn)代文明沖擊下,狩獵體育文化的家庭傳承已經(jīng)消失殆盡;學(xué)校傳承作為唯一的傳承途徑,其民族特色也不夠明顯。更有學(xué)校只求政策優(yōu)惠,所謂民族學(xué)校也只是須有其名。新媒體時(shí)代,信息傳播媒介多樣化的今天,鄂溫克族的狩獵體育文化的傳承手段僅局限于以人為載體,學(xué)校教育為輸出手段,明顯是不符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
4.3、傳承文化產(chǎn)業(yè)開(kāi)發(fā)不足
文化傳承者難以靠技能產(chǎn)生經(jīng)濟(jì)效益,迫于生活壓力導(dǎo)致精神文化傳承的后盾不足。從目前形勢(shì)來(lái)看,鄂溫克民族地區(qū)的現(xiàn)代化發(fā)展加快,農(nóng)牧區(qū)的全面小康進(jìn)程推進(jìn)。狩獵體育文化作為傳統(tǒng)生產(chǎn)類(lèi)體育項(xiàng)目的競(jìng)爭(zhēng)力明顯不足;并且在鄂溫克地區(qū)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的過(guò)程中,傳統(tǒng)的狩獵項(xiàng)目沒(méi)能實(shí)現(xiàn)體育-旅游業(yè)轉(zhuǎn)型。在新媒體加速生活節(jié)奏的背景下,手機(jī)直播帶貨、短視頻產(chǎn)品推廣等方式已經(jīng)基本普及,鄂溫克族的狩獵體育文化的副產(chǎn)品(魚(yú)皮、獸皮服飾)并沒(méi)有利用好新媒體平臺(tái)提供的賣(mài)貨途徑,沒(méi)有跟上大眾消費(fèi)的需求。導(dǎo)致對(duì)民族傳統(tǒng)文化感興趣的工藝品愛(ài)好者欲求無(wú)門(mén),傳統(tǒng)手藝傳承人卻欲銷(xiāo)無(wú)路。
4.4、傳承人發(fā)揮的作用不理想
鄂溫克族的狩獵體育文化作為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承過(guò)程中傳承人的作用至關(guān)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中第三十一條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代表性項(xiàng)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的義務(wù)規(guī)定包含四個(gè)方面:對(duì)后續(xù)傳承人才的培養(yǎng);保管相關(guān)的傳承資料;參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調(diào)查;參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公益性宣傳。目前,在鄂溫克族的非遺文化傳承調(diào)查研究中,其傳承人是政府官員冠名或上了年紀(jì)的老者。在媒體傳播多樣化的今天,老一輩的傳承人很難靈活運(yùn)用網(wǎng)絡(luò)社交媒體對(duì)狩獵體育文化的傳承資料進(jìn)行數(shù)據(jù)保存,也很難在社交媒體平臺(tái)對(duì)傳承文化進(jìn)行公益性宣傳。歸根結(jié)底是傳承人審批的把關(guān)不嚴(yán)、對(duì)傳承人的培養(yǎng)制度不夠完善,沒(méi)有利用新媒體的傳播優(yōu)勢(shì),致使傳承人的宣傳任務(wù)難以進(jìn)行。
5、新媒體語(yǔ)境下為鄂溫克族狩獵體育文化傳承提供的路徑分析
根據(jù)CNNIC(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信息中心)第52 次《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絡(luò)發(fā)展?fàn)顩r統(tǒng)計(jì)報(bào)告》。截至2023 年6 月我國(guó)網(wǎng)民規(guī)模達(dá)10.79 億人,較2022 年12 月增長(zhǎng)1109 萬(wàn)人,互聯(lián)網(wǎng)普及率達(dá)76.4%。即時(shí)通信、網(wǎng)絡(luò)視頻、短視頻用戶(hù)規(guī)模分別達(dá)10.47 億人、10.44 億人和10.26 億人,用戶(hù)使用率分別為97.1%、96.8%和95.2%。數(shù)據(jù)表明,網(wǎng)絡(luò)社交媒體用戶(hù)基數(shù)大,國(guó)民覆蓋率廣,通過(guò)新媒體手段民族傳統(tǒng)狩獵體育文化進(jìn)行推廣是成本低、機(jī)會(huì)大的可行途徑。
在新媒體環(huán)境中,民族體育文化需要新的傳播途徑。通過(guò)新媒體平臺(tái)的文化傳播已經(jīng)有不少成功案例,據(jù)《甘孜日?qǐng)?bào)》2023年8 月10 日工作動(dòng)態(tài)《我州促進(jìn)文旅融合激活發(fā)展活力》顯示,甘孜文旅微博、抖音傳播力指數(shù)2 月排名全省第一,“遇見(jiàn)甘孜的甘孜尋找15 個(gè)月亮”、“被甘孜的甘孜美到了”話題頻上熱搜,道孚文旅局長(zhǎng)降澤多吉走紅網(wǎng)絡(luò),累計(jì)曝光量超1 億次。上半年全州共接待游客1614.72萬(wàn)人次,實(shí)現(xiàn)旅游綜合收入174.23億元,同比2022 年分別增長(zhǎng)53.63%和52.54%,同比2019 年分別增長(zhǎng)46.39%和43.47%。該數(shù)據(jù)表明四川甘孜州在疫情管制結(jié)束的旅游綜合收入,游客量對(duì)比疫情前都有明顯提升,說(shuō)明通過(guò)新媒體手段對(duì)民族文化進(jìn)行推廣不再停留在理論,而是真實(shí)可行的。運(yùn)用新媒體社交平臺(tái)對(duì)鄂溫克民族傳統(tǒng)狩獵體育文化進(jìn)行傳承發(fā)展是有必要的。
新媒體社交全民化的今天,網(wǎng)紅已經(jīng)成為一種職業(yè)。網(wǎng)紅多以短視頻創(chuàng)作者為主,吸引同類(lèi)粉絲群體,因?yàn)槠浞劢z群體對(duì)某一領(lǐng)域興趣的共同性,使網(wǎng)紅具有一定商業(yè)價(jià)值。微博等圖文日志類(lèi)轉(zhuǎn)載數(shù)據(jù)媒體造就了第一代網(wǎng)紅。抖音、快手為代表的短視頻社交平臺(tái)孕育了現(xiàn)在的二代網(wǎng)紅。網(wǎng)紅們?cè)谄聊焕镉涗洝⒄故咀约旱纳睿粍?chuàng)造、表演直觀的短視頻作品。以短視頻傳播為例對(duì)四川甘孜州文旅在旅游文化傳播策略與黑龍江流域鄂溫克族的現(xiàn)有條件進(jìn)行對(duì)比分析,探究鄂溫克族狩獵體育文化的開(kāi)發(fā)建議。
5.1、培養(yǎng)網(wǎng)紅代言人:帶民族體育文化走出家鄉(xiāng)
甘孜州的旅游推廣成功過(guò)程中,有兩位網(wǎng)紅功不可沒(méi)。一位是騎白馬馳騁草原的藏族青年丁真,另一位是為發(fā)展當(dāng)?shù)芈糜萎a(chǎn)業(yè)走進(jìn)屏幕的文旅局長(zhǎng)劉洪。少年丁真掀起一股模仿康巴漢子的浪潮,文旅局長(zhǎng)劉洪打造出“甘孜州100個(gè)打卡點(diǎn)”短視頻欄目,吸引網(wǎng)民身臨其境地參與“空間芭蕾”活動(dòng)。兩人的走紅方式不同,但結(jié)果都是將四川甘孜州推向了全體網(wǎng)民,讓網(wǎng)民們開(kāi)始向往甘孜旅游地,提高了甘孜州知名度,帶動(dòng)當(dāng)?shù)芈糜萎a(chǎn)業(yè)發(fā)展。甘孜州的人氣上升,走出了一條網(wǎng)紅推廣家鄉(xiāng),帶著家鄉(xiāng)文化走出去的道路。鄂溫克族的傳統(tǒng)狩獵體育文化發(fā)展也需要培養(yǎng)出不少于一位網(wǎng)紅代言人,按照甘孜經(jīng)驗(yàn),可以將“草原-少年”替換為“雪地-少女”,甘孜草原有駿馬,鄂溫克族有馴鹿。鄂溫克族在培養(yǎng)網(wǎng)紅代言人方面是由足夠的條件與素材的。將狩獵體育文化的傳承人與網(wǎng)紅代言人結(jié)合或是聯(lián)動(dòng),對(duì)宣傳狩獵文化是一條可行的途徑。
5.2、講好狩獵文化歷史:打造領(lǐng)域垂直內(nèi)容
依賴(lài)具有視覺(jué)沖擊力的畫(huà)面雖然在短期內(nèi)能夠取得比較好的傳播效果,但由于傳播內(nèi)容易于模仿、短視頻平臺(tái)用戶(hù)眾多等,在長(zhǎng)久的發(fā)展中容易出現(xiàn)同質(zhì)化嚴(yán)重和后續(xù)發(fā)力不足等問(wèn)題。因此,培養(yǎng)專(zhuān)業(yè)團(tuán)隊(duì),打造他人不易模仿的專(zhuān)業(yè)性、原創(chuàng)性?xún)?nèi)容尤為重要。狩獵體育文化的短視頻賬號(hào)可以采用不同的傳承人運(yùn)營(yíng)不同賬號(hào),不同的文化內(nèi)容分給不同傳承人,將騎馬、射箭、馴鹿、手工制作獸皮衣分給不同的傳承人進(jìn)行推廣。
5.3、打造立足鄂溫克族特色的旅游打卡地
人們對(duì)一個(gè)民族的基本認(rèn)知往往始于其獨(dú)特的文化符號(hào),地區(qū)亦然,打造地方特色十分重要。狩獵文化作為體育活動(dòng),應(yīng)著重參與性,將騎馬、射箭等項(xiàng)目納入旅游體驗(yàn)。同時(shí),可將獸皮制品或工藝品作為旅游吉祥物,借助新媒體強(qiáng)化當(dāng)?shù)靥厣糜危蛟炻糜未蚩ǖ兀瑤?dòng)旅游產(chǎn)業(yè)發(fā)展,為狩獵文化傳承打下物質(zhì)基礎(chǔ)。
5.4、契合主流價(jià)值觀發(fā)揚(yáng)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
2023 年9 月6 日至8 日,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到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哈爾濱等地,深入林場(chǎng)、鄉(xiāng)村、高校等進(jìn)行調(diào)研,前往災(zāi)后恢復(fù)重建現(xiàn)場(chǎng)看望慰問(wèn)受災(zāi)群眾,聽(tīng)取黑龍江省委和省政府工作匯報(bào)并作重要講話。深刻闡明了新時(shí)代東北地區(qū)和黑龍江全面振興的重要性。從宏觀來(lái)看,鄂溫克族的狩獵體育文化傳承正是全面振興東北地區(qū)和黑龍江地區(qū)需要的。鄂溫克族作為山林中的游獵民族,也應(yīng)該擺脫在民眾眼里山林就是落后的固化思維。借助新媒體平臺(tái)號(hào)召當(dāng)?shù)孛癖娡膮f(xié)力發(fā)展家鄉(xiāng),讓各民族同胞了解鄂溫克族的狩獵文化,傳遞促進(jìn)民族團(tuán)結(jié)的深刻主題,發(fā)揚(yáng)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
6、結(jié)束語(yǔ)
文化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發(fā)展的過(guò)程,文化轉(zhuǎn)型不是傳統(tǒng)文化的消失,而是在繼承的基礎(chǔ)上的再創(chuàng)造。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轉(zhuǎn)型是少數(shù)民族在傳統(tǒng)文化的基礎(chǔ)上適應(yīng)現(xiàn)代外部環(huán)境變化的結(jié)果。習(xí)總書(shū)記指出,各民族都對(duì)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fā)展做出了貢獻(xiàn),各民族要相互欣賞、相互學(xué)習(xí)。將漢文化等同于中華文化,忽視少數(shù)民族文化,將民族文化與中華文化區(qū)分開(kāi)來(lái),缺乏對(duì)中華文化的認(rèn)識(shí)是錯(cuò)誤的。鄂溫克人的生產(chǎn)方式和生活方式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其狩獵體育文化曾經(jīng)受到過(guò)漢族優(yōu)秀文化的沖擊。在生產(chǎn)力不夠發(fā)達(dá)的時(shí)候人們更愿意接受先進(jìn)的文化發(fā)展生產(chǎn)力,但在生產(chǎn)力發(fā)展迅速的現(xiàn)代,人們已經(jīng)不僅以生產(chǎn)力為標(biāo)準(zhǔn),傳統(tǒng)文化作為精神財(cái)富也需要得到傳承。新媒體社交平臺(tái)的文化傳播中,網(wǎng)民愿意接受在新奇文化獲得的新體驗(yàn),這也為傳承鄂溫克族的狩獵體育文化提供條件。新媒體語(yǔ)境下傳承發(fā)展鄂溫克族狩獵體育文化既是振興了北方地區(qū)也符合發(fā)揚(yáng)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