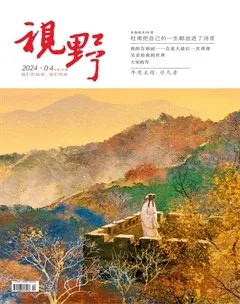杜甫到底牛在哪里

最近有些評論特別有意思,有一些聲音說:杜甫不行。主要是說:杜甫沒有才華,沒有文采,還不夠正能量,等等。附和的人還不少。
確實很多人有疑惑:總把杜甫說得水平那么高、那么偉大,可是他的詩到底好在哪里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龐大的工作,足夠寫幾大本書了。今天就從最簡單的角度來聊一聊杜甫牛在哪里。
詩人是什么?借用今天網絡上的話來說,其實就是“嘴替”。
所謂嘴替,就是替你說話,替你表達,替你發(fā)泄,替你把自己講不出來的話給完美地講出來。杜甫,其實不過也是一個“嘴替”而已。
嘴替和嘴替之間,是分層次的,是有水平差距的。最偉大的嘴替會有三個使命:世人的嘴替,文學的嘴替,時代的嘴替。
首先,杜甫就是世人的嘴替。
世人是什么?就是蒼生。蒼生是數以億萬計的,他們每個人的情況處境是不一樣的,有老人,有少年,有孩子,有母親,有士卒,有縉紳,有餓殍。蒼生的情緒狀態(tài)也是不一樣的,有歡喜,有悲傷,有憂懼,有驚怖,有希冀,有絕望。
杜甫是蒼生的最強嘴替,沒有之一。他可以替一切人的一切情緒來表達。比如人類歷史上一種常見的情緒:戰(zhàn)亂之中思念親人,杜甫十個字給你嘴替了: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你品一品這十個字。現在世界上也不消停,一些地方在打仗,人民流離失所。你倘若問問士兵們、難民們,不管他們是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翻譯一下,問他們能不能懂什么是“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他們一定秒懂,并且會熱淚盈眶。這就叫做嘴替。
又比如一種常見情緒:老友久別重逢后的歡喜,杜甫二十個字給你嘴替了: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
還能嘴替得更到位和動人嗎?很難了吧。
又如極度的絕望,那種哀到最深沉處的絕望,杜甫二十個字給你嘴替了: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絕望的人,莫哭了,就算你眼睛哭干,哭成黑洞,哭得見了骨頭,天地一樣無情,沒有憐憫,沒有救贖。二十個字,把絕望這種情緒寫到極致。
人類的所有情感,從至極的喜到至極的悲,是有一個區(qū)間的,比方說有100分。不同的詩人所能表現的區(qū)間是不一樣的。李白大概能表現95分,李煜也許能表現90分,都是不世出的文藝之神。柳永、秦觀等大概能表現75到80分,也都是非常優(yōu)秀的選手。
杜甫呢?他能表現全部的100分。所以他是最卓絕的蒼生的嘴替,是大能。
說了世人的嘴替,下面說第二點:文學的嘴替。
文學是一種專業(yè)技巧。作為一個大詩人,在評價你歷史地位的時候,肯定要面臨這樣一個專業(yè)審視:你把文學的專業(yè)技巧拓展了沒有?你把文學的表現力和可能性提升了沒有?
為了方便大家懂,舉一個小例子——曹丕,他不但是皇帝,也是詩人,是所謂“三曹”之一。按理說他的成就和才華趕不上他爹曹操,也趕不上他弟弟曹植。
那他在三曹里算啥?吊車尾嗎?然而咱們別的不說,只說曹丕的一樣貢獻,他搞出了一個《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注意到沒有,這是七言詩。而在那個時代之前,大家搞的主要都是五言詩,成熟的也是五言詩,曹操、曹植主要都是五言詩。曹丕卻搞出了成熟的七言詩。這就是對文學的開拓之功,是永遠無法抹煞的開拓之功。
那么杜甫呢?他對中國詩歌的形式、技巧、題材、法則、容量、表現力,有多大的開拓之功?四個字吧,亙古一人。
網上那些說“杜甫不行”的,他們懂也好,不懂也罷,知道這四個字就好了,亙古一人。他這方面的功績太輝煌了,幾句話列舉不完。
好比說律詩吧,杜甫是律詩的最終定型者和大成者。
宋人說,五七言律詩有“一祖三宗”,三宗的歸屬可以爭論一下,一祖沒有太多好說的,就是杜甫。你要是選四五個祖,還可以算到杜甫之前的宋之問沈佺期杜審言頭上,都是祖。但如果單提“一祖”,那不用爭競,就是杜甫。之前看到網上討論,大家很熱烈地討論杜甫的某首詩、某句詩是否“符合律法”,討論很熱烈。這很好玩,因為,這個討論恰恰有點搞反了。因為杜甫就是規(guī)范本范,就是律法本法。我這樣說,大家明白了沒有?說句不嚴格的,寫詩的時候,某一處的律法,杜甫破了,那么規(guī)范就是可以破;杜甫救了,那么規(guī)范就是可以救,懂了沒?好比打籃球的跳投,熱烈討論喬丹的跳投標準不標準,不是不行,可問題是某種意義上,喬丹就是跳投的標準本準。
唐朝在杜甫之后,所有的一流大詩人,基本沒有一個例外的,在形式、題材、技巧上都要學杜甫。因為他籠罩了一切。
我在以前《讀唐詩》書里寫過一個想象的故事,叫“杜甫一道傳三友”,說杜甫傳道,后輩韓愈得了一個字——“骨”,白居易得了一個字——“真”,李商隱得了一個字——“情”。你再不服,這種傳承也明明擺著,沒什么好辯的。莫礪鋒老師一個比喻說得很明白:杜甫就是長江上最大的水閘,上游所有水都聚到他那里去,下游所有波濤都從他這里泄出來。就好比一個專業(yè)領域里,后來人用的多數的技法,都和他有關,都是他開發(fā)的、打磨的、創(chuàng)造定型的。
不多啰嗦,下面簡單說第三點:時代的嘴替。
杜甫不但是世人的嘴替、文學的嘴替,還是時代的嘴替。這個也是老難了。你不妨把時代想象成一個人。這個人他自己是不會說話的,因為時代是不會說話的,時代永遠是沉默的,必須有人幫他說。
在公元8世紀的那個時代,那波瀾起伏、地崩山催的數十年間,發(fā)生了什么?經歷了什么?動蕩著什么?孕育著什么?糾結著什么?不安著什么?奔騰著什么?幻滅了什么?時代自己是不會說話的。那么誰為時代說出來?杜甫。
唐朝之前的一個大時代是南北朝。南北朝的詩總體不太好。除了陶淵明等寥寥個別強人外,都不太好。為什么不太好?只說一點:你把南北朝所有詩人寫的所有的詩加在一起,打個包,你能看出來南北朝的中國人經歷了什么嗎?能看出來那個時代發(fā)生了什么嗎?看不出來。所以那個時期的詩歌,還不配做時代的嘴替,沒有足夠的資格站在時代的面前。
但是唐朝僅一個杜甫,就用他一個人的力量,昂然站在了時代的面前。《北征》《壯游》《憶昔》《兵車行》《麗人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洗兵馬》……這些恢弘的詩篇,別說這么多首了,哪怕其中有一首能夠留下來,都是時代的幸事。杜甫卻用一己之力,用“疏布纏枯骨”之軀,給我們留下了這么多的宏偉詩章,完全了時代最珍貴的記錄。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戰(zhàn)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己。
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
野曠天清無戰(zhàn)聲,四萬義軍同日死。
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在祖國遼闊的土地上,在億萬生民之間,從京兆到洛陽,從秦州到蜀州,從泰山到汶水,從夔州到洞庭,那個時代的一個個正面、側面、高光、暗谷,各色人等的嗚咽、號泣,希望的燃燒和泯滅,都有杜甫的詩筆在。無論是耳目驚駭,還是飲恨吞聲;無論是地動山搖,還是向隅而泣,都有杜甫的詩筆在。時代有多大,他就有多大。時代的溝壑有多深,他詩就有多深。
這就是我說的三個偉大的嘴替:蒼生的嘴替,文學的嘴替,時代的嘴替。
最后給大家聊一個事情——文采。
簡單說幾句。我明白,許多人憑著主觀印象,覺得杜甫好像“沒有什么文采”。就好像網上人隨口說,杜甫文采不太行啊!這種誤會,是很深的。
因為不了解,就會有誤會,誤以為偉大文學家的使命是秀一下“文采”,搞幾個“金句”。
好比前些天,一個朋友說:“李白寫詩沒什么,就是像某地方人一樣會吹牛逼而已。”這就是典型的因為不了解造成的誤會。他印象里李白只有類似“白發(fā)三千丈”,所以說李白只會吹牛逼。請問,“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吹牛逼在哪里?同樣的,認為杜甫沒有文采,也是一種不了解造成的誤會。
他們不明白,一個人的才華太大了、造詣太高了,“文采”就是個小事了,是一個比較低的標準了。就類似很多人覺得好像金庸也沒文采一樣。說說杜甫的“文采”。
先說一個概念——分量。在所有存世的五萬首唐詩里,分量最重的五個字是哪五個?我來說一句吧:國破山河在。這五個字,一字有萬鈞之力,重如日月山河。
再說壯美。再隨便引兩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是不是壯絕千載?
再說思念: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xiāng)明。
再說蒼茫:無風云出塞,不夜月臨關。
說沉郁: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說絢爛: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說志向: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說創(chuàng)作: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說遺憾: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說惆悵: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
最后說說華麗,很多人誤以為老杜不能華麗,卻不知道老杜影響晚唐華麗詩風的偉績豐功。
所謂“雜徐庾之流麗”豈是吹的?《秋興八首》隨便來一首吧,看看老杜可以多華麗: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
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
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所以不是說什么杜甫有沒有文采,而是你所謂的“文采”“金句”,對一個文學巨匠來說,這個標準太小兒科了。人家隨口一句“人生七十古來稀”,都是我們民族流傳至今的俗語。隨口一句“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都讓千百年來無數癡兒女悵惘。
杜甫就是這樣的,無論你從哪一個角度去褒獎他,才力也好,技法也好,道德也好,文采也好,憂國憂民也好,都會覺得太小,無法籠罩他的功業(yè)。
當然了,永遠會有人像網上一樣說,什么杜甫的《登高》明顯不如崔顥的《黃鶴樓》,還煞有介事分析一番。嗯嗯,杜甫的《登高》不如崔顥的《黃鶴樓》,然后更不如“樹深時見鹿,海藍時見鯨”,還不如“誰執(zhí)我之手,斂我半世癲狂”,又不如“愿有歲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頭”。
最后統(tǒng)統(tǒng)都不如春風十里不如你。
(摘自微信公眾號“六神磊磊讀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