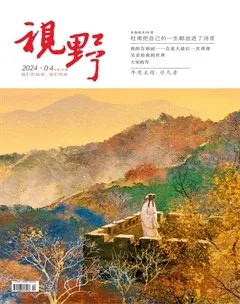杜甫的形象
西川

大家心里都有一個杜甫,都能背一些杜甫的詩,在這種情況下要將杜甫講出點新意有些困難,所以我就想到了“杜甫的形象”這個題目。杜甫的早年形象說不上,他的詩歌到現在流傳下來的有1400多首,90%以上的詩歌都是他40歲以后寫的,他早期的東西都沒了。所以談杜甫的形象,其實談的是杜甫晚期的形象。
美國有一位學者叫陸敬思,他說杜甫是中國古今詩人的“大家長”。——每個家里都有家長,中國詩人的大家長就是杜甫。這個說法很精彩,但也讓我們討論杜甫有了難度。今天我選的這個角度相對容易一點,講杜甫的形象。其他角度三兩句話沒法說清楚。我會談到杜甫的生平際遇、杜甫的趣味、杜甫的現實感,這些話題都跟杜甫作為一個詩人的形象有關系。
杜甫的詩被稱作“詩史”。那么歷史對于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的作用和意義,相當于神話對希臘人的作用和意義。中國的文學里很多東西都跟歷史有關系,二者很難分開。杜甫的詩歌滿足了歷史的要求,我們習慣于把詩和史聯系在一起,這使他成為了一個如此重要的詩人。這種情況在當代詩歌里沒有,當代詩歌基本上已經不負擔述史的作用。與此同時我們又受到外國文學的影響,包括浪漫主義、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影響,我們大多數人寫的基本上是抒情觀念之下的詩歌。
中國古代的詩人中,以現在的標準看,很長壽的幾乎沒有。杜甫在戰亂中活到58歲,公元712年到770年。杜甫的一生可以分成幾個階段。
首先是早年讀書漫游的階段,持續到杜甫30多歲。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他在洛陽遇到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后來他們倆又遇到高適。那時杜甫33歲,李白比杜甫大11歲,是44歲,高適比杜甫大6歲,是39歲。
對于李杜的關系,郭沫若寫過《李白與杜甫》,聞一多也提到過。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猜測和解讀,比如說他們覺得杜甫對李白那么好,李白卻拿杜甫開涮(《戲贈杜甫》:“飯顆山頭逢杜甫”,可能是偽作)。也有人猜測兩個人關系很好,兩人旅行的時候會蓋一條被子(杜甫《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白給杜甫寫過兩首詩,而杜甫給李白寫了很多的詩,主要的交流就是當年在一塊兒游歷。先是在梁、宋這塊地方,后來兩個人又一塊兒到了蘄州,分手之后再次見面的時候在東魯。
無論怎樣,李白應該對杜甫產生了不小的影響。杜甫在李白身上看到了一個奇觀。其實杜甫本身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奇觀,只不過更多的時候我們把他放在儒家的話語里。
頭兩天我在江西南昌,有一個寫古體詩的學生還跟我講,他分析有些古代詩人的詩不合平仄。我說所有合章法、合規矩、合平仄的寫法,都是小詩人的路數,對大詩人你沒法這么判斷。宋代的黃庭堅,說自己的書法是“老夫之書本無法”。也就是說,邁過很多的門檻兒之后,這些大詩人、大藝術家內心就開始有一種自由度,開始搞破壞。很多人是跟著章法走的,但大詩人總有破壞章法的能力,破壞工作有時候就能呈現為奇觀,而這也是建設。
在李白身上我們看到了這一點,在杜甫身上我們也能看到這一點。別人的詩很多四行一換韻,杜甫可以八行一換韻,杜甫就敢這么干。拗體詩,在別人那兒是缺點,到杜甫這兒就是精彩。對他來講這是自由,但對于整個詩歌史來講,他是在給詩歌立新的章法。所以說,杜甫也是一個奇觀。《新唐書·杜甫傳》說:“甫曠放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他后來在長安上玄宗三大禮賦時自謂:“沈郁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皋可企及也。”——這狂勁兒比李白也不差。
杜甫人生的第二階段是困居長安的時期,大概是30多歲到40歲;第三個時期是為官時期,大概是從他44歲到48歲,時間很短,正好是安史之亂的時間。
陳寅恪說安史之亂是中國古代史的分水嶺,之前和之后的中國,幾乎像兩個中國。日本大漢學家內藤湖南認為,從安史之亂開始,中國進入了唐宋變革期,跨度從中唐一直到宋,思孟系統、傳道系統的儒家在中國的影響開始變大,一直持續到明清、到今天。籠統地說起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我們往往會忽略這些變化。我們漢族人填表寫自己的民族時會填“漢”,可按照傅斯年的講法,實際上漢朝的漢族到六朝結束以后就沒有了。很難說今天的我們跟漢朝的漢族完全是同一個“漢族”,可能存在當時的基因,但已經有很大的變化了。
杜甫趕上了安史之亂,目睹了戰爭慘烈的情狀。肅宗朝宰相房琯在陳陶斜和青坂打了兩場大敗仗,讓唐軍損失慘重。杜甫曾經在《悲陳陶》里有一句 “四萬義軍同日死”。部隊大概有四萬多人,四萬義軍一天全死了,太可怕了。杜甫跟房琯兩個人是老朋友,他為此要疏救房琯,結果一下子得罪了皇上,就回家省親去了。后又隨肅宗還長安,然后被貶,然后棄官,于是杜甫離開朝廷,開始進入漂泊的生涯,也就是他人生的最后時期,大概是從48歲到58歲,十年的時間。我們所能知道的杜甫的形象,主要是來自于他的漂泊時期。他先是向西漂泊,到達天水、同谷一帶,后來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筑起草堂,后又離開成都在湖南湖北這一帶漂泊,直到死去。
進入杜甫西南漂泊的時期,就進入了杜甫晚年的形象。杜甫晚年的形象,可以分為精神形象、肉體形象兩方面。
首先是精神形象。杜甫晚年很潦倒,盡管他得到了高適、嚴武等人的幫助。他會毫不猶豫地請求高適的幫助。杜甫48歲時寫有一首詩,《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管高適要吃的:“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你什么時候來幫我啊。現在我們不好意思這樣說出口,但當時他們朋友之間可以這么干。
杜甫說自己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旅夜書懷》,永泰元年765年,53歲)。雖然有人幫助過他,但他內心是非常孤獨的。他在大歷四年,769年,57歲時寫過一首詩叫《南征》:“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杜甫一生的朋友其實都是很高大上的,李邕、李白、高適、岑參、裴迪、元結,打過交道的還有王維、顏真卿等。杜甫也認識一群畫家,包括被玄宗皇帝稱贊為“詩書畫三絕”的鄭虔、韋應物的叔父韋偃、曹操的后代曹霸等。韋偃還曾在杜甫草堂的墻上畫過畫。這都是赫赫有名、彪炳千秋的詩人、藝術家。所以杜甫的朋友圈按說是很豪華的,盡管他自己的官不大。可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杜甫還是覺得“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這可以看出他的精神面貌。
熟讀杜詩的人肯定會注意到,在《春望》這首詩里,杜甫寫道,“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這首詩寫在肅宗至德二年即757年春,杜甫才45歲——45歲都“渾欲不勝簪”了。杜甫還有一組詩叫《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肅宗乾元二年,759年,47歲),里面有一句,“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發垂過耳”,古人把頭發都往上盤,他是垂過耳,很狼狽的樣子。在《復陰》這首詩里,他說:“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牙已經掉得差不多了,左耳聾,聽不見了。這首詩沒有明確的紀年,不知道杜甫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耳聾的,大概開始在他寓居夔州這段時間,是代宗大歷元年,766年,這一年杜甫54歲。也就是說,在他去世之前四五年,左邊耳朵就聾了,牙齒也落了很多。而在54歲這一年上,杜甫寫下他偉大的詩篇《秋興八首》。
杜甫一直多病,55歲,他“衰顏更覓藜床坐,緩步仍須竹杖扶” (《寒雨朝行視園樹》,代宗大歷二年,767年),這一年他寫下《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他的《清明二首》,寫在大歷四年即769年,他57歲,去世之前一年。“此身漂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系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就是已經半身不遂了,右胳膊抬不起來了,只能伏在枕上,抬起左手在空中寫劃。他的左耳還是聾的,牙也掉了很多,頭發幾乎也沒了,剩下的就是白發。這時杜甫一家居無定所,住在船上,真是很凄慘——我們民族最偉大的詩人!這是晚年杜甫的身體情況,也是他肉體的形象。
這樣的身體情況,與殘酷的國家戰亂疊合起來,導致杜甫一天到晚忙活一件事,就是哭。至德二年(757年),杜甫45歲的時候,被安祿山的軍隊抓住了,這時候他寫下非常有名的一首詩叫《哀江頭》。他說:“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少陵野老吞聲哭”的時候實際上杜甫只有45歲,他就把自己叫“野老”。古人好像一過40歲就覺得自己老了。
后來他遭遇顛簸,到處亂跑,于代宗廣德元年即763年寫下《天邊行》。他說:“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在江邊上,一個人就在那兒哭。大歷五年,杜甫58歲,快要去世的時候,寫了一首詩叫做《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他說:“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這是他臨死那年說的。在顛沛流離、流離失所的情況下,怎么可能不哭呢?“身老不禁愁”,讓我們對杜甫當時的處境有了更深的體會。
今天我們說杜甫是“現實主義者”。在中國,我們接受的更多的是積極浪漫主義一派。說起李白是“浪漫主義”,就強調他“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這一面——這表明了他對于唐朝權貴的反抗。但與此同時,我們可能忘了李白還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一面,那時候皇上召他入宮,他非常高興。——只是強調李白反抗的、不同流合污的那一面,是不夠的。同樣,只強調杜甫是現實主義詩人也是不夠的。如今,我們已經獲得了各種文學批評的方法,這時候我們看古代文學,就應該不囿于既有觀念,進入到更多的歷史細節,進入歷史的此時此刻。
那么要談論杜甫的此時此刻就不得不看一看安史之亂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朝的人口峰值是安史之亂之前的754年,正逢開元盛世,中國人口達到5300萬或者還多一些。安史之亂大概有七年時間(755-762年),等到那時朝廷重新開始統計人口,發現人口至少減少了一半。死了那么多人,這不是簡簡單單說浪漫主義或者是現實主義能對付得了的。多少人的去世才把杜甫推到現實主義的位置?所以討論杜甫的現實主義,一定要將杜甫的詩歌和當時死亡的人數掛鉤。
“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陳陶》,至德元年,756年)唐軍四萬人嘩啦就沒了。廣德二年,764年,他寫過一首詩叫《釋悶》:“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尸縱橫。”烽火照著夜晚,死尸狼藉,這不是杜甫的想象,一定是他見到的情況。永泰元年,765年,杜甫寫過《三絕句》,其中第二首很有名:“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自說二女嚙臂時,回頭卻向秦云哭。”二十一家人一起逃難進入蜀地,只有一個人出了駱谷,全死掉了。這人遇到杜甫,回想起逃難經歷,“自說二女嚙臂時”,嚙臂就是咬自己手臂咬到出血。古人如果知道這是生離死別,就要“嚙臂而別”。想起這些慘痛的經歷,講述人面向著秦地的云彩,號啕大哭。這些東西杜甫全都碰上了,這構成了他強烈的現實感。
大歷元年秋,766年,杜甫在《驅豎子摘蒼耳》這首詩里說到:“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大歷元年他還寫過一首詩叫做《白帝》:“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只有百家存。”——基本上活人只剩下十分之一了。從杜甫的詩里可以感覺到一個最醒目的話題,就是戰亂流徙中死了多少人。與唐朝其他詩人相比,杜甫直面了這些東西,其他人少有做到。所以杜甫孤零零地成為了大詩人。——當然他成為大詩人也是因為他“晚節漸于詩律細”——而這一點又是他迎著戰亂,在逃亡、饑餓和漂泊中,面向死亡,而做到的。
杜甫在那樣一種戰亂的情況下,遇到那么多的艱辛、別離、饑餓(《彭衙行》“癡女饑咬我”)、死亡,可以說他被激發成一位如此獨到的詩人。如果我們只是討論杜甫的現實主義,而不能把現實主義討論到杜甫的此時此地、此時此刻這個點上,討論到杜甫本人的現實感這個點上,我們實際上還不能切身感覺到杜甫詩歌的力量,我們讀杜甫詩歌的時候就不會起雞皮疙瘩。
在《唐詩的讀法》里我特別強調回到唐詩的現場,切身感受唐代詩人的寫作觀念。杜甫的詩歌處理的是他的此時此刻和此地。但他所有的此時此刻,又跟百年之前或者百年之后勾連在一起,他喜歡以“百年”作為時間跨度(“百年多病獨登臺”)。而他的此地此景,又常跟千里之外、萬里之外勾連在一起。所以說,杜甫的時空感是非常復雜的。
他的詩歌中包含了三種時間。一種是自然時間,一種是個人時間,一種是歷史時間。此時此刻的有血有肉的個人時間,與四季輪回的自然時間,每個詩人都有。但杜甫的歷史時間感,在其他詩人身上是很少見的。我們發現杜甫經常會使用到一個字,“萬”。比如 “萬里悲秋常作客”。這個字(詞)在西方語言里沒有,西方語言一萬就是ten thousand(十千)。即使是一個數詞,也能說明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我們看問題的單位是萬,人家看問題的單位可能是千。這是個有趣的現象。
杜甫的時空感,是以蒼茫的“萬”字為基本單位的:
三年笛里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洗兵行》)
我生何為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
(《登高》)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其六》)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登樓》)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詠懷古跡五首》)
十年戎馬暗萬國,異域賓客老孤城。
(《愁》)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
(《蠶谷行》)
這是我從杜甫的詩里找出來的跟“萬”字有關的詩句。我們于此可以感覺到杜甫的時空感。又是此時、此刻、此地,又是極其廣闊,無邊無際。也就是有限和無限的交融,此時此刻和古往今來,和天下萬國之間的關系。所以,只強調杜甫的此時此刻、他的現實感,還不足以討論杜甫,必須是把這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杜甫為什么是集大成者?為什么高于別的詩人?就是因為他的詩里充滿了辯證法,陰和陽的辯證法、古往和今來的辯證法、此地和萬里之外的辯證法,還有言志和載道的辯證法,等等。
討論杜甫的平仄,討論杜甫的用韻,討論杜甫的語詞、用典、對仗、拗體、雄渾、巧妙、省儉、鋪排,那只是欣賞型的閱讀。這種閱讀當然是必要的,但我不滿足于這樣來讀古詩。我希望我們讀詩的時候,能回到那個時代,能起一身雞皮疙瘩。這時候,我們就不是在“欣賞”杜甫這樣一位偉大的詩人,而是在“體驗”一位偉大的詩人。
杜甫作為一位偉大的詩人,他的藝術趣味究竟如何?這從他跟視覺藝術的關系就能感受出來。
我在書里用了一個拓片作為插圖,是《嚴公九日南山詩》,有人說這是杜甫唯一存世字跡,在四川的一個石窟里發現的,上面寫著“乾元二年杜甫書”。但究竟這是不是杜甫的文字書寫我不敢打包票。啟功先生判斷這是宋人的仿造。如果是宋人的仿造,那仿造者有所本嗎?那個碑的形制——中間有一個窟窿——應該是古制。類似的形制在漢代較常見,例如東漢《袁安碑》。
《嚴公九日南山詩》的字形偏瘦,我猜應該接近于杜甫的書寫風格。杜甫曾經稱贊過薛稷的書法,而薛稷《信行禪師碑》是偏瘦的初唐書風。再看為杜甫所贊慕的李邕的書法,也是偏瘦。見其《云麾將軍碑》。杜甫晚年(大歷元年,766年)為其外甥李潮作《李潮八分小篆歌》曰:“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有趣的問題來了:他喜歡顏真卿的字嗎?顏真卿審訊過杜甫,在杜甫因疏救房琯而得罪了肅宗皇帝以后。
杜甫的藝術趣味看來偏瘦。玄宗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正值30歲的杜甫寫有一首詩叫《房兵曹胡馬》,“胡馬大宛名,鋒棱瘦骨成”。杜甫從年輕時代就對瘦馬感興趣。他后來寫《瘦馬行》,看來“詩”出有因,他對瘦馬很有感覺。
杜甫在寓居成都時曾經給三國高貴鄉公曹髦的后代,也就是曹操的后代、畫家曹霸寫過一首中國美術史繞不過去的詩《丹青引贈曹將軍霸》。詩中說:“弟子韓干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干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韓干是唐代畫馬高手,早年從曹霸學過畫。他的畫跡或者畫跡摹本現在還能看到。從現藏于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的《韓干照夜白》和現藏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韓干牧馬圖》看,韓干的馬畫得的確肥壯,馬屁股渾圓。這是杜甫不喜歡的。他認為這樣的馬沒畫出骨頭。
現在,我們慢慢建立起杜甫的形象了。從他“天地一沙鷗”的精神狀態,到他衰朽的外貌,從他目睹生靈涂炭的現實感,到他有限與無限相結合的時空觀,以及他偏瘦的美學趣味,我們大概知道杜甫這個不到60歲的“老頭”長什么樣子了。這是一個看上去悲苦的形象。當然,杜甫也有他稍微高興的時候。他也寫過有意思的詩,像《縛雞行》《驅豎子摘蒼耳》,都寫得比較爛漫。
美國當代有一位大詩人叫雷克斯羅斯,他翻譯過中國很多詩,也翻譯過李清照的詩。他對杜甫有一個看法我覺得特別好,我用它來結束今天跟大家的談話。
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他說:“我的詩歌毫無疑問的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非常崇高的評價,這樣崇高的詩人值得我們想盡一切辦法向他靠近。在靠近的努力當中,當代通行的很多關于杜甫的陳詞濫調就被打碎了。
(摘自微信公眾號“十月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