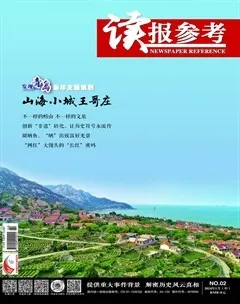古人點菜,按單數還是按雙數?
現代人請客,點菜一般是雙數,至少兩個菜,多則四個菜、六個菜、八個菜、十個菜、十二個菜……很少有人點三個菜、五個菜或者七個菜。有人說,中國人講究“好事成雙”,所以點菜必須按雙數,只有給死者擺供品時才按單數,這是“自古以來的傳統”。這個說法真的符合歷史嗎?古代中國真的有按雙數點菜的傳統嗎?真實情況可能恰恰相反。
在宋朝,菜肴和果盤通常是單數
按宋人筆記《避暑錄話》上卷記載,司馬光在洛陽撰寫《資治通鑒》時,經常跟幾位老友聚餐,他們點幾個菜呢?“果實不過三品,肴饌不過五品,酒則無算。”果盤不能超過三個,菜碟不能超過五個,酒不限制,想喝多少就整多少。請注意,“不能超過”就是小于等于。果盤不能超過三個,意思是最多點三個;菜碟不能超過五個,意思是最多點五個。這說明,司馬光點菜最多的時候,果盤一定是單數(三個),菜碟也一定是單數(五個)。
司馬光本人寫過一篇《訓儉示康》,教育他的養子司馬康要節儉,他舉了個例子:“吾記天圣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多不過七行。酤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柿,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說是宋仁宗天圣年間(1023-1032年),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在群牧司(購買、飼養、管理全國戰馬的機構,王安石變法以前隸屬于樞密院)當判官,請客時一般會上酒,但敬酒數量有限制,一頓飯吃下來,少則敬酒三杯,多則敬酒五杯、七杯,最多不超過七杯。果盤和菜肴都是叫外賣,其中果盤只用梨子、栗子、大棗、柿子等普通水果,菜肴只用肉干、醬菜、菜湯等便宜菜肴,餐具只用瓷器和漆器,不用奢華的金銀器。當時士大夫請客都是這個樣子,沒有人說司馬池寒酸。
根據司馬光的描述,他父親司馬池以及與司馬池同時代的其他士大夫在請客吃飯時,敬酒數量是按單數。其實,不僅僅是敬酒按單數,上菜同樣是按單數,因為司馬光原話中的“或三行,或五行,多不過七行”,暗含著宋朝宴席上的另一種傳統——以菜行酒。宋朝正規宴席的行酒儀式,行酒就是敬酒,主人向客人敬酒,敬一次叫“一行”,敬三次叫“三行”,敬五次是“五行”……當時敬酒的節奏極慢,而且是每敬一杯酒都至少要換一道菜,這道菜吃完,再敬下一杯酒,同時換下一道菜。“或三行,或五行,多不過七行。”對這句話的完整理解應該是:或敬三杯酒,換三道菜;或敬五杯酒,換五道菜;最多敬七杯酒,最多上七道菜。換句話說,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請客,同樣是按單數上菜。
陸游壯年時在杭州做官,當過一段時間“膳部郎中”,隸屬于禮部,平常負責監督御廚房的膳食,當外國使臣到訪時,又要負責國賓宴席的飲食安全。有一年,金國使臣抵達杭州,南宋朝廷在集英殿設宴,陸游將那場宴席的菜單和敬酒次序記錄下來,寫進《老學庵筆記》一書。南宋朝廷總共敬金國使臣多少杯酒呢?九杯。按照以菜行酒,每敬一杯酒都要換新菜的規矩,總共上了多少道菜呢?總共十五道菜,仍然是單數。
陸游年輕時,宋高宗曾經去大將張俊府邸作客,張俊設下宴席,全部菜單在宋朝飲食文獻《玉食批》和南宋風俗寶典《武林舊事》中均有記載,其中最關鍵的五個字:“下酒十五盞。”這五個字意思是說,張俊前前后后向宋高宗敬了十五杯酒,同時換了十五回下酒菜。另外,《玉食批》還說,張俊在宴席之后給宋高宗隨行官員上的果盤數量:“每份時果五盤。”為每人上了五個果盤,仍舊是單數。
現在可以小結一下:在宋朝,從大將招待皇帝的宴席,到朝廷招待外賓的宴席,再到士大夫待客的宴席,敬酒數量通常是單數,菜肴和果盤也通常是單數。
當時的風俗,“男忌雙,女忌只”
為什么按單數呢?宋朝皇族子弟趙與時的著作《賓退錄》也許能給我們提供答案。趙與時說:“今世男子初入學,多用五歲或七歲,蓋俗有‘男忌雙,女忌只之說,以至冠笄皆然。”宋朝男孩上學,大多是五歲入學,或者七歲入學,很少有人在六歲、八歲入學,當時世俗認為“男忌雙,女忌只”——雙數對男人不吉利,單數對女人不吉利。因為這個緣故,《周禮》中男生二十歲成人禮、女生十五歲成人禮的規定在宋朝也失效了。宋朝男生寧可在十九歲或者二十一歲時舉行成人禮,為的是避開“二十”這個雙數;女生寧可在十四歲或者十六歲時舉行成人禮,為的是避開“十五”這個單數。
那么,宋朝世俗為何會有“男忌雙,女忌只”的觀念呢?趙與時沒有深究,我們只能推測這與“雙數為陰,單數為陽”的陰陽五行傳統有關。男人是陽性,所以只能配單數;女人是陰性,所以只能配雙數。不過,趙與時注意到,男忌雙數的傳統由來已久,早在南北朝時就已經存在,他還舉了《北齊書》里的一個例證:北齊大臣李渾的弟弟李繪自幼聰明好學,六歲時就吵著要上學,家長堅決反對,認為六歲是雙數,不該是男生的上學年齡,李繪便偷著學,很快就把漢朝人編寫的兒童識字啟蒙手冊《急就篇》學完了。
再看五代十國時期,文官牛希濟著有《貢士論》,論述晚唐及五代的科舉風氣:“名第之中,以只數為上,賤其雙數。”科舉放榜,被取中的考生在一塊兒討論名次,認為排在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等單數名次比較吉利,而排在第二、第四、第六等雙數名次比較倒霉。
單數吉利,雙數不吉利,這種觀念至少在南北朝時已經誕生,至少在五代時期已經盛行。到了南宋時期,連一些醫藥學家都追求單數。南宋醫生聞人規《痘瘡論》是這么寫的:“疔瘡、惡腫,普濟方,用荔枝三個或五個,不用雙數。”治療腫瘡可用荔枝,但只能用三顆或者五顆,不能用四顆或者六顆。
從南北朝和五代十國到宋朝,都以單數為吉利,那么宋朝以后呢?筆者在明朝崇禎年間編訂的《長沙府志》讀到一句記載:“童子入塾,多用七歲、五歲,俗云忌雙。”明朝長沙的小朋友通常在七歲或者五歲入學,因為當地忌諱雙數。
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年,有兩本教朝鮮人學漢語的教材,一本叫《老乞大》,一本叫《樸通事》。其中,《樸通事》上卷有一段請客吃飯的對話:“第一道爊羊蒸卷,第二道金銀豆腐湯,第三道鮮筍燈籠湯,第四道三鮮湯,第五道五軟三下鍋,第六道雞脆芙蓉湯,都著些細料物,第七道粉湯饅頭,官人們待散也。”一桌飯上了七道羹湯和點心,是單數。《老乞大》下卷也有請客吃飯的對話:“咱們做漢兒茶飯著,頭一道團攛湯,第二道鮮魚湯,第三道雞湯,第四道五軟三下鍋,第五道干按酒,第六道灌肺、蒸餅、脫脫麻食,第七道粉湯饅頭打散。”這桌宴席有炒菜(“干按酒”即炒菜),有羹湯,有主食,具體數量不詳,但上菜次數依舊是單數。
18世紀的朝鮮有一位儒生黃德吉,漢學功底深厚,精通儒家禮儀,當時朝鮮人已經流行按雙數敬酒、按雙數上菜,他表示反對:“侑食必以三飯,奉酒必以三獻。三,陽數也。而更有添盞之節,其義何據?”佐餐一定要用三道菜,敬酒必須要用三杯酒,因為三是陽數,現在非要添成雙數,理論根據在哪里呢?
筆者覺得,黃德吉過于較真了,傳統是被人發明的,習俗是不斷演化的,既沒必要固守傳統,也沒必要跟習俗過不去。習俗認為雙數吉利,當然沒有理論根據,可是宋朝前后的古人認為單數吉利,在邏輯上也未必顛撲不破。更科學的選擇或許應該是“從眾而不盲從”——以后不管誰請咱吃飯,如果堅持按雙數點菜,咱千萬不要反對;而如果主人點成了單數,您也可以由衷地說,按單數點菜曾經是古代中國延續很久的傳統。
(摘自《北京青年報》李開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