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靈魂的攝像機
劉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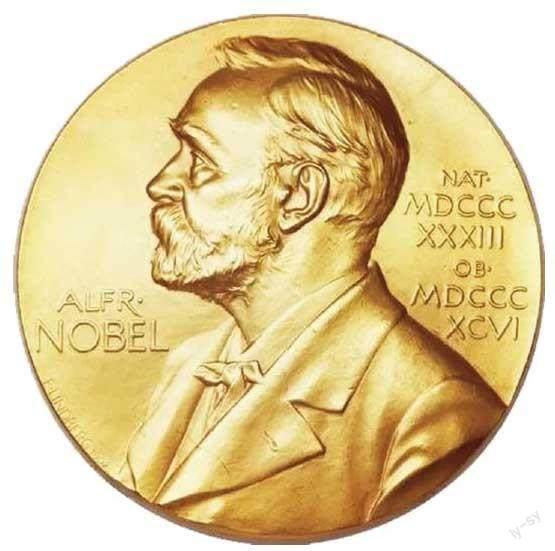

白俄羅斯著名女作家,斯韋特蘭娜·亞歷山德羅夫娜·阿列克謝耶維奇(下文稱為阿列克謝耶維奇)畢業(yè)于白俄羅斯國立大學新聞系(現(xiàn)明斯克大學新聞學系),畢業(yè)后做過老師、記者,這些職業(yè)經(jīng)歷讓阿列克謝耶維奇的寫作風格更加紀實。
在她的代表作《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于死亡還是愛情》這部非虛構作品中,阿列克謝耶維奇采訪了上百位在切爾諾貝利爆炸事件中的親歷者、幸存者,最終以“口述史”的方式整理成書。這本書是當代罕見的紀實文學經(jīng)典,極具新聞價值。
新聞寫作與非虛構文學創(chuàng)作有相似,更有不同。它們都屬于非虛構寫作范疇,都源于事實,都盡可能地用實地采訪、調查的方式接近事實。不同的是,新聞寫作更傾向對事實的選擇和記錄。而非虛構文學是—種寫實性的文學體裁,在事實的基礎上要用文學的方式完成藝術化的表達。相比新聞寫作,非虛構文學創(chuàng)作的敘事方式更加多樣化,它借助人類學、語言學、考古學等各學科的經(jīng)驗和手法,完成調查、研究和創(chuàng)作。正如阿列克謝耶維奇所說:“非虛構絕非簡單意義上的新聞報道,而是作家經(jīng)過提煉和淬火的心靈寫作,是作者靈魂與人類精神的展現(xiàn)。”
本文通過研究這部完成于上個世紀末的作品,追溯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品背后的創(chuàng)作觀念,體會她在創(chuàng)作時進行的各種艱難嘗試,為當下的新聞寫作收集濃縮的養(yǎng)料。
沖擊的漣漪
阿列克謝耶維奇是怎樣通過口述者的言語構筑起一個叫切爾諾貝利的世界的?她選擇了哪些人?為什么這樣選擇?又是如何選擇的?
作品中的近百位口述者絕大多數(shù)是平凡的普通人,這些悲劇的主角出現(xiàn)在媒體上的機會很少,“他們不允許任何人錄下這些悲劇,只能錄下英雄事跡。”(在《謊言與真相》這一篇章中,切爾諾貝利防護協(xié)會執(zhí)行委員會副主任謝爾蓋·瓦西里耶維奇·索博列夫口述)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作品中借口述者的敘述為事實畫像。口述者們的處境是相似的,看著身邊的人不斷病倒、離開,他們的疑惑、痛苦、憤懣與悲傷長久以來沒有任何出口,知情者遵守保密原則,沒人為他們解釋到底發(fā)生了什么。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采訪時選擇了涉事各方:有被蒙蔽的百姓,有政府選派的執(zhí)行領導,有蘇聯(lián)政府的護衛(wèi)者,有前斯塔夫哥羅德共產黨地方委員會的第一書記,有科學家(白俄羅斯國家科學院前核能研究所主任)等。通過他們,讀者得以了解當時政府的政策是怎樣形成并如何執(zhí)行的。這位接受采訪的科學家說,他始終無法理性地敘述在切爾諾貝利發(fā)生的一切。
他對接到的第一個任務的描述生動至極。他要將一筆錢分給三十五個寡婦,他們的丈夫都是清理人(特指在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核泄漏事件后處理善后和融毀反應堆核心的人)。“怎么做,才不會虧待這些人?”他為這個問題輾轉反側。每一個寡婦都有自己的境況,有些已經(jīng)生病,有人需要撫養(yǎng)四個孩子……這位科學家做不出這道生活上的數(shù)學題,最終只能把錢平均分配給這三十五個寡婦。
當人面對巨大的災難而無法了解真相,而巨大的悲慟又超出了個體的承受能力,當生命的意義變得模糊不清時,這位科學家嘗試用科學來衡量,用理性來認知,卻以失敗告終。生命的意義無法量化,每個犧牲的生命都無法重來。
這位科學家還接到了組建切爾諾貝利博物館的任務,他想起了一位哭泣的寡婦。她愿意用亡夫的獎章、獎狀、撫恤金換回她的丈夫。她號哭了好久,最終把獎章、獎狀留給了博物館,連同她丈夫的名字。每當科學家擺設這些獎狀時,耳邊似乎都回蕩著她的哭聲。
談到亞羅舒克上校,這位科學家說:“只有等他死了,才會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條街道,一座學校,或一項軍事武器。但這些都要等他死了才會發(fā)生。”但他還活著,只能躺在床上等待那一刻的到來。他一貧如洗,做不了腎結石手術。亞羅舒克上校是一位放射化學家,他曾經(jīng)走遍了整個隔離區(qū),憑一雙腿和輻射劑量計勘測出高輻射地點,把它們一一標注在地圖上。“政府徹頭徹尾利用了他,把他當成機器人。”
同樣被當作機器人的還有三十四萬士兵,他們被派去清理反應爐屋頂,他們都是年輕人,也都是犧牲品。
為了避免再次發(fā)生核爆炸,政府在士兵中征集自愿去打開排水管活門的人,保證提供汽車、公寓、別墅和全家人的永久補助金。科學家說,這些無名小卒都過世了,他們不是沖著物質保證去的,他們最不看重的就是這個。而是他們被教化成要從死亡和犧牲中換取人生的角色和意義,他們因此而去赴死。
這部作品讓讀者看到了爆炸發(fā)生后的切爾諾貝利,游蕩著各種人。
時間捕手
全書的序幕《孤單的人聲》和最后一篇《孤寂的人聲》在內容上首尾呼應。它們分別是兩位有著相似經(jīng)歷的妻子的講述,她們的丈夫都執(zhí)行了致命任務,她們都深愛著自己的丈夫,并在超乎理性之愛的驅使下陪愛人走過強輻射后的臨終一程。
在《孤單的人聲》這一篇章中,口述者露德米拉的講述自然地穿插著她和丈夫瓦西里甜蜜的新婚生活,口述在時間線上的跳躍,讓讀者更能體會她一生難以痊愈的傷痛。講述以“我不知道該說什么,關于死亡還是愛情?”開始。在露德米拉的講述中,所有和瓦西里有關的細節(jié)她都以小時為單位進行。阿列克謝耶維奇并沒有把她時常穿插的對往日幸福時光的回憶以及講述瓦西里的重疊的部分按照時間順序理性地規(guī)整排列,而是保留了這部分,這樣讀者更能感受到露德米拉的注意力只圍繞著瓦西里和不隨時間改變的愛。
“當時我不知道自己有多愛他”是這篇口述的詠嘆調,重復了四次。
有靈魂的攝像機若隱若現(xiàn)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這部非虛構作品中有一個鮮明的個性——隱去“我”。所有的表達、觀點、感嘆、神情都來自口述者。作者成為記錄者,不只記錄口述內容,還包括口述者當時的神態(tài)、表情和動作:開始哭、沉默、停了下來、再次沉默不語、她站起來,走到窗邊……對于一般的采訪者而言,這些不易察覺的細節(jié)很容易被忽略,而阿列克謝耶維奇會對每一個口述者做細致的觀察和記錄。
她不是出于獵奇而采訪,她關切這些有著獨特體驗人群中的每一個人,關心他們的生命和靈魂。阿列克謝耶維奇就像一架有靈魂的攝像機,記錄下另外一架有靈魂的攝像機在切爾諾貝利事件后看到的、感受到的、銘記的。
讀者在全書中看不到阿列克謝耶維奇對自己感受的描述和她個人的明確立場。就連面對口述者歇斯底里的質問時,她也只是做了一名忠實實的記錄者。例如在《大叫》這一篇章中,一位農村醫(yī)療服務員說:“你為什么來這里?想問我們問題?我拒絕出賣他們的悲劇或談論膚淺的哲理。不要來煩我們了,拜托。我們還得住在這里。”另外一個生動的例子來自書中唯一一位無名氏的口述,無名氏發(fā)出一連串責問:“你在寫什么?誰允許你寫的?誰準許你拍照的?東西拿走。把相機拿走,不然我就把相機弄壞。”讀者能夠強烈地感受到現(xiàn)場的氣氛和口述者的情緒,而記錄者永遠不為自己說一個字。
作者摘錄了一篇《歷史背景》,三段文字堪稱新聞寫作的典范。它們分別來自白俄羅斯百科全書、白俄羅斯薩哈羅夫國際生態(tài)學院的《切爾諾貝利災變的影響》以及核泄漏十年后《星火》雜志上的一段文字,三段文字分別立足于白俄羅斯、全世界、四號反應爐的爐心,用新聞、統(tǒng)計數(shù)字和資料極簡而科學地表述了切爾諾貝利的地理位置、爆炸事件和事發(fā)之后給全世界帶來的至今難以估量的影響。
三段說明文字向讀者展示了一個客觀準確的世界,說明了切爾諾貝利核泄漏是什么,意味著什么,影響了什么,作者的選擇體現(xiàn)了她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的認知。她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話把事件的時間、地點、來龍去脈、世界各地對環(huán)境的監(jiān)測再說一遍,但這樣的“轉述”會比這三段文字更直接和具有說服力嗎?作者又一次隱去了“我”,而僅僅充當了《歷史背景》這一篇章的一個編輯的角色,而這些宏觀的、出處明確的、客觀權威的論斷對于讀者來說,無疑都是振聾發(fā)聵的。
“攝像機”不發(fā)聲,卻有靈魂。“有靈魂的攝像機”和口述者交流,引導口述者進入回憶模式并開口說話,這些過程在創(chuàng)作中被全部略去,對于當下媒體環(huán)境的記者而言,對“我”有意地“隱藏”是殘忍的選擇,而阿列克謝耶維奇大刀闊斧地刪除了個人外在的表現(xiàn),完美地隱身在文字里,向讀者呈現(xiàn)出切爾諾貝利核泄漏后一個個被剎那間全然改變的人。近百位口述者講述同一事件,每個人的篇章長短不一,沒有長篇大論,有些人的口述只留下了短短的一段文字,沒有重疊的內容,可想而知,阿列克謝耶維奇對這些采訪材料進行了大量的刪減。
書中來自切爾諾貝利的聲音無不是作者的選擇和“再敘述”。但這種敘述完全忠實于口述記錄,從大量敘述中萃取出他們靈魂深處的發(fā)聲,表達出口述者的立場和觀念。阿列克謝耶維奇在一次采訪時表示:“我試圖透過無數(shù)鮮活的講述,無數(shù)深埋多年的歡笑和眼淚,無數(shù)無法回避的悲劇,無數(shù)雜亂無章的思緒,無數(shù)難以控制的激情,看見唯一真實的和不可復制的人類史。”
只有在后記中,作者才“吝嗇”地表達了自己:“我時常覺得簡單和呆板的事實,不見得會比人們模糊的感受、傳言和想象更接近真相。為什么要強調這些事實呢,這只會掩蓋我們的感受而已。從事實當中衍生出的這些感受,以及這些感受的演變過程,才是令我著迷的。我會試著找出這些感受,收集這些感受,并將其仔細保護起來。”在追尋事實和關注基于事實的感受的過程里,作者關注事件帶給人們的感受的變化,不放過口述者轉瞬即逝的任何細枝末節(jié),精微地感受他人的情感脈絡。
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的認知過程,如果說揭示事實是認識論,那么關注感受的變化則是人類獨有的無可替代的偉大情感。
親歷了切爾諾貝利核泄漏的“他”成為作者筆下的“我”,是敘述主體。作者從有限的、雜亂的、模糊的言語里走近他們、了解他們、成為他們,讓“他”成為那個“我”,遴選出近百位口述者,“他們”如此動情地敘述。“關心他人,才是真的人道主義……當學會尊重他人,又得到了他們的回報——人好像就不再害怕孤獨。”作家張承志的論斷似乎可以作為阿列克謝耶維奇寫作動力的另一種有力的注腳,她以自己的方式——用筆關心生活在切爾諾貝利周圍的人(包括兒童,甚至包括牛、貓、狗和植物)、去清理的人及其家人、政府派去的官員以及被污染后移居切爾諾貝利的人們,都是阿列克謝耶維奇作品中的“他者”。
在新聞寫作中,“感受”是不容易找到容身之處的。記者不是囿于篇幅,就是受限于時間,很難像作者這樣用三四年的時間采訪近百位親歷者,耐心地傾聽,任憑事實與感受在心中發(fā)酵,從口述者表達的蛛絲馬跡中敏銳地發(fā)現(xiàn)語言與思維的風暴,那背后有民族的、地域的和時代的文化對人的塑造,輿論氛圍和社會風潮在新聞寫作中是非常難準確表達的部分。
作者單位:中國民航報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