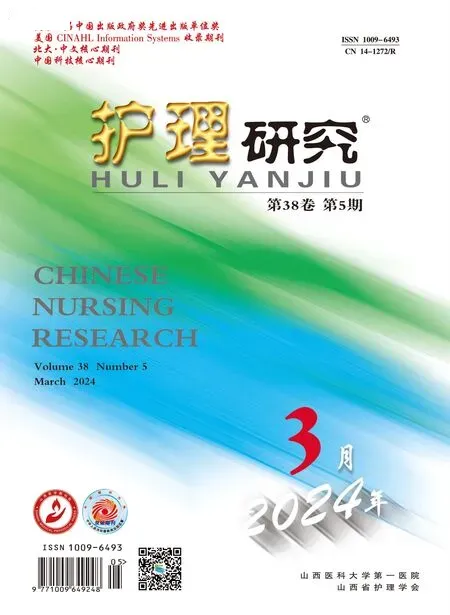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現狀及影響因素
余 琳,范慧芳,李曉麗,杜 姣,賈澤歡
1.山西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山西 030001;2.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
頭頸癌是世界上第七大癌癥類型[1],指發生于頭頸部的惡性腫瘤。手術是頭頸癌主要治療手段之一,但由于頭頸部解剖部位的特殊性與復雜性,頭頸癌疾病本身及治療常會造成病人面容的毀損及言語、張口、吞咽、咀嚼和呼吸等功能受損,對病人的日常生活、社會交往及家庭都帶來巨大影響,因此頭頸癌術后病人往往面臨著較大的心理負擔。有研究表明,頭頸癌病人不僅身體上承擔著巨大痛苦,心理上也經常遭受折磨,常伴隨焦慮、抑郁與孤獨感,病恥感體驗明顯[2-3]。頭頸癌的病因也往往與不良生活習慣相關,如抽煙、喝酒、嚼檳榔、人乳頭瘤病毒(HPV)感染等,病人常伴隨患病后的后悔、自責和羞恥感[4]。一方面,病恥感會延遲病人就醫時間,影響其尋求幫助的主動性,并損害病人自尊心,降低自我認同感,影響病人社會交往[5];另一方面,病恥感與病人癥狀群呈正相關[6],與病人生命質量呈負相關[7],病恥感水平會影響病人疾病癥狀體驗與嚴重程度。但目前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水平及相關影響因素不明朗,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現狀,并分析其影響因素,以期為臨床降低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提供理論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便利抽樣法,選取2022 年4 月—12 月在山西省某三級甲等醫院行手術治療的175 例頭頸癌術后病人為研究對象。所有病人均簽署知情同意書,自愿參與調查研究。納入標準:1)年齡≥18 歲;2)經病理診斷為頭頸癌;3)接受手術治療;4)了解自身病情,無認知障礙。排除標準:1)具有精神疾病或其他類型傳染病;2)合并其他類型癌癥;3)合并其他嚴重軀體疾病。分析有關變量的影響因素時,樣本量至少為變量數的5~10 倍,考慮到20%的無效問卷,樣本量應為94~188 例。
1.2 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資料調查表
由課題組自行設計,包括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居住地、工作狀況、家庭人均月收入、疾病類型、TNM 分期、術后住院時間、是否聯合放化療、是否氣管切開、頭頸手術史。
1.2.1.2 簡體中文版頭頸部惡性腫瘤病人羞恥與恥辱量表
原量表由Kissane 等[8]于2013 年編制,是針對頭頸癌病人病恥感的特異性量表。本研究采用2022 年郭冰潔等[9]對該量表漢化版本[10]進行修訂而形成的簡體中文版頭頸部惡性腫瘤病人羞恥與恥辱量表,修訂版本包括外貌羞恥、自我貶低、后悔、社交/言語關注及外在恥感5 個維度,共計20 個條目,采用Likert 5 級評分法,總分為0~80 分,分值越高,代表病恥感越強。量表在386例頭頸部惡性腫瘤病人中進行驗證,Cronbach's α系數為0.930,內容效度為0.942,重測信度為0.959。
1.2.1.3 簡易應對方式問卷(Simple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采用解亞寧[11]于1998 年對國外應對方式量表進行簡化和修改而形成的簡易應對方式問卷,包括積極應對(12 個條目)和消極應對(8 個條目)2 個維度,共計20 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Likert 4 級評分法,總分為0~60 分。總量表Cronbach's α 系數為0.90,積極應對量表Cronbach's α 系數為0.89,消極應對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78。
1.2.1.4 領悟社會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
原量表由Zimet 等[12]編制,本研究采用姜乾金[13]翻譯和修訂形成的領悟社會支持量表,量表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3 個維度,共計12 個條目,“極不同意”計1 分,“極同意”計7 分,總分12~84 分,得分越高,領悟社會支持越好。量表Cronbach's α 系數為0.914。
1.2.2 資料收集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法,由經過培訓的調查人員使用統一指導語向病人解釋調查的目的及意義,并進行填寫說明。征得病人同意后,現場發放紙質問卷并填寫,所有問卷當場填寫并回收。共發放紙質問卷190 份,回收有效問卷175 份,回收有效率為92.11%。
1.2.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 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定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定性資料以頻數、百分比(%)表示;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t檢驗、χ2檢驗比較不同特征病人病恥感得分的差異;采用Pearson 相關分析法分析病人病恥感與應對方式、領悟社會支持之間的相關性;采用線性回歸分析探討影響病人病恥感的因素。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總分及各維度得分
175 例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總分為(20.97±7.26)分,條目均分為(1.05±1.32)分,其中后悔維度條目均分最高,外在恥感維度條目均分最低。見表1。

表1 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總分及各維度得分情況(n=175) 單位:分
2.2 不同特征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得分比較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齡、工作狀況、TNM分期、術后住院時間、氣管切開及頭頸手術史的病人病恥感總分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影響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單因素分析(x±s,n=175) 單位:分
2.3 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與應對方式、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
本研究中頭頸癌術后病人積極應對得分為(20.55±4.38)分,消極應對得分為(12.19±3.78)分,領悟社會支持得分為(64.93±6.38)分。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病恥感總分與積極應對得分及領悟社會支持得分呈負相關(r值分別為-0.537,-0.488,均P<0.01);病恥感總分與消極應對得分呈正相關(r=0.615,P<0.01)。見表3。

表3 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與應對方式、領悟社會支持的相關性(r 值)
2.4 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影響因素的線性回歸分析
以病恥感總分作為因變量,單因素分析中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變量及應對方式、領悟社會支持得分作為自變量進行線性回歸分析,自變量賦值方式見表4。結果顯示,年齡、TNM 分期、氣管切開、頭頸手術史、消極應對及領悟社會支持是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的影響因素,共解釋病恥感48.2%的變異。見表5。

表4 自變量賦值方式

表5 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影響因素的線性回歸分析
3 討論
3.1 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現狀
本研究結果顯示,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量表總分為(20.97±7.26)分,條目均分為(1.05±1.32)分,略高 于Kissane 等[8]測 評 的(18.08±14.67)分 和Wang等[10]測評的(17.51±12.208)分。分析原因可能是:1)本研究納入的研究對象均接受了手術治療。手術是頭頸癌主要的治療手段,是病人治愈疾病、爭取更長生存期的重要方法。但手術帶給病人暫時或者長期的身體上的損傷也是客觀存在的,術后病人常常面臨毀容和身體意象障礙的風險[14],進而增加病人的病恥感水平[15-16]。2)疾病嚴重。本研究中疾病中后期病人占45.71%,Kissane 等[8]的研究中疾病Ⅰ期、Ⅱ期病人占比大,提示本研究納入的研究對象疾病嚴重程度更高。研究表明,疾病越嚴重,病人病恥感越高[17-18]。3)文化差異。癌癥是帶有死亡等消極色彩的疾病,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死亡常常是禁忌話題[19],導致許多癌癥病人難以與家人朋友坦率、深入地交流病情,病人身邊的親屬也經常對病人回避癌癥或死亡相關話題,外界的反應導致病人自我負性評價,加重了病人病恥感。
3.2 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的影響因素
3.2.1 年齡
本研究結果顯示,年齡較小的病人病恥感高于年齡較大的病人,與相關研究結果[20-21]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中青年人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與家庭經濟負擔,他們更需要注重外貌形象,對社交和工作的需求也更大,更容易感受到頭頸癌術后功能障礙對生活和工作的影響,產生更高水平的病恥感。與此同時,年齡較小者社會經驗相對更少,心理穩定性與承受力也較年老者差,面對疾病與手術的應激、遭遇疾病術后生活的重大轉變,更容易產生消極的情緒,產生自卑、絕望的想法,喪失自我價值感。提示醫務人員在臨床工作中應更加注重對于年齡較小的頭頸癌病人的心理疏導,在治療過程中考慮同步進行形貌修復,術后告知病人修飾形貌的方法,盡量減小手術對病人工作和生活的影響。
3.2.2 TNM 分期
回歸分析顯示,分期越高,病人病恥感越強,與以往研究結論[17-18]相似。疾病分期越高,表示病人疾病越嚴重,手術難度與治療時間相應增加,治療費用也會更高,帶給病人及其照顧者更多身體、心理與經濟上的壓力,病人病恥感體驗增加。研究表明,家庭主要照顧者的照顧負擔是形成病人病恥感的重要因素之一[22]。疾病分期高的病人手術范圍和難度增大,術后遺留功能障礙的機會增加,導致其癥狀群增加、癥狀體驗更差,家屬的照顧負擔也隨之加重,進一步促進了病人病恥感的形成。同時TNM 分期越高,疾病治愈的希望越小,而希望水平與病恥感呈負相關[23],當病人遭受嚴重的疾病折磨卻沒有治愈疾病的希望時其病恥感體驗會顯著增強。提示醫護人員面對疾病嚴重的頭頸癌病人,應盡量緩解其癥狀體驗,促進病人舒適,做好飲食、功能鍛煉、睡眠等相關的指導,減輕病人及照顧者的負擔,給予病人更多生活的希望,以此減輕病人病恥感。
3.2.3 氣管切開
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后氣管切開是病人病恥感的影響因素,氣管切開者病恥感更高。分析原因可能是:氣管切開病人往往面臨暫時或長期的語言溝通障礙,語言是人們日常生活交流的重要途徑。喪失語言系統,病人日常生活將面臨諸多不便,病人將難以傳達自身需求,不僅不利于病人身體的恢復,也不利于病人情緒的表達。戴丹丹等[2]的質性研究顯示,全喉切除復聲失敗病人病恥感體驗明顯,多數病人在生活中曾遇到諸多不便,許多病人存在社交回避現象。Devins等[24]的研究也表明,在頭頸癌病人相關壓力源中,來自人際關系的壓力源是最為常見的,給病人帶來明顯的痛苦感受。因此,對于頭頸癌術后氣管切開病人,醫護人員應提前教會病人語言的替代方法,比如書面表達或者肢體語言表達等。同時鼓勵病人積極進行發音訓練,比如食管發音、電子喉發音等,減輕病人因語音障礙造成的病恥感。
3.2.4 頭頸手術史
本研究發現,有過頭頸癌手術史的病人病恥感更高,與陳瀟等[21]的研究結果相似。分析原因可能有:1)再次進行頭頸癌手術的病人常常是癌癥復發或者返院進行功能障礙修復的病人,無論是哪種情況,病人都會產生更嚴重的病恥感。疾病復發者,意味著疾病治療難度大,疾病預后可能不容樂觀,病人容易產生消極情緒和自我否定感;進行功能障礙修復的病人,表明術后遺留的功能障礙已經嚴重影響日常生活,病人病恥感會更強。2)有過頭頸癌手術史的病人在上次術后已經回歸社會一段時間,病人可能會發現自己很難回到與患病前一樣的生活,他們可能已經實際了解了外界對頭頸癌術后病人的態度與看法,遭遇過他人的歧視言語和行為。當病人實際經歷過來自外界環境的壓力后更容易產生更加深刻的內在病恥感[25-26]。Rapoport等[27]的研究也顯示,隨著時間推移,頭頸癌病人的多數疾病診療問題逐漸減少,但許多心理問題,包括焦慮與憤怒反而加重。提示當病人度過手術康復期,病人的心理健康問題將會更加明顯,醫護人員需要對頭頸癌術后病人進行延續性的心理護理,可以通過建立微信群或網站等方式,對病人的恢復情況進行長期追蹤,必要時進行遠程心理干預,減輕術后病恥感對病人回歸日常生活的影響。
3.2.5 消極應對本研究結果顯示,消極應對得分越高,病人病恥感越高,與以往研究結論[28-29]相似。應對方式是指個體面對現實世界中的應激事件所采取的認知與行為調節策略,是病人處理事件或調節事件帶來的情緒反應的過程。積極應對方式包括面對、發泄等;消極應對方式包括回避、幻想、壓抑和屈服等。病人病恥感與積極應對呈正相關,與消極應對呈負相關。本研究最終消極應對進入回歸方程,提示消極應對方式對病人病恥感的影響更大。病人對于患病和手術治療采取消極應對,不僅不利于疾病的治療與康復,更不利于情緒的宣泄與心理的健康[18]。提示醫護人員應該幫助病人更快適應疾病,可以采取積極心理學方法,鼓勵病人積極應對,減少消極應對,從而減輕病恥感,促進病人心理健康。
3.2.6 領悟社會支持
本研究結果顯示,領悟社會支持越高,病人病恥感越低,同相關研究結論[17,30]相似。分析原因可能是:一方面,社會支持會影響病人心理調適水平[31],更高的社會支持能夠幫助病人更好地調節情緒,增強面對病恥感的抵抗力;另一方面,社會支持可以幫助病人解決實際問題,減輕病恥感帶給病人的一些負面后果,從而為病人面對疾病治療和康復的壓力提供緩沖,增強病人對抗疾病、回歸日常生活的信心。與此同時,家庭支持是病人社會支持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表明,家屬與病人的日常互動會影響病人病恥感的內化[32]。因此,未來病恥感干預的方向可以是發展更多社會支持,包括促進家庭內支持、提高家庭外支持(包括醫院、社區、社會大眾等)來幫助病人克服病恥感。
4 小結
綜上所述,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不容忽視。年齡、TNM 分期、氣管切開、頭頸手術史、消極應對和領悟社會支持是頭頸癌術后病人病恥感的影響因素。醫護人員在臨床工作中應注意篩查病人,對于年齡較小、分期較高、行氣管切開及有過頭頸手術史等的高危因素病人進行提前心理干預,同時根據病人的具體情況,采取針對性的護理措施,減少病人消極應對,提高病人社會支持水平,以降低其病恥感,提高心理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