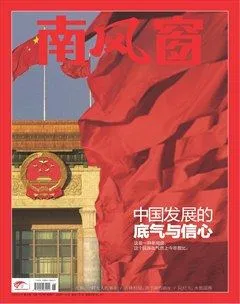在海外,找人比找錢更難
趙靖含 張旦珺

2023年末,畢業六年的王羽從雅加達飛往馬德里,開啟了人生中的第二輪駐外生涯。他的就職軌跡背后,是公司不斷擴張的出海版圖。
與此同時,27歲的劉強從國內一線城市搬至新加坡,成為“宇宙大廠”字節跳動全球化布局網絡中的一員,在陌生國度里收獲令同齡人艷羨的高薪。
今天,無論是龐大的企業,還是飄搖的個體,出海都成了因勢利導的熱門賽道。
回看歷史,中國人的出海之路,自古未絕。西漢時期,張騫率隊通西域,絲路文明自此誕生。明朝年間,鄭和領航七下西洋,創下劃世紀的奇跡。
其中,上位者的前瞻思維、時代之勢所趨,是出海戰略的由來根本,但出色的執行者,卻是決定這一路徑成敗的核心所在。
走出國門,意味著語言、文化、法律、政治,以及市場環境的高度陌生,意味著一切母系支持都將變得遙遠,想象中的藍圖將面臨現實的重構。高回報和高風險,始終似黑白雙生,如影隨形。而關鍵的破局密碼即是—人。
領英曾聯合波士頓咨詢公司編寫《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白皮書》,其研究顯示,以財富中國500強企業為例,2021年就已有約90%的企業,擁有不同形式的國際化業務。
2024年即將進入第二個季度,中企大航海之路依然穩中求進。“不出海,就出局”的讖言四起,如同高懸于企業之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管理者決策一旦出現偏差,市場份額就將拱手讓出。
上述白皮書還提到,與過去的海外投資并購不同,在這一階段,中企更加兼顧海外本土化運營,如建設海外營銷能力、海外供應鏈和海外技術。名創優品集團副總裁兼海外事業部總經理黃錚,對南風窗直言,人才難尋,是出海戰略順利推進的掣肘。
領英中國區總經理王茜提到,在中企出海的“能力國際化”階段,通過服務75%的中國出海百強企業,領英發現雇主對理想候選人的需求從單一技能向綜合技能轉變,企業急需擁有國際視野的復合型人才。
未來兩年,人才出海,也許是整個出海經濟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已經成為全國人大代表的關注焦點。據《華夏時報》報道,在2024全國兩會召開之際,全國人大代表胡成中將帶著多份議題赴京參會,其中包括建議國家有關部門在人才落戶海外中企的過程中提供更多便利,同時對這類人才在出海之前提供專業培訓。
每一個意欲揚帆的中國民營企業,都在尋找自己的張騫與鄭和。但對于蓄勢待發,甚至已經拔錨起航的企業而言,全球化人才到底搶什么人,為什么搶,該怎么搶?
搶人,企業出海必修課
“如果沒有選對人,那么再好的戰略也沒有意義。”這是通用電氣原CEO杰克·韋爾奇的名言,他將人才視為企業經營最重要的因素。
而在國內,熱衷講故事的雷軍也在公開場合多次提到,小米公司尚在襁褓的那年,他80%的時間都用在了一件事上:找人。雷軍自述每天花費12個小時用于招人,為了一個關鍵的候選人,他在兩個月中邀約對方談話17次。
但隨著出海人才需求的爆炸式增長,以及外國環境存在的不確定性,“人才搜索”的難度也隨之增加,企業領導者和人力資源部門開始向外尋求幫助。諸如領英等全球職場社交平臺,成為了許多中企出海的“最佳媒人”。
2023年8月9日,國內本土化求職平臺“領英職場”正式停止服務。與外界猜測其放棄中國市場恰恰相反,中國區總經理王茜用數據說服總部,成功保留并壯大了領英中國的B端業務,全面賦能中國企業全球化。
人才出海已經遠遠不是“招募—面試—入職”這樣的線性作戰。
根據領英提供的官方數據,中國有5.9萬家企業需要在海外招聘,到2026年招聘450萬人才,市場規模將達到84億美金。脈脈發布的《2023年度人才遷徙報告》也顯示,中企出海相關崗位的招聘需求,連續三年增長。
其中,新能源汽車行業2022年的出海崗位同比增長249%,2023年再次攀升86%。互聯網、游戲、新能源、新生活服務等新經濟企業,對運營崗及市場崗的招聘需求最為濃烈。
王茜對南風窗表示,當前中企的“能力國際化”階段,主要面臨三個問題。一是全球經濟新格局的產生;二是技術的更新換代,例如新能源汽車替換傳統燃油車,互聯網的AI轉型等;三是出海目的地的拓新,從過去熟悉、主攻的一些市場,到現在逐步走向全球開花。
種種因素,既加速推動了中企出海的步伐,也暴露出了一些共同的問題。
在海外的“水土不服”,最先暴露在“人”的問題上。領英曾服務過一個案例,客戶希望在海外市場建造一個2萬人的研發中心,但滿足其行業背景的華人非常有限,甚至總人數都不足2萬。
要想成為成熟的全球化企業,必須更加重視本土文化、本地人才和在目標市場的適應力,并注重階梯式吸引和培養海外本地人才,以更好地完善國際化人才建設。
出海選址也極大地影響人才招募的效率。
比如,王茜提到,一家國內知名的科技企業曾委托領英在硅谷或西雅圖為其選址,建造海外研發中心。當時的普遍觀點認為,這些地方的研發技術人才資源非常成熟且豐富。但領英大數據洞察提供的建議是,這些區域雖然人才儲備非常充足,但是競爭非常激烈。
最終,領英為該公司提供的選址方案是一個中歐國家,當地的人才供給量是需求的100倍,市場競爭并不激烈,性價比更高,并且該地擁有非常豐富的高校研發資源。
這些信息背后透露出的一個規律是,人才出海已經遠遠不是“招募—面試—入職”這樣的線性作戰,雇主需要考量的,是更加立體且復雜的海外布局網絡和人才擇選方式。
企業人力資源部門與各大招聘平臺之間的關系,也從單一的產品服務深化為全方位的解決方案定制。以領英為例,王茜認為,其發揮的是精準探測器功能,幫助企業明確適合的人才,借鑒他人經驗,在全球化過程中,利用數據幫助戰略合作伙伴做導航,從而做出正確的業務決策。
駐外,個體的考量
從人才側來看,國內就業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裁員危機不時出現,選擇順應出海大潮,成為一名中企駐外員工,是當代年輕人的解題方案之一。
獵聘大數據研究院發布的《2023上半年人才流動與薪酬趨勢報告》顯示,截至2023年上半年,求職者投遞海外/境外職位與2022年同期相比增長了92.9%,其中,“95后”的海外投遞意愿增長了135.7%。
王羽畢業不久后,加入了一家新生代手機品牌。因公司入局較晚,國內智能手機市場已成為一片紅海,但該品牌創立僅三年,就已經躋身全球手機市場銷量前十,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創業初期,便快、準、狠地選擇了出海戰略。
幾乎與公司的發展同頻,王羽也在駐外的道路上一往無前。2023年11月以前,他一直在雅加達生活,為公司開展東南亞、南亞及拉美市場的公關工作,如今已遷至馬德里,轉戰西班牙市場的整體營銷。
他認為中國品牌出海是一個大趨勢,尤其在手機行業,國內市場已經高度飽和,“完全就是在玩零和游戲,內卷所產生的價值趨弱”。
對于個人發展而言,海外的工作履歷無疑是簡歷的加分項,可以開闊自己的國際化視角,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工作與生活經驗,對營銷的工作前景也更添競爭力。
除了為履歷增色以外,吸引人才遠赴他國的重要因素,還有足夠誘人的待遇。
中企出海的樣本企業廣西柳工集團,前海外業務總經理黃兆華曾在文章中寫道:“一般而言,駐外人員的基本收入(不包括差旅補貼)高于國內同等崗位的30%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某國企控股的制造業上市公司,駐非洲地區辦公室的中國員工,僅基礎工資及駐外補貼,不含其他獎金,年薪可達到稅后60萬元左右,東南亞地區的駐外薪酬則略低于這個數字。
27歲的劉強聽從公司安排,于去年選擇前往字節跳動關聯的新加坡辦公室工作。他的工資水平,在新加坡政府推出的“互補專才評估框架(COMPASS)”中基本能得20分,這意味著他需達到或超過其當地同行的前10%水準。
工科碩士畢業的陶豐,也選擇從事了出海相關工作,但并沒有邁出正式駐外的一步。他在中興通訊負責無線產品的國際售后,同事中有許多年輕的“00后”,一年中大概有6—10個月需要出差海外。在其他時間,他們仍然可以待在國內辦公室工作,遠程協助國外訂單的開展與維護。
一般而言,駐外人員的基本收入(不包括差旅補貼)高于國內同等崗位的30%左右是比較合理的。
最近,陶豐正在支援德國。中國時間下午四點,他正準備開始新的工作—盡管身處深圳,但他需要配合德國的時差,該地正是上午九點。
直接選擇出國待遇會更好,陶豐所在部門也有機會進行駐外申請與選拔。但他還是沒能下定決心,只因無法接受一年只能回國一兩次,這意味著他的親緣、朋友,以及戀人關系都將面臨重大挑戰。
事實上,在宏觀向好的大趨勢和耀目的發展數字之外,陶豐所面臨的糾結與困惑,也是人才出海中無法忽視的客觀存在。個體所面臨的困境,人心的選擇與考量,很大程度上,都在影響一艘大船的航向。
砸錢,不是萬全之法
領英中國區總經理王茜對南風窗總結了中企出海招聘中,存在的三大問題。
首先,我們過于追求中國速度,忽視了人才戰略的整體規劃。這導致招募速度較快,表面上取得了良好進展,但后來人才流失率也很高。
其二,缺少換位思考,缺乏吸引核心崗位高端人才的軟性招聘能力,人才的求職需求愈加多元化。“用高薪在市場上去買人才”不是萬全之法,很多成功的高管及研發人員,更講究的是自我價值的實現,Z世代的年輕人可能更注重感受。
其三,合規風險和價值觀差異,帶來的思維和做事方式的沖突。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當地的法律法規都有所區別,如產業限制、數據安全隱私等,甚至有一些地區,還有傳統的宗教文化風俗禁忌。這要求中國企業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需要合法合規,也要合情合理。
王羽、陶豐等人的經驗、感受也佐證了這一觀點。
從王羽的駐外經歷來看,印尼對于外資企業的入市有一定限制,甚至還會面臨移民局的刁難。
而西班牙的政策相對寬松,但歐盟對于進口、隱私數據管理、產品認證等等都有相關的法律法規限制。
文化差異也帶來了潛在的工作問題,例如當地員工對加班的不同看法,以及對于中國企業員工關系之間的理解與適應。種種因素,都對他的整體營銷工作產生了一定沖擊。
陶豐則告訴南風窗,孟加拉國、斯里蘭卡等南亞國家,還經常發生當地員工因不滿加班,多次罷工的問題。而中國負責人不得不多方柔性處理,以承諾加薪等方式換取工作的順利推進。

此外,如果在招聘后沒有做好人才管理,極易被競爭對手挖人。例如這兩年,華為勢頭強勁,就讓同類型的出海公司“有所擔憂”。
領英中國區總經理王茜認為,中國企業往往喜歡先嘗試,在做出行動的過程中,進行下一步的探索。但在實際的出海過程中,計劃,要更為重要。
她還提到,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市場,品牌世界化,不是一味地沿襲、借力中國的品牌聲量。領英的客戶之一傳音控股,在非洲的不同市場都制定了不同的戰略,結合當地市場說出品牌故事,因此才能觸達目標人群。
人才招聘也是如此,僅憑品牌效應的大旗并不能真正地收攏軍心。管理者對員工的體察、溝通,及對人才的專項培育,都相當之重要。
李書福的人才森林理論是極佳表率,外聘高端人才(大樟樹)及培育內部人才(小樹苗)同樣重要,且應該彼此成就。
黃兆華在《出海·征途:解碼中國企業全球化之道》一書中,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2009年,廣西柳工派出了第一位中國員工擔任海外子公司總經理。直到駐外總經理要出發機場,赴任他鄉的那個下午,黃兆華才著急忙慌地行使了管理談話的職責。
他對此事深感愧疚,認為這是中國企業對國際化人才培養的理解太過稚嫩。后來,他曾深度參與中國中車、華潤集團等多家大型企業的全球化人才培養工作。他認為,李書福的人才森林理論是極佳表率,外聘高端人才(大樟樹)及培育內部人才(小樹苗)同樣重要,且應該彼此成就。
自2001年入世以來,“走出去”的口號已經響徹商界,但對于個體的人而言,遠航依然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對企業來講,如何找到合適的舵手,并幫扶、培育合適的舵手成為優秀的舵手,是值得持久修煉的課題。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王羽、劉強、陶豐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