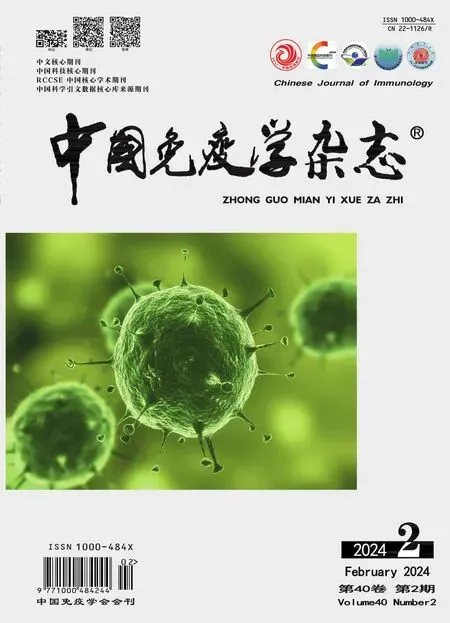雷公藤甲素對肺動脈高壓大鼠免疫炎癥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
王梅愛 黃秋虹 陳慧勤 黃倩 鄭丹丹 (泉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基礎醫學部,泉州 362000)
肺動脈高壓是較常見且嚴重的血管性疾病,特點為肺動脈壓力、肺血管循環阻力升高,以動脈型肺動脈高壓亞型研究最為廣泛,病因為肺小動脈原發性病變、肺小動脈血管重塑增厚而致肺動脈阻力增加,可累及心臟,最終引起右心衰竭或死亡[1]。臨床研究發現,肺動脈高壓的發生與免疫炎癥所介導的肺小動脈重塑相關,重塑的肺小動脈周圍存在不同程度的淋巴細胞、肥大細胞、巨噬細胞等炎癥細胞浸潤,上述炎癥細胞分泌炎癥因子,隨著病程發展,最終導致肺動脈內皮損傷[2]。
野百合堿(monocrotaline,MCT)屬吡咯烷生物堿,可引起肺動脈平滑肌細胞異常增殖、肺小動脈重塑,最終導致肺動脈高壓發生[3]。目前利用MCT所致的肺動脈高壓模型較為經典,可用于研究藥物效果和作用機制。
目前臨床上多采用波生坦、貝前列素等藥物治療肺動脈高壓,雖能明顯控制疾病進一步進展,但長期療效不佳,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尋找治療肺動脈高壓的有效藥物刻不容緩。雷公藤甲素屬本質藤本植物雷公藤提取物,隨著對雷公藤甲素的研究增多發現其具有免疫抑制、抗腫瘤、抗炎的藥效,且可改變血管病變[4]。雖然早在2010年就有研究發現雷公藤甲素具有治療肺動脈高壓作用,但其具體作用機制尚未明確[5]。因此本文采用MCT誘導的肺動脈高壓大鼠模型,使用雷公藤甲素干預,分析其治療肺動脈高壓的作用機制,現報道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
1.1.1 實驗動物 選取6~8周齡SPF清潔級SD雄性大鼠90只,體質量190~240 g,均購自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動物許可證號:SYXK(京)2021-0019。在恒溫(22±2) ℃、恒濕(55±5)%、人工光照明暗各12 h環境下適應性飼養7 d,均自由活動、飲水、取食。本研究獲得泉州醫學高等專科學校倫理委員會批準[泉醫高專動物倫理審字(2021013號)]。
1.1.2 試劑與儀器 MCT(TargetMol,中國);雷公藤甲素(滁州仕諾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規格20 mg,質量分數>98%);蘇木精-伊紅染液(上海吉至生化科技有限公司);ELISA試劑盒及相關試劑(江西艾博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小鼠抗大鼠TLR4抗體、兔抗人NF-κB抗體(深圳海思安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光學顯微鏡(奧林巴斯);流式細胞儀(美國BD)。
1.2 方法
1.2.1 肺動脈高壓模型構建 隨機選取15只大鼠作為正常組,其余75只大鼠作為肺動脈高壓組,建立肺動脈高壓模型,均一次性皮下注射60 mg/kg MCT,連續觀察14 d,建模過程中肺動脈高壓組共死亡5只。在建模第15天隨機選取2組中的5只大鼠測定平均肺動脈壓(mean pulmonary arterial pressure,mPAP)、右心室收縮壓(right ventricular systolic pressure,RVSP),若與正常組相比,肺動脈高壓組mPAP、RVSP均明顯升高,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則說明模型建立成功。
1.2.2 分組干預 分析mPAP、RVSP水平發現肺動脈高壓組均建模成功,將剩余的65只大鼠隨機分為模型組、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每組13只。陽性對照組使用30 mg/kg潑生坦灌胃,雷公藤甲素A、B、C組根據文獻[5]劑量給藥,分別腹腔注射0.1、0.2、0.4 mg/kg雷公藤甲素,正常組、模型組注射等體積生理鹽水。連續干預28 d,觀察大鼠變化。
1.2.3 指標觀察
1.2.3.1 mPAP、RVSP測定 在藥物干預結束后次日,稱量大鼠體質量,根據體質量腹腔注射3%戊巴比妥鈉(30 mg/kg)麻醉,在其右頸部做一切口,將右側頸外靜脈分離,經上腔靜脈、右心房將右心導管插至肺動脈,導管另一端連接壓力傳感器,智能生理信號采集、記錄系統,當出現穩定的波形后測定mPAP、RVSP。
1.2.3.2 樣本采集 在上述操作完成后,抽取6組大鼠腹主動脈血,備用。之后遵循動物實驗倫理要求處死大鼠,迅速取心肺組織,心臟組織用于測定右心室肥厚指數(righ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index,RVHI),右肺制備石蠟切片,做肺小動脈形態、肺小動脈重塑分析,左肺首先進行肺泡灌洗,將得到的灌洗液保存,灌洗之后的左肺組織保存于液氮中備用。
1.2.3.3 RVHI測定 取各組所分離的心臟組織標本,沿室間隔(ventricular septum,S)將心室分離出后沖洗、吸干水分,對室間隔左心室(ventricular septum was left ventricle,LV)、右心室(right ventricle,RV)質量進行稱量,計算RVHI,RVHI=RV/(LV+S)。
1.2.3.4 肺小動脈形態、肺小動脈重塑觀察 取右肺石蠟切片樣本,蘇木精-伊紅染色,光學顯微鏡下觀察6組大鼠肺小動脈形態。同時測定肺小動脈重塑相關指標:肺小動脈中層血管壁厚度占肺小動脈外徑的百分比(MT%)、肺小動脈中層橫截面積占總橫截面積的百分比(MA%)。
1.2.3.5 免疫炎癥相關指標測定 取所采集的腹主動脈血,分離出淋巴細胞,進行細胞表面熒光染色,使用流式細胞儀測定Th17細胞、Treg細胞比例。取腹主動脈血、肺泡灌洗液,使用ELISA測定血清、肺泡灌洗液中Th17細胞相關因子IL-6,IL-17、Treg細胞因子IL-10表達水平。
1.2.3.6 TLR4/NF-κB信號通路蛋白測定 取液氮中保存的左肺組織,分離出肺動脈,肺動脈加入80 μl裂解緩沖液,提取蛋白,制備為勻漿,在4 ℃下離心15 min(12 000 g,r=5 cm),收集所分離的上清液,定量分析蛋白,并使蛋白變性、電泳,采用Western blot法測定TLR4/NF-κB信號通路蛋白TLR4、NF-κB蛋白表達量。
1.3 統計學分析 數據使用SPSS22.0軟件分析,各組間差異比較使用單因素方差或雙因素方差分析,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肺動脈高壓模型鑒定 建模過程中,正常組大鼠無死亡,活動自如。肺動脈高壓組隨著MCT注射時間延長,活動逐漸減少,呼吸困難,毛發粗糙,體質量增長緩慢,且癥狀逐漸加重,共死亡5只。在建模第14天測定mPAP、RVSP,肺動脈高壓組mPAP、RVSP均顯著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提示肺動脈高壓模型建立成功。見圖1。

圖1 正常組、肺動脈高壓組mPAP、RVSP比較Fig.1 Comparison of mPAP and RVSP between normal group and pulmonary hypertension group
2.2 mPAP、RVSP對比 與正常組相比,模型組、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mPAP、RVSP升高(P<0.05);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mPAP、RVSP均低于模型組(P<0.05);雷公藤甲素A、B、C組mPAP、RVSP均低于陽性對照組(P<0.05);隨著雷公藤甲素干預劑量的增加,mPAP、RVSP逐漸降低,雷公藤甲素C組低于B組、A組(P<0.05)。見圖2。

圖2 各組mPAP、RVSP對比Fig.2 Comparison of mPAP and RVSP in each group
2.3 RVHI對比 與正常組相比,模型組、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RVHI升高(P<0.05);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RVHI均低于模型組(P<0.05);雷公藤甲素A、B、C組RVHI均低于陽性對照組(P<0.05);隨著雷公藤甲素干預劑量的增加,RVHI逐漸降低,雷公藤甲素C組RVHI低于B組、A組(P<0.05)。見圖3。

圖3 各組RVHI對比Fig.3 Comparison of RVHI in each group
2.4 肺小動脈形態觀察 正常組大鼠肺小動脈管壁厚度一致,內皮細胞均勻緊貼于血管壁,無炎癥浸潤;相比于正常組,模型組管壁明顯增厚,管腔狹窄,內皮細胞部分腫大脫落,有炎癥浸潤現象。相比于模型組,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病理改變均顯著改善,且雷公藤甲素C組改善程度大于雷公藤甲素B組、A組、陽性對照組。見圖4。

圖4 肺小動脈形態蘇木精-伊紅染色(×400)Fig.4 Hematoxylin-eosin staining of pulmonary arteriole morphology (×400)
2.5 肺小動脈重塑指標水平對比 與正常組相比,模型組、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肺小動脈重塑指標MT%、MA%升高(P<0.05);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MT%、MA%均低于模型組(P<0.05);雷公藤甲素A、B、C組MT%、MA%均低于陽性對照組(P<0.05);隨著雷公藤甲素干預劑量的增加,MT%、MA%逐漸降低,雷公藤甲素C組低于B組、A組(P<0.05)。見圖5。
2.6 免疫炎癥相關指標水平對比 與正常組相比,模型組、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Th17細胞比例、IL-6、IL-17水平升高,Treg細胞比例、IL-10水平降低(P<0.05);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Th17細胞比例、IL-6、IL-17水平低于模型組,Treg細胞比例、IL-10水平高于模型組(P<0.05);雷公藤甲素A、B、C組Th17細胞比例、IL-6、IL-17水平低于陽性對照組,Treg細胞比例、IL-10水平高于陽性對照組(P<0.05);隨著雷公藤甲素干預劑量的增加,Th17細胞比例、IL-6、IL-17水平逐漸降低,雷公藤甲素C組低于B組、A組,Treg細胞比例、IL-10水平逐漸升高,雷公藤甲素C組高于B組、A組(P<0.05)。見圖6。

圖6 免疫炎癥相關指標水平對比Fig.6 Comparison of levels of immune inflammationrelated indicators
2.7 TLR4/NF-κB信號通路蛋白表達量對比 與正常組相比,模型組、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TLR4、NF-κB升高(P<0.05);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TLR4、NF-κB均低于模型組(P<0.05);雷公藤甲素A、B、C組TLR4、NF-κB均低于陽性對照組(P<0.05);隨著雷公藤甲素干預劑量的增加,TLR4、NF-κB逐漸降低,雷公藤甲素C組低于B組、A組(P<0.05)。見圖7。

圖7 TLR4/NF-κB信號通路蛋白表達量對比Fig.7 Comparison of proteins expressions of TLR4/NF-κB signaling pathway
3 討論
肺動脈高壓屬惡性肺血管疾病,主要病理改變為肺血管重塑,而在此過程中免疫炎癥發揮重要作用,因此多數學者致力于肺動脈高壓免疫炎癥的研究[6-7]。鑒于此,本文以免疫炎癥為研究方向,分析藥物干預對肺動脈高壓大鼠免疫炎癥的影響,并探究其具體作用機制,為臨床上治療肺動脈高壓疾病提供參考。
臨床研究認為,在肺動脈高壓進展過程中可累及心臟,肺動脈-肺臟-右心室形成此病的發病軸,右心功能明顯改變[8-10]。因此根據右心功能相關指標可評價疾病情況,本研究使用RVSP、RVHI分析各組右心功能,結果發現,模型驗證時,肺動脈高壓組RVSP、RVHI較正常組均顯著升高,提示肺動脈高壓已經累及心臟。雷公藤甲素屬于一種炎癥反應抑制劑,具有較強的抗免疫炎癥的作用[11]。CHEN等[12]研究認為雷公藤甲素具有抑制深度低溫循環停止大鼠炎癥的作用。且部分研究證明,雷公藤甲素用于多種疾病的干預治療效果理想[13-14]。在上述背景下本文將雷公藤甲素用于肺動脈高壓的干預中,經藥物干預后發現,陽性對照組、雷公藤甲素A、B、C組RVSP、RVHI均有一定程度降低,且以雷公藤甲素C組降低幅度最大,此結果提示雷公藤甲素可修復肺動脈高壓累及的心臟病變。
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雷公藤甲素干預后大鼠免疫炎癥明顯被抑制,表現為Th17/Treg細胞失衡被修復,且經雷公藤甲素干預的肺動脈高壓大鼠TLR4/NF-κB信號通路蛋白TLR4、NF-κB蛋白表達量明顯降低,此結果說明雷公藤甲素具有改善肺動脈高壓大鼠免疫炎癥表現的作用,且TLR4/NF-κB信號通路可能為其具體作用機制,此結果與孫貝貝等[15]、宗佳琪等[16]的研究結果相似,均認為TLR4/NF-κB信號通路為雷公藤甲素發揮作用的靶點。報道稱,TLR4/NF-κB信號通路中的TLR4廣泛分布于中性粒細胞、肺巨噬細胞、氣道上皮細胞中的Toll樣受體家族成員,TLR4與肺動脈高壓關系密切,在肺動脈高壓中表達異常升高[17-18]。研究顯示,在肺組織受到外部因素刺激后,存在于肺血管內的TLR4與其對應的配體發生特異性結合,此時作為TLR4的下游轉錄子NF-κB被激活,NF-κB被激活后Th17/Treg失衡,進而誘導肺動脈高壓的發生[19]。在肺動脈高壓發生時,TLR4/NF-κB被激活,隨著疾病的進展Th17細胞分泌IL-6、IL-17能力增強,Treg細胞所分泌的IL-10水平降低,其中IL-6、IL-17為促炎因子,可促進肺局部免疫炎癥級聯,抑炎因子IL-10低水平不足以維持Th17/Treg平衡,而導致肺小動脈重塑,最終導致疾病的發生發展[20-22]。本文發現雷公藤甲素經肺動脈高壓大鼠TLR4/NF-κB信號通路蛋白TLR4、NF-κB蛋白糾正Th17/Treg細胞失衡表現,通過抑制免疫炎癥反應而修復肺小動脈重塑,最終發揮治療肺動脈高壓的作用。
本研究認為,雷公藤甲素可劑量依賴地改善肺動脈高壓,但僅分析對動脈型肺動脈高壓的藥效,并未分析雷公藤甲素對其他類型肺動脈高壓的干預作用,還需進一步分析是否可用于其他類型的肺動脈高壓干預治療。
綜上,本研究發現雷公藤甲素可劑量依賴地改善肺動脈高壓大鼠肺動脈病理損傷,抑制肺小動脈重塑、免疫炎癥,其機制可能與TLR4/NF-κB失活有關。綜合以上結果可認為雷公藤甲素具有治療肺動脈高壓的潛力,值得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