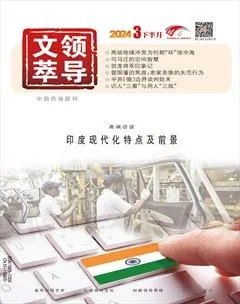山河故人劉禹錫的起落悲欣
鄒安時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劉禹錫的《秋詞》和《酬樂天揚州初逢席上見贈》,恰好是詩人23年貶謫生涯的起止點。無論仕途起落,還是詩文創作,劉禹錫的命運,均與數位重要人物羈絆甚深。
等閑平地起波瀾
劉禹錫21歲進士及第,同年又通過博學鴻詞科考試。《唐摭言》記錄時人諺語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可見進士科的含金量。“博學鴻詞科”考試亦稱“制科”考試,乃是優中選優的干部選拔測試,錄取率極低,是真正的“一登龍門,身價百倍”。顯然,青年劉禹錫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
劉禹錫先在外省歷練,于30歲回到京城,欲大展身手。恰在此時,他遇到了生命中帶給他最大希望,同時也帶給他最大絕望的人——王叔文。所謂“二十三年棄置身”的源頭,便是王叔文領導的“永貞革新”失敗。
王叔文本是順宗的“棋待詔”,唐中期的“待詔”并非清流出身,通常是有一技之長的人,在宮中陪伴皇帝娛樂。然而,王叔文其人頗有政治野心,當順宗李誦還是太子時,便經常縱論時局,深得信賴。
順宗即位后,旋即重用王叔文等人,其中當然包括劉禹錫、柳宗元。劉禹錫堪稱王叔文的“左膀右臂”,時人號稱“二王、劉、柳”。
不久,順宗身疾,在宦官和敵對官僚的運作下,順宗被動禪位于憲宗,史稱“永貞內禪”。政局本來便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憲宗為鞏固權柄,自然要任用自己的心腹;更何況王叔文出身微末,為士大夫清流所不齒。如此,全然依附于順宗皇權的王叔文集團,命運天翻地覆。
劉、柳等人皆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更絕望的是,元和元年(806),朝廷詔令“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亦即無論如何,難以赦免減罪。毫無疑問,憲宗對于順宗舊臣,采用了超絕的態度,詔令也基本宣告劉禹錫等人政治生命的完結。
暫憑杯酒長精神
政治風波改變了劉禹錫的人生走向,但真摯的友情,卻在余生中不斷慰藉和鼓舞著他。這未嘗不是一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劉禹錫的好友包括“老戰友”柳宗元、詩歌并稱“劉白”的白居易、共倡古文的韓愈等一連串文化名人。劉禹錫與柳宗元的交往,當屬君子知己的典范,兩人關于“天人之際”的討論,在中古思想史上閃耀“光芒”;而柳宗元三十卷詩文作品,有賴于劉禹錫花費大量精力編纂的《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紀》保留。只可惜,隨著47歲的柳宗元撒手人寰,兩人陰陽兩隔。
客觀而言,劉禹錫在后半生交流最密切、給予他最多鼓舞的好友當數白居易。劉禹錫23年的貶謫生涯中,二人的交往逐漸密切。
以唐宋觀,判斷官員起落,主要察其任職之地。大致而言,離國都愈遠愈差,經濟、軍事地位高者好于低者。劉禹錫的貶謫可分為四段,分別是:元和元年(806),任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元和十年(815),任連州(今廣東清遠)刺史;長慶元年(821),任夔州(今重慶奉節)刺史;長慶四年(824),任和州(今安徽和縣)刺史。大和元年(827),回東都洛陽任主客郎中。
朗州的九年歲月,劉禹錫收集民歌,與友人通信,度過寂寥的歲月。其后,劉禹錫在連州四年余,因母喪離開連州,回洛陽丁憂。在連州,他依舊保持在朗州的狀態——創作詩文,與好友互通有無。
當劉禹錫于長慶四年(824)調任和州刺史時,年過半百的他,已經歷妻子薛氏、王叔文、柳宗元、韓愈先后離世,加之政治形勢的反反復復,已經多了幾分淡然。正如他后來在給白居易的詩中寫道:“游人莫笑白頭醉,老醉花間有幾人?”劉禹錫無非是在蹉跎與落寞中,等待命運的轉機。
歸來還見曲江春
“前度劉郎”可謂文學史上最著名的典故之一,故事的發生地點——長安的玄都觀,卻是劉禹錫一則以喜、一則以悲的感慨之地。
元和九年(814),身處朗州的劉禹錫奉命回京,仕途似乎峰回路轉。他激動地寫道:“十年楚水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關于此次回京,普遍認為憲宗在臣僚建議下,意欲重用舊人。
然而,劉禹錫此次未能擺脫“永貞舊黨”的陰影。他來到長安的玄都觀,回憶起自己在貞元二十一年(805)曾游覽此地,時光易逝,物是人非,于是創作絕句: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
這本是一首有感而發的詩作,卻被別有用心的人指摘,向武元衡報告說劉禹錫詩涉諷刺,抱怨牢騷。偏偏此時執政的武元衡,身份極為敏感,當年王叔文執政,將武元衡貶官,自此元衡終其一生,都與劉、柳等人不睦。此時有人煽風點火,自然勾起往昔不愉快的記憶。于是,元和十年(815),劉禹錫再次被貶為播州(今貴州遵義)刺史。
斯時,武元衡的副手、后世賢相典范裴度,以御史中丞的身份,為劉禹錫求情——劉禹錫要贍養80歲老母,攜母前往荒蠻的播州,對老人家而言九死一生,有違孝道。最終,憲宗在猶豫之下,還是將劉禹錫改貶連州(今廣東清遠)刺史,算是稍加體恤。裴度為劉禹錫的陳情,便是二人關系的絕好體現。不同于武元衡,裴度終其一生與劉禹錫保持著良好的關系,晚年更有人生知己的意味。
寶歷二年(826),劉禹錫終于被調回洛陽,任主客郎中一職。此官屬于閑職,實權不多,但地位待遇尚佳,后又以集賢殿學士的頭銜,整理典籍,倒也符合劉禹錫此時的心境。其實,劉禹錫能夠在晚年善終,多賴宰相裴度的薦舉。裴度一生功績卓著,分別于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拜相,煊赫一時。多虧裴度的提攜,劉禹錫才有機會成為“劉賓客”“劉尚書”,而在政局之中浮沉數十載的裴度,也必然理解劉禹錫的寥落與遺憾。
太和二年(828),劉禹錫故地重游,再于玄都觀題詩云:“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過盡千帆,前度劉郎,晚年歸來,心境究竟如何?其人又是否有所改變?
劉禹錫也許沒有變——他始終沒有放棄對歷史、政治、家國的思考;文宗召其交談,遣職蘇州,臨行之時,姚合說他“三十年來天下名”;晚年到任蘇州,劉禹錫積極行事,疏浚水災,政績卓著,文宗后賜金紫魚袋,加以表彰。他用自己的行動,踐行著“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的詩句。
劉禹錫也許改變了——他以七十高齡創作《子劉子自傳》,文中絲毫沒有表現他作為“詩豪”的一面,只是羅列晚年擔任的重要官職,作為自己的“蓋棺定論”,乍看上去,仿若一位平平無奇的官僚。也許,對劉禹錫而言,他的一生,終究有未盡其能的遺憾,正如其晚年所言“以閑為自在,將壽補蹉跎”,悲愴與失意在所難免。
(摘自《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