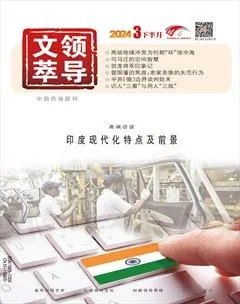乾隆為何要敕修《貳臣傳》
卜鍵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日,皇帝弘歷諭稱翻閱《明末諸臣奏疏》,語多可采,不必全禁,而王永吉、龔鼎孳、吳偉業(yè)等“其人既不足齒,則其言不當復存,自應概從刪削”。那是四庫開館的第五個年頭,伴隨而起的還有禁書潮,弘歷認為王永吉等在降順后雖也曾效力,但大節(jié)有虧,不可與大清開國元勛并列,命國史館另立《貳臣傳》一門。收錄的原則為“在明已登仕版,又復身仕本朝”,即所謂兩仕。
招降納叛,實乃每一個新王朝興起過程中的必要舉措,大清亦然,曾對明朝大臣和邊將極力收買羅致,多多益善。而在建國定鼎之后,功績卓著者寫入國史,并不區(qū)分原屬本部還是敵方。忽忽一百多年過去了,設立《貳臣傳》無疑為一種羞辱,爾輩雖已化煙化灰,其后嗣則大量存在,乾隆究竟要干什么?
厭惡錢謙益
比較起來,在晚明備受傾軋,不得已退居常熟的原禮部侍郎錢謙益投降略晚:順治二年(弘光元年)五月十五日,清軍進入放棄抵抗的南京城,弘光朝禮部尚書錢謙益與幾位公侯勛裔在大雨中迎降,“褰裳跪道旁”。據說柳如是曾力勸其投水自盡,他伸手摸了摸,以水太涼拒絕,而好友河南巡撫越其杰、參政袁樞皆絕粒而亡。朝廷很快任命錢謙益為禮部右侍郎,兼明史館副總裁,約半年稱病辭歸。之后,錢氏兩次入獄,放出后仍與南明政權頻頻聯(lián)系,參與反清活動,也在詩文中抒發(fā)對新朝的不滿,其時文網不密,竟也僥幸活到八十三歲。
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甚受弘歷禮遇的老臣沈德潛進京為皇太后祝壽,上呈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求皇上題序。弘歷隨手披閱,見以錢謙益冠首,加上排序、避諱等問題,遂命南書房翰林逐頁審核,重加編定。應是見老沈對錢氏吹捧太過(如“推激氣節(jié),感慨興亡,多有關風教”),上諭中特別提到錢謙益:“伊在前明曾任大僚,復仕國朝,人品尚何足論!即以詩言,任其還之明末可耳,何得引為開代詩人之首?”除責備沈氏年老昏聵,乾隆也對兩江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陳宏謀未加規(guī)正予以訓斥。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乾隆翻閱錢謙益的《初學集》《有學集》,越看越氣,認為對清朝多有詆謗,即加痛斥:“錢謙益果終為明臣,守死不變,即以筆墨騰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為本朝臣仆,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列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jié)之羞,尤為可鄙可恥!”諭令各督撫等廣發(fā)告示,盡行收繳,將書版解送京師,并命京城地面由九門提督、巡城御史嚴密稽查。
至四庫開館,從繳進圖書中發(fā)現違礙作品,弘歷降諭各省查辦,再一次強調提出品節(jié)問題,指斥錢謙益身仕兩朝,不能死節(jié),禁毀其書意在“勵臣節(jié)而正人心”;而“劉宗周、黃道周立朝守正,風節(jié)凜然,其奏議慷慨極言,忠盡溢于簡牘,卒之以身殉國,不愧一代完人”。他歷來心思縝密,想到沈德潛雖逝,其家可能保存《國朝詩別裁集》原刻本,傳諭江蘇巡撫楊魁速查明回奏,并再一次提及“集內將身事兩朝、有才無行之錢謙益居首,有乖千秋公論”,可謂厭憎入骨。
特設立《貳臣傳》
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二月初三日,乾隆諭令國史館編纂一部曠古未有的《貳臣傳》。閣部大臣遵旨集議“明季殉節(jié)諸臣謚典”,擬分為專謚、通謚兩類:“其生平大節(jié)卓然,又艱貞自靖者,宜特予褒崇,按名定謚;其平時無甚表見,而慷慨致命,則匯入通謚之例。”乾隆認為“于崇獎忠貞、風勵臣節(jié)之道,已無遺憾”,賜題《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交武英殿刊刻頒行。
而與之相映襯,乃欽命編纂一部《貳臣傳》。當初對明臣的招降本屬費盡心機,就連皇太極也不惜降尊紆貴,此時則以“望風歸附”概括之。弘歷也稍加區(qū)分,先是遼東交兵時期的洪承疇、祖大壽,再是定鼎北京時的馮銓、王鐸等人,然后才輪到南明總兵田雄與將軍左夢庚,次第分明。畢竟已是乾隆朝,可以撇開利用價值論人了,弘歷將之提升至品節(jié)的高度,認為爾輩在故國危亡之際貪生怕死,實在是人格有虧。諭旨稱這些人雖為本朝立下大功,但不應與范文同等純臣并列,也不宜忽略不計,準情酌理,特設立《貳臣傳》一門。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清初貳臣頗有因功授爵者,子嗣承繼,也至于高位。如時任兩廣總督李侍堯,其四世祖李永芳就是貳臣,萬歷末以撫順游擊獻城而降,是為第一個投降的明朝邊將。弘歷略加安撫,表明其后代“原在世臣之列,受恩無替”,接著就強調此舉意在公平修史,在于為世人樹立一個品節(jié)綱常的標桿。
不知貳臣之后有多少正在朝為官,原來的家族榮耀化為恥辱,百口莫辯,也無人敢辯,試想李侍堯等又能說些什么呢?
貳臣的再分類
乾隆四十三年(1778)二月,應是在翻閱了部分文稿后,乾隆命將《貳臣傳》分為甲乙。
同為貳臣,差別實際上很大。弘歷認為洪承疇、祖大壽、李永芳等歸附后勛績昭著,忠于大清,應列入甲編;而像龔鼎孳之類先降大順軍再降清軍、貳而又貳者,以及錢謙益這種帶頭歸降、觍然受官又私下寫詩詆毀之流,只可列入乙編。
貳臣,實乃一個久遠且普遍的存在,歷朝修史皆將之附入列傳,而單設一門,再分甲乙,實屬弘歷的創(chuàng)立。編纂過程中,乾隆又發(fā)現新問題:“沖冠一怒為紅顏”的明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降清后封平西王,復舉兵叛亂,數年始定,可列入《貳臣傳》乎?經過思考甄量,乾隆決定再加區(qū)分:“惟《貳臣傳》一門,前經降旨另編甲乙,乃我朝開創(chuàng)所有。此實扶植綱常,為世道人心之計,自應另立專門,以存直道。至叛逆之臣如吳三桂等,亦應明正罪狀,另立一門,用昭斧鉞之嚴。”至五十四年(1789)歲末,乾隆諭令:“特立《逆臣傳》,另為一編,庶使叛逆之徒,不得與諸臣并登汗簡;而生平穢跡,亦難逃斧鉞之誅。”不光要為錢謙益等貳臣立傳,也要為吳三桂這樣的逆賊立傳,看來弘歷是想明白了,把一大堆難題拋給了史官。
忠貞的意義
設立《貳臣傳》,弘歷一再宣稱為的是“昭褒貶之公”,即公平客觀地評價歷史人物。應予追問的是,怎樣才能做到評價的公正?褒貶之依據又是什么?
首在品節(jié)。
對于國之大臣,忠誠堅貞,實乃品節(jié)之大端。曾任南書房翰林的朱珪有句話值得注意:“賜勝朝守節(jié)之謚,以顯忠也;貳臣有傳,以勵貞也。”此人立朝清正,以人品學問深得弘歷信任,他將《貳臣傳》與此前的《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合并論列,可謂抓住了關鍵。
乾隆敕修二書時,清朝臻于極盛,而衰象亦顯,突出表現為貪腐滋蔓、叛亂時起。有的學者以為弘歷已有危機感,故而拿著貳臣做文章,實則未必。更可能的是:由于對興修《四庫全書》的重視,他集中閱讀儒家經典,大量翻閱明末奏議和遺民著述,亦重新思考前明的敗亡和本朝的興起,看到了明末群臣的品節(jié)差異,也看清了忠貞的意義。褒揚忠貞不貳,貶斥投降變節(jié),從來都是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的評判原則,而非國難當頭時的臨時需要,不是嗎?
如果說乾隆此舉的特別之處,應在于他試圖將臣子的品節(jié)標桿化。《勝朝殉節(jié)諸臣錄》系為忠臣立傳,大節(jié)卓然、艱貞自靖者“按名定謚”(即專謚),唯有史可法一人的謚號為“忠正”,置諸頂端;而對那些平日未見杰出、臨事慷慨效命者予以通謚,再細分為忠烈、忠節(jié)、節(jié)愍、烈愍,各有刻度。至于《貳臣傳》,則可視為變節(jié)者的恥辱柱,又因叛附時情勢懸絕、降清后作為不同,分為甲編和乙編,那位被譏為“非人類”的錢謙益當處于柱之底端。至于吳三桂,則被從《貳臣傳》除名,列為《逆臣傳》之首。
品節(jié),本來就具有層級的義項,以之紀事論人,法度儼然,刻度判然。乾隆將之作為官修國史的重要標尺,值得關注和研究。而人性的千差萬別,易代之際的復雜錯綜,使得評判很難,量化尤難。如清太祖努爾哈赤,也曾被明朝封為龍虎將軍,“給都督敕書”,其算貳臣乎?逆臣乎?
(摘自《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