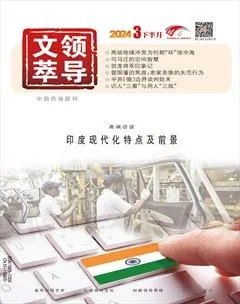逆境和腳手架
萬維鋼
一
不知道你有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困境:某一天你突然發現,自己的能力,好像到頭了。
你不是不勤奮,可是成績突然就不再提高了,怎么練都難以寸進,你進入了死胡同。
是不是繼續加倍努力,堅持堅持再堅持,奇跡就會出現?我想告訴你,那是沒前途的,科學證據支持的是,成長遭遇平臺期,其實是個正常現象。人人都會經歷這一步,而且不止一次。兩個認知科學家,韋恩·格雷和約翰·林德施泰特考察了一百多年間有關進步的各種數據后,發現一個規律——成績停滯不前的時候,你要想再提高,就必須先讓成績降下來。你得以退為進。
這是因為你必須換方法。舊方法只能讓你走這么遠,而新方法你還不熟練,所以剛換方法的時候你的成績一定會下降,下降代表進步。
比如,打字。如果一開始學打字你是眼睛盯著鍵盤打,很快就能達到每分鐘三四十個單詞的水平……然后你就到了平臺期,你發現再怎么練也不能提高了。這時候你就得換方法,改成盲打,眼睛只看屏幕不看鍵盤。盲打會讓你的成績下降,你需要適應,但是只有這樣你才可能突破瓶頸。
這個道理簡單吧?問題是,方法不是說換就能換的,你需要幫助。
二
職業棒球投球手R.A.迪奇(以下簡稱RA)上初中的時候就被視為棒球天才,高中時候就有專業球探來看他比賽,大學期間代表美國國家隊拿了一塊奧運會銅牌,然后被得克薩斯游騎兵隊在選秀首輪選中,據說光是簽字費就有八十萬美元。
然而就在即將簽約之前,游騎兵隊查出RA的手臂有問題。他的右肘缺了一條韌帶。這使得他的投球速度將會有一個很低的上限。游騎兵隊還是留下了RA,但是簽字費改為八萬美元,而且把他下放到了小聯盟。你要是能練出來,我們保留一個希望;你要練不出來,這筆投資損失也不大。
RA當然不甘心,他想了一個辦法。我手臂力量不夠,那我能不能投聰明球呢?RA嘗試每次投球給出不同的速度和旋轉,這樣能迷惑對方的擊球手。這招見效了,他在小聯盟打出了名堂。七年后,游騎兵隊把RA召回了大聯盟。
然而故事沒有這么簡單。RA那些招數對大聯盟的擊球手不太好使,他表現平平,三個賽季之后又被下放到小聯盟。然后RA繼續苦練,他練到了癡狂的程度,開車時都得拿個球找手感……于是游騎兵隊又給了他一次機會。然后他又失敗了。
此時的RA已經31歲,別的投球手到了這個歲數都快退役了。命運的曲折都可以忍,問題是,RA好像怎么練都再也無法提高。
就在最后一次被下放到小聯盟的時候,RA的投球教練給了他一個模糊的指點。教練說,你這個投法是不可能再回到大聯盟的,但是我發現你有時候能投出一種“怪球”。多年來江湖中一直傳說有一種“指節球”,又叫“蝴蝶球”,投出去之后不走直線,會左右搖擺,讓擊球手無所適從。你那個怪球好像有點那個意思。要不你練練指節球?
那種球確實存在。棒球的正統投法,是用手指把球包住,用力投出的一剎那手腕上加一個轉動,給球一個強烈的旋轉。這樣球的路線穩定,指哪兒打哪兒。指節球,卻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甲摳著球投,刻意地不讓球旋轉。這樣的球出去之后,球自身的縫線區域和光滑區域在空氣中會產生不同的湍流,這些小湍流會給球一個不確定的擾動,結果就是一種“之”字形的路線。不但擊球手難以捕捉指節球,連捕手都得換個特大號的手套才能接到球。
指節球還有個好處是對速度和力量要求不高,這就延長了投手的運動壽命,而這恰好最適合RA。但問題是,教練不知道怎么練指節球。
沒有人確切知道。為了練指節球,RA必須先忘記熟練的投法,重新學習。
RA開始到處拜師求教。的確曾經有十幾個球員成功投出過指節球,但是他們大都退役了,現在大聯盟只有一個現役球員會投指節球。所有這些人的功夫都不成系統,沒有人總結理論。RA 一個個登門求教,這些人也都傾囊相授。特別是那個現役球員,等于把自己的商業秘密告訴了RA……
RA像海綿一樣吸收和過濾信息,終于練成了自己獨有的指節球投法。
那些幫助RA的人給他提供了一個“腳手架”。你向上攀登,遇到障礙可能靠自己過不去,你需要找個腳手架借力,英雄不能只靠自己。
35歲這一年,RA重返大聯盟。
37歲時,RA已經是大聯盟的精英級球員,但他還想再進一步。職業生涯到了這個程度就已經不是技藝水平的問題了,需要心態上的突破。
這次,RA找到的腳手架是攀登非洲最高峰——乞力馬扎羅山。那是他兒時的夢想,而且他還給此行搞了個特別的意義:只要他能登頂,贊助商會籌集一筆錢用于慈善事業。
這個活動非常冒險,但RA用了七天,登頂了。他在山頂深切感受到自己比任何時候都要渺小,而“這種感覺令人陶醉”。
也許是登山帶來的渺小感和慈善事業的貢獻感提高了RA的上限,下山后,RA打出了職業生涯中表現最好的一個賽季,創造了好幾項紀錄。
改變路線、尋求指點、互相幫助——遇到進步瓶頸的時候,想想你有哪些“腳手架”吧。
(摘自“得到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