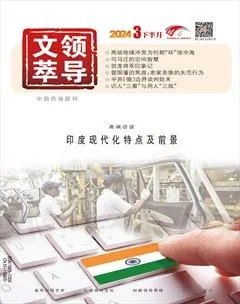說好官話好做官
講歷史的王老師

古代有普通話嗎
官話至少在周朝時候就出現了。分封制下,各個諸侯國相對獨立,割據狀態下,各個諸侯國語言交流相對封閉,發音差距越來越大,長此以往就形成了地域性的方言。《左傳》記載:“衛侯歸,效夷言。”衛侯曾被吳國扣留,回國后口音就變了,居然說起了吳國的“夷言”。這說明春秋時期衛國和吳國的方言發音差距很大,一聽就不一樣。
諸侯國方言各異,但彼此的交流又很密切,特別是在政治上都尊奉周王室為正宗,要定期朝貢,所以大家需要一種各國都能聽得懂的方言用作交際,“標準音”應運而生。到底用哪種方言作為標準音呢?這就是一個政治問題了,必須給“大哥”周王室留點面子,所以標準音只能用周王室的方言。周王室使用河南地區的“洛陽音”,洛陽話就成為最早的普通話。
先秦時期的洛陽音,在當時被稱為“雅言”,因為它的發音被認為很優雅。漢朝時,洛陽依舊是文化中心,在東漢時期還成了首都,所以洛陽音作為標準音的地位在漢代得以延續。然而,洛陽音也分很多種,就像今天的北京話,既有京片子里的“您猜怎么著”之類的市井俗音,也有《新聞聯播》里“觀眾朋友們晚上好”的官方標準音。當時最正宗的洛陽音是洛陽太學里學生們讀書的聲音,被認為最文雅、最好聽、最標準,得名“洛陽讀書音”。
東晉十六國及南北朝時期,中國陷入數百年的大分裂狀態,漢語標準音也發生了分化,形成了北方的“洛陽音”和南方的“金陵音”。受到游牧民族進入中原的影響,北方的洛陽音發生了一些變化。另外,大量中原漢人南遷,在金陵(今天的南京)建立了政權,把洛陽音也帶到了南方。根據史料記載,南方的原住民聽到這種北方語音后瞬間陶醉,盛贊洛陽音“真香”,并掀起了學習熱潮。南遷貴族謝安,能用標準的洛陽音讀書,被稱為“洛下書生詠”,當地人爭相模仿。甚至連謝安因鼻炎而特有的鼻音,也都一起學了。
隋唐時期,中國再次實現統一。盡管首都在長安,但文化中心和經濟中心則在洛陽,洛陽音依舊是漢語標準音,成為官話。如今去西安旅游,經常會有導游自豪地說“唐朝皇帝都講陜西話”,一張嘴就是“額們大唐”。其實這是一個誤解,唐朝的皇帝、大臣講的其實是洛陽音,并非長安音,更不可能是今天的陜西話。唐朝的長安音又稱“秦音”,當時上層社會認為其發音“很土”。武則天當政時期,有個大臣叫侯思止,他讀書少且不擅長講洛陽音。一次在朝堂之上,當他說到“豬”這個字的時候,沒有按照洛陽音讀“dyo”(音似“雕”),而是發出了秦音“jyu”(音似“誅”),引得滿堂大臣一片哄笑。此事說明,說好普通話在當時很重要。
因此,一直到宋朝,漢語的標準音都是洛陽音,延續了兩千多年,宋朝之后,北方少數民族頻繁入主中原,并出現了元朝和清朝這樣的全國性政權。游牧民族本不講漢語,但成為中原大地的統治者后,他們不得不學習如何講漢語。其發音到底“味道”如何,可以腦補今天外國人講漢語的樣子。但由于擁有政治優勢,統治者所講的“有味道的漢語”不可避免地影響著漢語的發音。此外,元明清三朝的首都都在今天的北京,洛陽在中原的“大哥地位”一落千丈,遠離政治中心的洛陽音逐漸在歷史中謝幕。
元明清三朝的官話是哪一種方言呢?元朝時北京稱大都,當時講幽燕地區(今天的京津冀加遼寧和內蒙古)的方言。這種方言再加上點蒙古語的味道,就形成了元朝的官話——大都音。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又將官話改回金陵音。可沒多久,發生了靖難之役,朱棣上臺后遷都北平(后改稱北京),金陵音同大都音融合,形成了明朝的北京官話。清朝建立后,滿洲人入主北京,又在明朝北京官話中融入了滿語和東北話的味道,融合形成了清朝的北京官話。到清朝中期,北京官話已通行全國。我們今天講的普通話,就源于清朝的北京官話。
古人如何學普通話
古人,特別是讀書人和官員要學習普通話,即當時的官話。古人是如何學習普通話的呢?首先,官方會編訂和發行漢語標準音的書籍。其次,古代的學校教育都會盡量使用官話教學,對讀書人推廣普通話。會講官話是古代讀書人的必備技能,也是識別知識分子的重要標志。所以,古代的文盲一般沒法和讀書人爭論,因為一開口就暴露了文盲的知識水平,讀書人是懶得和他抬杠的。
最后,統治者會要求官員階層熟練掌握官話,以此作為官員是否勝任的標準。清朝時,官員必須會說北京官話,特別是那些想當大官的。因為你將來可能會面見皇上匯報工作,如果你操著一口方言,皇上聽不懂啊!雖說清朝皇帝文化水平較高,能說滿、漢、蒙古等多種語言,但面對中國龐雜的方言體系,他們實在招架不住。
清朝時,皇上對于廣東人和福建人的講話最吃不消,完全聽不懂。雍正皇帝特意為此下發過諭旨,大意是說:“每次引見臣子,只有福建、廣東兩省的人仍然操著鄉音,說的話讓人聽不明白。這些人已經通過了科舉考試和吏部培訓,但是在大殿之上說話依舊說不清楚,這要是去別的省赴任怎么能做好父母官呢?這可不僅僅是我聽不懂的問題,而是百姓聽不懂的重要問題!”
雍正皇帝對官員學習官話高度重視,將其重要性上升到治國安民的政治高度,地方政府自然不敢怠慢。廣東、福建兩地各級官府迅速落實整改工作,掀起了一場大清朝的“學習官話運動”。為了加快讀書人和官員群體學習官話,各地政府紛紛辦起了“官話培訓班”,名為“正音書院”。福建開辦了一百一十二所,廣東估計高達上千所。書院多用當地駐防旗人任教,招收當地舉人和秀才學習。清廷甚至還規定了學成年限,以八年為限,如果學不好,學員將會被暫停科舉考試資格。
通過上述方式,古代的讀書人和官員群體都能一定程度地使用普通話。但是,對于人數眾多的普通百姓,講普通話還是太難了。由于清朝有官員任職的回避制度——官員不能在本鄉任職,所以地方官一般不會懂本地方言,這就極易造成官民間的溝通障礙。這時候就只能用翻譯了。是的,你沒聽錯!同是漢語,不同的方言之間需要用翻譯來溝通。《六字課齋卑議》就記載過清朝政府的規定:“所有土話與官話歧異縣份,知縣到任,著延方言師一人。”這里的方言師就是翻譯,是地方官到任時的標配。然而,用翻譯只能是權宜之計,為了更好地深入群眾,清朝政府還規定地方官要“每日從學土話二點鐘,成而止”。地方官必須學會本地的方言,對于那些在廣東和福建任職的父母官,真是有點吃不消啊!
(摘自《古代人的日常生活》)
中國人不容易像西方人那樣因為上帝之死而失魂落魄,也許是因為虛無主義本來就潛伏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里了。西方的虛無主義是即興的,中國的虛無主義則是慢性的;西方的虛無主義是自覺的,中國的虛無主義是隨性的。中國的虛無主義者往往對虛無主義本身也持一種可有可無的、虛無主義的態度。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教授童世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