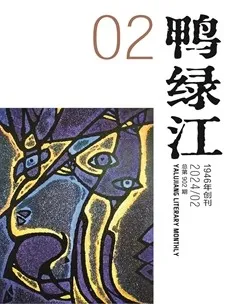1985年的愛情
邱大龍參加頭一年的高考,落榜了。這不丟人,那個(gè)年月,萬人過獨(dú)木橋,能過去的是極少數(shù),留在此岸的也用不著變聲變色。但邱大龍還是失落了好久。倒不是他學(xué)習(xí)多好,沒有發(fā)揮出水平,主要是他有過很大的理想。當(dāng)年在看過手抄本小說《第二次握手》后,他就夢想著像主人公那樣能上北大物理系,然后當(dāng)科學(xué)家。這個(gè)理想雖然有些縹緲,有些不著邊際,但實(shí)實(shí)在在有過,所以落榜后多少有點(diǎn)理想破滅的感覺。他聲稱要復(fù)讀,可內(nèi)心對(duì)這個(gè)選擇并不篤定,反而有些虛勢聲張的意味,還有點(diǎn)外強(qiáng)中干的虛套。
就這樣在躊躇中蹉跎了一陣子,舅舅興高采烈地來找他,說工商局在應(yīng)屆畢業(yè)生中招干,通過關(guān)系搞到一個(gè)指標(biāo),讓他趕緊準(zhǔn)備考試。其實(shí)也就是走一個(gè)過場,錄取肯定沒問題。舅舅本以為邱大龍會(huì)喜出望外,沒想到這小子沒什么反應(yīng),還拿三捏四地說不想去還要復(fù)讀繼續(xù)高考云云,氣得舅舅一下子蹦了起來。舅舅比他大十幾歲,從小帶他玩,他倆之間既是舅甥,又似哥弟,說話就不客氣了。舅舅說你小子做什么白日夢呢,就你那點(diǎn)水兒,明年就能考上?為了這個(gè)指標(biāo),你知道我費(fèi)了多大勁?再說就算考上個(gè)破大學(xué),畢業(yè)了指不定分到哪兒,想上工商局也沒那么容易,何況一上班就是干部,過了這個(gè)村可沒這樣的好事了,你別不知道好歹!一直小心翼翼安慰他的父母也立馬變了臉,說明年再考不上自己掙錢養(yǎng)活自己,我們養(yǎng)你這么大也夠了。到了這個(gè)時(shí)候,邱大龍也只得順坡下驢,很不情愿地答應(yīng)了。
事實(shí)證明了舅舅的高瞻遠(yuǎn)矚,許多年后,多少名校畢業(yè)生,甚至碩士研究生要進(jìn)工商局,必須經(jīng)過嚴(yán)格的公考,層層過關(guān),好比萬人過獨(dú)木橋。
僅剩下的那點(diǎn)遺憾,在上班前的業(yè)務(wù)培訓(xùn)開始后,很快也煙消云散了。七十多個(gè)年輕人,有男有女,都是一色的落榜生,沒有任何落差和陌生感,就好似上高中那會(huì)兒,重新打亂分了一次班,并且宣布不用高考上大學(xué)了,直接分配工作。這是多么幸福的事啊!邱大龍因?yàn)榭催^些雜七雜八的書,懂得多,愛琢磨,凡事都能說出個(gè)一二三四,又高大帥氣,就當(dāng)了班長,很快有了一幫能玩到一起的伙伴,心情不禁大好。
一天課間休息,黑子找到邱大龍,說晚上出去搓一頓。邱大龍說好。食堂的大鍋飯油水太寡,他們時(shí)不時(shí)出去找地方改善改善。其實(shí)也不用找,培訓(xùn)的地方偏僻,附近就一家川菜館,飯菜做得還有些滋味,是他們常聚的地方。黑子招呼了七個(gè)人,其中有兩個(gè)女同學(xué),一個(gè)是他的高中同學(xué)何玲,另一個(gè)是他現(xiàn)在的同桌。一伙人吆吆喝喝舉起酒杯,不一會(huì)兒,靠墻擺滿了一圈啤酒瓶。
酒桌上的女士很容易成為焦點(diǎn),有酒精撐腰,男人們也就脫去了靦腆的外衣。面對(duì)輪番轟炸,何玲很有主意,說自己不會(huì)喝酒,一杯的量,再多就出洋相了。黑子觍著臉說:“沒見過你出洋相,出一個(gè)也讓我們開開眼唄。”別看何玲長得文文靜靜,話說出來毫不留情面:“我出洋相你能得著什么便宜?就你那三塊豆腐干樣兒,還想來消遣我?”一句話把黑子噎得滿臉通紅。黑子其實(shí)姓白,白建國這名字叫起來挺響亮,細(xì)琢磨卻不夠昂揚(yáng)向上,還有點(diǎn)消極。他個(gè)子矮,五官也沒太長開,膚色不夠明亮,照相要開大一檔光圈,嘴還貧,所以在很多場合都會(huì)成為調(diào)侃對(duì)象。邱大龍見局面尷尬,端起一杯酒說:“這樣何玲,你給點(diǎn)面子,我陪你倆把這杯酒干了,后面誰再跟你喝我都替了。”“說話算數(shù)?”“一口唾沫一顆釘,絕對(duì)算數(shù)。”三個(gè)人喝了酒,桌上又鬧哄起來。
英雄好漢也不是隨便當(dāng)?shù)摹R粫r(shí)間大家的矛頭又都對(duì)準(zhǔn)了邱大龍,饒是他酒量不小,結(jié)束后也不禁有些踉踉蹌蹌。旁邊的何玲連忙一把攙住。女同桌也喝了不少,走路有點(diǎn)搖晃,不得不把手就近搭在一位同學(xué)肩上。黑子左瞧瞧,右看看,有些失落,又有點(diǎn)興奮,出了門大聲說道:“咱們唱個(gè)歌吧,《年輕的朋友來相會(huì)》怎么樣?”不知誰就開頭唱了起來:“年輕的朋友們,我們來相會(huì),蕩起小船兒,暖風(fēng)輕輕吹……”于是別人也就跟著唱。大家都喝多了酒,嗓子充血,聲音都跟劈了似的。一伙歪歪扭扭的身影,走在夜間空曠的鄉(xiāng)野小路上,發(fā)出狼嚎一般的聲音。一條在垃圾堆里覓食的狗受了驚,跳到路上,盯著看了一會(huì)兒,扭身逃得無影無蹤了。
這次聚會(huì)以后,邱大龍對(duì)何玲有了一種異樣的感覺,上課的時(shí)候,不由自主就會(huì)用眼睛的余光看向前排的何玲,她腦后那只蝴蝶形的發(fā)卡就像活了一般總在眼前飛舞,被攙過的胳膊有一種熱乎乎麻酥酥的感覺,而且這種感覺不斷向全身蔓延……他不知道這算不算是朦朧的愛情,或者是一廂情愿的暗戀。那個(gè)年代,中學(xué)生戀愛還是禁區(qū),個(gè)別搭訕或遞條子給女生的,必定是調(diào)皮搗蛋的壞孩子,會(huì)受到一致的鄙視和唾棄。這樣的事對(duì)于在正統(tǒng)家庭長大的邱大龍來說連想都沒敢想過。如今雖然走上社會(huì),但那種早戀的恥感還沒有完全消除。他不知道該不該,更不知道怎樣來表達(dá)對(duì)何玲與眾不同的渴望。倒是何玲,好像并不在意這些,星期天從家里帶回來蘋果、栗子和其他吃食,毫不避諱地拿到邱大龍宿舍:“給你的,讓你的狐朋狗友也嘗嘗。”室友們就起哄:“為什么是邱大龍而不是我們?”何玲也不羞澀:“他英雄救美,我不該報(bào)答一下?”室友們更加起哄:“是以身相許還是來世再報(bào)?”何玲笑著嗔道:“去去,這些吃的還堵不住你們的臭嘴?”
邱大龍很是慚愧,自己一個(gè)男子漢,竟不如一個(gè)女生敞亮大方。轉(zhuǎn)念又想,也許人家純粹就是心地單純沒有“雜念”吧。
后來有了一次單獨(dú)相處,是在公交車上。那天剛上車的邱大龍,在稀稀拉拉的乘客中看到何玲。何玲也看到了他。他從何玲的眼神中看到了驚喜,于是挨坐在一起,雖然只是沒話找話地說了些家住哪里天氣真冷之類不咸不淡的話,但邱大龍心里還是美滋滋的,就像經(jīng)歷了一場約會(huì)。臨下車,邱大龍遞過裝著飯盒的塑料袋:“我媽包的芹菜餡餃子,可香了,你拿去吃吧。”何玲掩嘴一笑:“不好意思,我從小不吃芹菜。”邱大龍也笑了:“下次包韭菜雞蛋餡的。”
三個(gè)月的培訓(xùn)結(jié)束了,有六個(gè)學(xué)員留在市局機(jī)關(guān),邱大龍和黑子分在辦公室,何玲去了市場科。宣布完分配方案,邱大龍注意到何玲回頭掃了他一眼,臉上帶著一抹欣喜,還有一點(diǎn)羞澀。
報(bào)到第二天,邱大龍?jiān)缭缟习啵拿亟M這屋還有辦公室副主任老魯和兼職黨辦主任張姐。他剛擦完地板,一個(gè)很有氣度的胖老哥徑直進(jìn)來,反客為主地示意他坐下,張口問道:“小邱是吧?有對(duì)象了嗎?”邱大龍不知道這是個(gè)什么領(lǐng)導(dǎo),問的話更讓他突兀,一時(shí)間摸不著頭腦。他想到了何玲——這算不算是對(duì)象呢?心里沒底,因此有點(diǎn)不知道如何回答。對(duì)方見他猶豫且面露羞澀,頗為理解地說:“有了是吧?那就好好處。我手頭有好幾個(gè)女孩子,都挺優(yōu)秀,以后有需要幫忙隨時(shí)找我。哦,我是消協(xié)老趙。”邱大龍覺得挺好笑,但又不好意思笑出來,只得說聲“謝謝”。抬頭正看見黑子從門口經(jīng)過,就招手喊過來,說:“這位老哥要給你介紹對(duì)象,快說說你的情況。”黑子滿臉興奮,樂得嘴都合不上了,點(diǎn)頭哈腰地說:“謝謝哥,我叫白建國……”老趙盯著他看了一會(huì)兒,笑道:“小伙子不錯(cuò),有合適的我一定給你介紹一個(gè)啊。”
正說著,張姐進(jìn)了辦公室,見此情景,虎著臉對(duì)老趙沒好氣地說:“又來拉皮條了?你們太閑了是吧?別把孩子們教壞了。”老趙也不惱,滿臉帶笑地說:“這話怎么說的,我是積德行善,老話不是說嘛,成就一樁婚,勝拜十座廟。”張姐把他往外趕:“去去,你真進(jìn)錯(cuò)門了,咋不開婚介所去呢?”回過頭又對(duì)邱大龍說:“別聽他的,年輕人還要以事業(yè)為重,多學(xué)習(xí)多進(jìn)步,出息大了還怕找不到對(duì)象?”沒等邱大龍說話,黑子連忙表態(tài),“大姐教導(dǎo)的是,我們一定多向前輩們學(xué)習(xí)。”
門口有人叫道:“小邱,來我辦公室一下。”見是主任老胡,邱大龍忙跟過去。老胡是轉(zhuǎn)業(yè)干部,一口四川腔,據(jù)說在部隊(duì)職務(wù)不低,很有理論水平,長得有棱有角,若不是臉上那幾顆麻子,也算一表人才。他問了邱大龍一些家庭情況,然后點(diǎn)點(diǎn)頭,語重心長地說:“我們辦公室雖然和別的科室同級(jí),但重要得多,是機(jī)關(guān)的司令部,領(lǐng)導(dǎo)的參謀部,系統(tǒng)的聯(lián)絡(luò)部,是培養(yǎng)人才的地方。你們是新鮮血液,將來還要挑大梁,要注意少說,多學(xué)多干,長了本事都是自己的,是將來吃飯的家伙。”邱大龍認(rèn)真聽著,覺得老胡這人挺實(shí)在,因?yàn)樗f的這些,跟爸媽囑咐的一模一樣。老胡又給他幾本書,讓他了解一下局里的各項(xiàng)業(yè)務(wù)工作。邱大龍剛要告辭,老胡又突然問道:“有對(duì)象了嗎?”邱大龍不明白單位的人怎么都對(duì)這個(gè)問題如此重視,鬼使神差搖了搖頭。老胡點(diǎn)點(diǎn)頭,“這樣好,年輕人要把精力多用在學(xué)習(xí)和工作上,戀愛的事不著急。”
機(jī)關(guān)和學(xué)校不同,忙的時(shí)候通宵加班,閑的時(shí)候也很無聊。午休時(shí)間,邱大龍喜歡湊到黑子辦公室,和幾個(gè)管行政后勤的小年輕打撲克。這天講好誰贏晚上誰請(qǐng)客,剛洗好牌,一抬頭,見一把手孟局長推門進(jìn)來,忙站起身,有點(diǎn)手足無措。那兩個(gè)小年輕倒很隨意,笑嘻嘻地說:“局長來兩把?”孟局長擺擺手,“你們玩,我上年紀(jì)了,中午要睡會(huì)兒,你們小點(diǎn)聲啊。”
開始還能悄聲悄色,怕打擾到隔壁的孟局長,沒一會(huì)兒就把這事忘到了腦后,高一聲低一聲地爭執(zhí),一驚一乍地出牌,直到孟局長“咚咚”敲墻,才又靜下來。打著牌,黑子說:“大龍,今天應(yīng)該你請(qǐng)我們大家。”“為什么?”“這還看不出來?”黑子故作神秘:“老胡看上你了,想找你當(dāng)上門女婿呢。”邱大龍“呸”了一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別胡說八道。”黑子愈加神秘地說:“說你聰明,其實(shí)很遲鈍。你不知道,老胡家有一對(duì)雙胞胎女兒,長得如花似玉,和你剛好般配,要不老胡對(duì)你那么好,看見你麻子坑里都帶著笑。”邱大龍心里翻個(gè)過,想起過往的種種,覺得黑子說得似乎也有那么點(diǎn)眉眼兒,嘴上卻說:“你小子花癡了吧?滿腦子都是女人,有本事你上,別拿我開涮。”其他人也跟著起哄,黑子有點(diǎn)急了:“我要有你那桃花運(yùn),早就……”門“砰”的一聲開了,孟局長氣沖沖站在門口:“讓小點(diǎn)聲,怎么回事你們?不像話。”幾個(gè)人忙住了嘴。
晚飯是黑子請(qǐng)的,除了牌友,還叫了主管的張局長和何玲。到了下班時(shí)間,老胡正給邱大龍交代修改材料的事,何玲過來喊他:“大龍,快走了,都在樓下等著呢。”老胡皺皺眉頭,看看何玲,又看看邱大龍,收拾好東西,一聲不吭出了門,把何玲搞得有點(diǎn)莫名其妙。邱大龍想起黑子的話,心中不由好笑,畢竟在機(jī)關(guān)磨煉了幾個(gè)月,心理建設(shè)已大有長進(jìn),也不管這些,和何玲有說有笑地下樓去了。
張局長也是“老轉(zhuǎn)”,挺豪爽的一個(gè)人。邱大龍第一次跟領(lǐng)導(dǎo)吃飯,端著酒恭恭敬敬站起來,“敬張局長一杯。”張局長手一揮:“弟兄們?cè)谝粔K兒,沒那么多講究,叫我老張就行了。”見邱大龍囁嚅著不好開口,一笑道:“叫局長喝三杯,叫老張喝一杯,自己選。”邱大龍想想局里那些小年輕們也“老張老張”地叫過,就一咬牙,“張哥,敬你一杯。”“好,這才是兄弟,喝。”
邱大龍生怕黑子管不住自己的嘴,又提起中午的話題,忙招呼著打圈,又替何玲喝酒。張局長笑瞇瞇地看著他倆,說我給你倆喝一杯,我覺得你倆很有夫妻相。何玲說是嗎?我咋還沒看出來呢?黑子也很知趣,接過話頭說:“你倆該敬我一杯,我還是媒人呢,你們不會(huì)忘了吧?”邱大龍看看何玲說:“黑子我跟你喝三杯。”
吃完飯時(shí)間還早,大家散去后,邱大龍對(duì)何玲說:“我送你回去吧,反正也順路。”何玲假裝不悅,說:“不順路就不送了嗎?”邱大龍嘿嘿一笑說:“只要你愿意,天天送。”何玲說:“我說過不愿意嗎?”邱大龍說:“你怎么學(xué)會(huì)抬杠了。天不冷,我們溜達(dá)著回去吧。”
一邊走一邊說,今天的話題格外豐富。不知不覺,兩個(gè)人的手拉到了一塊兒。這一刻,邱大龍覺得心里暖暖的,甜甜的,周圍的一切,稀稀拉拉的霓虹燈,過往的車輛,嘈雜的聲音,都和自己無關(guān),他只想著就這樣牽著何玲的手,一路走下去。
夏天快過完的時(shí)候,老胡把邱大龍叫到辦公室,說:“小邱啊,市政府跟師大聯(lián)合辦了個(gè)夜校大專班,本來只招科以上干部,我單獨(dú)給你要了個(gè)指標(biāo)報(bào)了名,以后咱倆就是同學(xué)了,下班簡單吃點(diǎn)飯就去上課時(shí)間正好,拿個(gè)文憑將來用得上。”
邱大龍一點(diǎn)也不想去,他和何玲的戀愛正在升溫階段,上班都忙,也不敢暴露,晚上正是約會(huì)的時(shí)候,誰愿意天天去上那勞什子課?他甚至想,老胡是不是看出了什么端倪,想用上課占住他的時(shí)間,阻止他和何玲交往?但又一想,也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拂了人家一番好意,再說文憑也確實(shí)有用,就答應(yīng)了。
周末上完課往回走的時(shí)候,老胡看似隨意地說:“小邱,明天中午要沒事,到我家吃個(gè)便飯吧,我老婆老家送來一只羊,咱們涮羊肉。”邱大龍心里一動(dòng),他很想看看老胡那一對(duì)雙胞胎女兒到底是如何地如花似玉,但一想已經(jīng)跟何玲約好要去正定大佛寺,忙說:“不好意思,我媽明天過生日,說好在家吃飯,改天我請(qǐng)你吧。”老胡說:“有孝心,要得。”
沒多久,開發(fā)區(qū)商務(wù)局出事了,牽涉到一樁走私案,市紀(jì)委派專案組調(diào)查,需要工商局配合,張姐建議讓邱大龍去,老魯說不行,小邱走了材料誰寫。兩個(gè)人爭來爭去誰也不讓步,張姐就去找孟局長,最后還是讓邱大龍去了。開發(fā)區(qū)離市區(qū)很遠(yuǎn),專案組工作沒時(shí)沒晌,在賓館吃住,不能回家。邱大龍和何玲聯(lián)系,要等下班后何玲辦公室沒人的時(shí)候,把電話打過去,壓低聲音匆匆說幾句話,就像地下工作者接頭一般。
一個(gè)星期天中午,老胡突然給邱大龍打來電話。一向?qū)η翊簖埡皖亹偵睦虾恢趺椿饸鉀_天,開口就問:“何玲干什么去了?”把邱大龍搞得一臉蒙,說:“何玲干什么我哪兒知道啊?”老胡說:“該她接班了現(xiàn)在也沒來,人家把電話打到我這兒了,你趕緊找找她。”邱大龍說:“我在專案組呢,上哪兒找去。”老胡有點(diǎn)蠻不講理地說:“你想辦法找,找不到你就來值班。”說完掛了電話。邱大龍一肚子怨氣沒處發(fā)泄,就打電話給張局長,把過程講了,說:“張哥你看我招誰惹誰了他來這么一通,簡直莫名其妙嘛。”張局長哈哈笑道:“這事我來處理吧,你安心工作就是了。”
專案組結(jié)束回到局里后,邱大龍還為這個(gè)電話感到別扭,何玲給他講的一件事,更讓他忐忑不安。原來,老胡為值班的事專門跟何玲談了一次話,盡管何玲解釋了因?yàn)楣卉囍型境鍪鹿实⒄`了時(shí)間,但老胡還是若有所指地批評(píng)了她,說做錯(cuò)了事情,什么原因都不叫原因,年輕人要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不要過多過早考慮個(gè)人的事,路是自己一步步走出來的,到什么時(shí)候都要嚴(yán)格要求自己。何玲越聽越氣,這哪跟哪啊,卻又無從反駁。第二天很早來到單位,擦了地,打好水,別人還沒來,看到對(duì)面桌上的毛筆硯臺(tái),就倒上墨,攤開一張報(bào)紙胡寫亂畫。腦子里還想著老胡的事,鬼使神差就一筆一畫寫:胡馬列,胡錘子,胡大麻子……正得意間,忽聽背后咳嗽一聲,接著是一口四川腔:“字寫得不錯(cuò)嘛,要得要得。”何玲頓時(shí)渾身一顫,不用看也知道是老胡。待回過頭,只看到老胡離去的背影。
邱大龍感到了事態(tài)嚴(yán)重了,如此說來,何玲或者說是他邱大龍,算是把領(lǐng)導(dǎo)老胡得罪透了。正好紀(jì)委專案組組長想把他借調(diào)去紀(jì)委工作,邱大龍就想借機(jī)會(huì)離開這個(gè)是非之地。意外的是,辦公室?guī)讉€(gè)領(lǐng)導(dǎo)意見出奇地一致:堅(jiān)決反對(duì)。為此孟局長還專門給紀(jì)委領(lǐng)導(dǎo)打電話做了解釋。
邱大龍有點(diǎn)垂頭喪氣,就埋怨何玲不該那么不謹(jǐn)慎:“有怨氣心里罵兩句也就罷了,怎么能寫到紙上呢?”何玲心里正不痛快,就回嗆道:“是我牽連了你,補(bǔ)救還來得及,干脆咱倆一拍兩散,你去找那如花似玉的雙胞胎,奔你的大好前程吧。”邱大龍想想這事兒也不能全怪何玲,忙哄道:“她倆加一塊也不如你,和你在一起,我什么也不在乎了。”
事已至此,干脆就隨他去吧,邱大龍和何玲也不再遮掩,該咋咋,倒也沒見老胡為難他們。反而是黑子,東一出西一出地追過幾個(gè)女孩兒,戀情都無疾而終。一天剛上班,樓道里突然鬧嚷嚷地不知發(fā)生了什么事,老魯進(jìn)來說勸業(yè)場看自行車的老太太找來了,說是一個(gè)黑老頭兒存了自行車不給錢,趁她不注意騎上車就跑,老太太一路追到工商局,上到五樓人不見了,就直接找到孟局長,讓他主持公道。孟局長領(lǐng)著老太太挨屋去辨認(rèn),鬧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好多人擠在樓道里看究竟。等到了黑子他們辦公室,老太太看到戴一頂毛線帽、低頭躲在角落里的黑子,用手一指說就是他。孟局長先是“撲哧”笑了,說:“這就是黑老頭兒?大姐你什么眼神嘛。你先回去,這件事我一定給你找回公道。”接著拉下臉,沖黑子厲聲喝道:“白建國,到我辦公室來。”
不知道孟局長會(huì)怎么收拾黑子,出了這么丟人現(xiàn)眼的事,領(lǐng)導(dǎo)能不生氣?邱大龍為黑子著實(shí)捏了一把汗,心里想著一會(huì)兒怎么安慰他。過了能有半個(gè)小時(shí),黑子過來了,倒沒見他沮喪,反而嬉皮笑臉一副得意樣兒,見屋里沒有別人,從懷里掏出一條絲巾說:“大龍,搞定了。”邱大龍一臉疑惑:“什么搞定了?”黑子小聲說:“就是打字員小郭,我約她晚上吃飯,人家答應(yīng)了。剛才我去買禮物了。”邱大龍說:“你小子瘋了吧?窩邊草你也吃啊?”黑子理直氣壯地說:“窩邊草怎么了?我不吃難道要等別人吃?”又說:“她說再帶個(gè)人行不,我說當(dāng)然行。大龍,你也參加一下,給我撐撐面兒,畢竟是第一次,人多更自然一點(diǎn)。”邱大龍覺得黑子可憐兮兮的,就答應(yīng)了。
他倆早早到了飯店,點(diǎn)好菜,不一會(huì)兒,小郭也來了,身后跟著一位身材高大的青年,穿一身軍裝,顯得很威武。小郭介紹說:“這是我男朋友,哦,現(xiàn)在應(yīng)該說是我愛人,郝哲,我們下午剛領(lǐng)了證,他過幾天就要去前線了。”郝哲很友好地跟他倆握了手,說:“謝謝你們對(duì)小郭的照顧,有你們這樣的好同事,我去前線也就放心了。”
黑子傻子似的愣在了那里,邱大龍用胳膊肘捅捅他,笑著說:“恭喜啊,黑子聽說了這事,一定要請(qǐng)你們倆吃頓飯,一是祝賀,二呢也是要表達(dá)對(duì)解放軍的崇敬之情。”黑子像是剛剛活過來,擠出一點(diǎn)笑容:“對(duì)對(duì),保家衛(wèi)國無上光榮,我們作為軍嫂的同事和領(lǐng)導(dǎo),應(yīng)該表示表示。”
幾個(gè)人坐下來,找各種話題打破尷尬,酒是好東西,幾杯下肚,氣氛就活絡(luò)起來。郝哲說:“本來不打算這么快結(jié)婚,這一去,不知道會(huì)有什么事情發(fā)生,不想連累小郭,但小郭執(zhí)意要在我走前把婚事辦了,好讓他安心。”邱大龍沒想到平時(shí)不哼不哈的小郭還有如此境界,內(nèi)心充滿敬佩和感動(dòng),連連敬酒,說了很多真誠祝福的話。黑子也活躍起來,說:“兄弟啊,小郭是我們局的第二美女,你一定要珍惜,若是將來你發(fā)達(dá)了,辜負(fù)了她,我可跟你沒完。”小郭笑盈盈地說:“那第一是誰啊?”黑子一臉認(rèn)真地說:“誰知道呢,現(xiàn)在還沒生出來呢。”邱大龍笑得嗆了嗓子,捂著嘴咳嗽了半天。
黑子經(jīng)此打擊,徹底蔫了,一天到晚沒精打采,不停地唉聲嘆氣。邱大龍正看報(bào)紙,見黑子踅摸進(jìn)來,指指報(bào)紙說:“你的個(gè)人問題內(nèi)部解決怕是沒戲了,不妨開拓思路,擴(kuò)大范圍,你看報(bào)紙上這么多征婚廣告,要不咱也發(fā)一條?說不定就能找到中意的。”黑子一下子來了勁,說:“大龍你文筆好,幫我寫一下唄。”邱大龍就拿出紙筆,寫道:“白某某,男,21歲,機(jī)關(guān)干部,愛好文學(xué),樸實(shí)大方,身高……”這條就別寫了,欲覓一……說說你的條件。黑子拿過報(bào)紙,仔細(xì)研究了一會(huì)兒,一拍桌子說:“不用寫了,這不就有現(xiàn)成的嗎?哈哈,各方面都符合,就是她了。”忙記下電話,哼著小調(diào)走了。
周一一上班,邱大龍就找到黑子,問怎么樣,搞定了嗎?黑子恨恨地說:“搞個(gè)鬼,整個(gè)兒一虛假廣告,什么身材苗條,媽呀,足有150斤,說以前苗條過,今后還可以苗條。還愛好文學(xué),連茅盾是誰都不知道,問我到底跟誰有矛盾了,嚇得我趕緊溜了。”抽了一顆煙,他十分鄭重地說:“我想明白了,要想出人頭地,先得提高自己,讓自己強(qiáng)大起來。我準(zhǔn)備寫詩,等成了大詩人,崇拜我的少女跟著一串,還不是任咱挑選?”邱大龍差點(diǎn)笑噴了:“就你還寫詩?怎么不做夢得諾貝爾獎(jiǎng)?”黑子認(rèn)真地說:“你別笑,我真有這個(gè)基礎(chǔ),當(dāng)年在老家上小學(xué)時(shí),我的詩上過校報(bào)。現(xiàn)在還記得幾句:‘公社的玉米大又大,一輛牛車裝不下……”見邱大龍一臉不屑,又嚴(yán)肅地說:“等著瞧吧,到時(shí)候找我簽名,可別怪我不給你面子啊。”
黑子真的一心一意埋頭寫起詩來,還經(jīng)常神秘兮兮地給邱大龍念一首。何玲聽說了這件事,也笑得前仰后合。也別說,過了一段,他居然在晚報(bào)發(fā)表了一首,雖然只有短短四行,在角落里,不仔細(xì)找都發(fā)現(xiàn)不了,但到底是印成了鉛字,還是讓黑子興奮了一陣子,詩寫得更勤奮了。還有一點(diǎn)他沒說,要想出人頭地,首先要當(dāng)個(gè)一官半職,因此他更加察言觀色,人氣也慢慢上升。
冬天到了,北方的天氣說冷就冷,辦公樓里暖氣不足,人們上班還要裹著厚厚的棉衣,連說出來的話好像也被壓縮了。這時(shí)候發(fā)生的一件事,給冬天的壓抑氣氛增添了很多熱度。
辦公室老魯?shù)侥挲g退休了,空出來的副主任位置成了很多人的關(guān)注點(diǎn),畢竟局里年輕人多,都想進(jìn)步。一天,張姐看屋里沒別人,悄聲對(duì)邱大龍說:“這次你也列入了副主任人選,你要抓住機(jī)會(huì),一步趕上,步步順利。”這個(gè)信息讓邱大龍有點(diǎn)興奮,說真的,以前他從未想過這個(gè)事,相反,他覺得自己太嫩了,當(dāng)領(lǐng)導(dǎo)怕是不合適。但機(jī)會(huì)來了,也不免有點(diǎn)蠢蠢欲動(dòng),誰不想進(jìn)步呢?他不知道自己應(yīng)該做些什么,想來想去,就找到張局長,說了自己的想法。張局長鼓勵(lì)說:“年輕人要求進(jìn)步是好事嘛,我一定支持。”
又過了好一陣子,這件事無聲無息了,張姐對(duì)邱大龍嘆了口氣,說:“大龍啊,一個(gè)人遇到點(diǎn)坎坷是正常的,你還年輕,有的是機(jī)會(huì),不要?dú)怵H啊。”邱大龍就知道自己提拔的事沒戲了。他知道以老胡對(duì)他的成見,自己這一步很難跨過去,想通了也就放下了,正好可以跟何玲專心致志地戀愛。
接著,很快出了一件讓人大跌眼鏡的事。老胡因?yàn)樽黠L(fēng)問題被人告到了紀(jì)委,說他和小郭上了床,還鉆了一個(gè)被窩。壞事傳千里,這事兒鬧得沸沸揚(yáng)揚(yáng),老婆要跟他離婚,女兒們也不理他了。事情傳到郝哲單位,部隊(duì)還專門派人來了解情況——涉及軍婚了!經(jīng)紀(jì)委調(diào)查,事情澄清了,原來是一次局里組織大會(huì),小郭負(fù)責(zé)照相,中間膠卷卡了,為了取出膠卷又不曝光,就在會(huì)務(wù)組的床上用被子蒙住,在被子里鼓搗相機(jī)。她是外行,半天也沒弄好,正好老胡進(jìn)來,就把頭也鉆到被子里幫著弄。這件事其實(shí)也沒別人看見,是小郭在某個(gè)場合當(dāng)笑話說了,被別有用心的人添油加醋舉報(bào)的。后來雖然有了結(jié)論,但男女這種傳聞,就像荒原上的野草,越割長得越多,永遠(yuǎn)無法除根。當(dāng)事人也就被曬到了一個(gè)十分尷尬的境地,很難抬起頭來。小郭申請(qǐng)去了一個(gè)直屬分局,離開了機(jī)關(guān)。五十不到的老胡堅(jiān)決地辭去了主任職務(wù),找了個(gè)閑差,開始埋頭研究歷史。
老胡是悄么聲走的,跟誰也沒打招呼。過后辦公室的人三三兩兩去看老胡,表示一點(diǎn)安慰,也表示一份情誼。邱大龍沒去,他覺得,搞這些虛頭巴腦的,實(shí)在沒什么意思。
后來真相慢慢傳出來,老胡是極力推薦邱大龍的,孟局長也很認(rèn)可,說這小伙子任勞任怨,做什么事都有板有眼讓人放心,是個(gè)好苗子。但張局長不同意,說小邱固然不錯(cuò),但太年輕了,自己主管科室的誰誰從資歷和經(jīng)驗(yàn)上更合適。據(jù)說在研究干部的會(huì)議上,從不發(fā)言的黨組成員老胡拍了桌子,說我們選拔干部最主要的是看誰在這個(gè)位置更合適,如果都論資排輩,還用得著我們?cè)谶@費(fèi)啥子口舌嗎?要是連這點(diǎn)公道都沒有,老子這個(gè)主任也不當(dāng)嘍。畢竟老胡資歷擺在那兒,從工商局成立就當(dāng)主任,已經(jīng)陪了三任局長,大家都給點(diǎn)面子,誰也不吭聲了。孟局長見局面僵持,就說這事以后再議吧。
邱大龍聽到這些傳聞,覺得很對(duì)不起老胡,在一天快下班的時(shí)候去了老胡的辦公室。桌子上堆滿了書籍、報(bào)刊,把老胡和外面的空間隔開了,邱大龍扭扭捏捏地表達(dá)了對(duì)老胡的感激,老胡一臉淡然,說:“我也不全是為你,當(dāng)年我也有過很多機(jī)會(huì),可惜沒遇到為我據(jù)理力爭的人。我人微言輕,也幫不上你什么了。”邱大龍只覺得鼻子酸酸的,眼淚快要落下來了。
經(jīng)此一事,一向自信滿滿的邱大龍對(duì)自己的能力產(chǎn)生了深深的懷疑,他覺得單位的水太深了,遠(yuǎn)不是自己能夠適應(yīng)的。他非常后悔當(dāng)初的選擇,甚至對(duì)舅舅也產(chǎn)生了某種怨恨,但又一想,這怎么能怪到舅舅呢?沒一點(diǎn)道理嘛。照本意,自己最大的愿望是當(dāng)個(gè)科學(xué)家,最起碼當(dāng)個(gè)工程師可能更適合,可連大學(xué)都考不上,那些想法不是扯淡嗎?
不久局里人員調(diào)整,配了新主任,也來了副主任。雙向選擇,邱大龍去了企業(yè)科,成了一名業(yè)務(wù)干部,也算滿足了心愿。
倒是黑子,一路順風(fēng)順?biāo)K恢眻?jiān)持寫詩,還進(jìn)入了市作協(xié),名片上印著“詩人白建國”,逢人就發(fā)。他也談起了戀愛,是消協(xié)老趙給介紹的,對(duì)象是縣工商局干部,據(jù)說還是市里某領(lǐng)導(dǎo)的侄女,找他不是因?yàn)槌绨菰娙耍饕羌庇谡{(diào)到市里。不久局里成立了行政科,黑子當(dāng)了副科長,科長空缺,他主持工作,管的是吃喝拉撒的雜事,但衣食住行誰也離不了,黑子熱心又會(huì)來事,上上下下都滿意,他也很滿足。
又過了一些年,黑子提了副局長。平心而論,他的提拔公平公正,這時(shí)候干部選拔工作已經(jīng)走上正軌,在推薦環(huán)節(jié),黑子得票最高,考察全票同意,誰也無話可說。他寫詩更勤了,隔長不短在晚報(bào)發(fā)表,雖然這時(shí)候晚報(bào)和詩歌都沒人看了,尤其是這種“老干體”,常成為嘲諷的靶子,但黑子不管這些,依然筆耕不輟,竟落了個(gè)“詩人局長”的美名。可惜的是,在孩子剛上大學(xué)那會(huì)兒,因?yàn)榻?jīng)濟(jì)問題,紀(jì)委對(duì)他進(jìn)行了調(diào)查,雖然結(jié)論遲遲沒下,但也夠讓人糟心的。當(dāng)然這是后話了。
邱大龍愛學(xué)習(xí)善動(dòng)腦,在注冊(cè)業(yè)務(wù)上成了公認(rèn)的權(quán)威,人們都尊稱一聲“邱科”,雖然他從未當(dāng)過科長。一旦哪兒有了空缺,都風(fēng)傳他要提拔,有些不常在一塊起吃飯的人莫名其妙要請(qǐng)他,他都笑笑拒絕了。有人為他鳴不平,他倒不以為意,“哪兒有哪兒的規(guī)則,規(guī)則是給能適應(yīng)規(guī)則的人制定的,我玩不了那個(gè),我服氣。”
一年就這么過去了。說快,1985還沒叫習(xí)慣,馬上又1986了,快得腦子都有點(diǎn)兒跟不上趟。說慢,天天都有啰里八唆的事,上面這些,只是用勺子從歲月的大海里舀出的幾朵浪花。
邱大龍和何玲戀愛已經(jīng)成熟,家里催著結(jié)婚,就給局里打了報(bào)告,沒想到卡在了孟局長那兒,原因是那時(shí)候提倡晚婚,男25歲女22歲,邱大龍不到線。他也不好意思為這事去找領(lǐng)導(dǎo),有點(diǎn)悶悶不樂。張姐看不過眼了,說:“符合《婚姻法》為什么不批?”就去找孟局長,不知道怎么說的,反正蘑菇了很長時(shí)間,高高興興拿著批了同意的報(bào)告回來了,說:“小邱準(zhǔn)備喜糖吧。”邱大龍說不光喜糖,還有喜酒。
星期天,邱大龍和何玲趁著休息把證領(lǐng)了。從辦事處出來,他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從此就是一家人了,覺得更親近了幾分,又有點(diǎn)陌生,就像出了趟長差,回來在火車站見了面。何玲竟有些羞澀,低下頭說:“傻呆呆地看什么?不認(rèn)識(shí)了?”邱大龍捏捏何玲的鼻子:“真有點(diǎn)不認(rèn)識(shí)了,哪兒來這么個(gè)大美女,怎么就成我老婆了呢?”“討厭你。”邱大龍把何玲要擂他的手抓在手里。
冬天的天很冷冽,也很清澈,太陽明明白白地掛在瓦藍(lán)的天上,十分耀眼。邱大龍?zhí)ь^看向太陽的時(shí)候,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上中學(xué)的時(shí)候,物理老師講到過的一個(gè)名詞:太陽黑子。他已經(jīng)忘了太陽黑子是怎么回事,反正不是好詞,他想,無所不能的太陽,怎么也會(huì)長上這些東西呢?又一想,這才叫杞人憂天呢。
邱大龍拉著何玲的手,滿心歡喜地往家走去。
作者簡介>>>>
兵哥,原名尹兵輝,河北省作家協(xié)會(huì)會(huì)員。曾在部隊(duì)多年從事新聞工作,90年代轉(zhuǎn)業(yè)到地方政府部門。2018年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部分作品在《長城》《河北文學(xué)》《青少年文學(xué)》《小小說月刊》《長城文藝》《歲月》發(fā)表。
[責(zé)任編輯 陳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