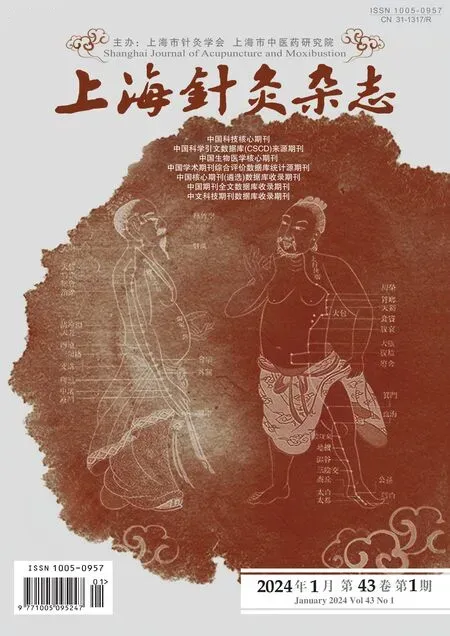小膠質細胞在缺血性腦卒中的作用及針刺對其調控研究進展
黃慧源,黃麟荇,易麗貞,陳瑞雪,綻晟,岳增輝
(湖南中醫藥大學,長沙 410208)
腦卒中是世界范圍內危害人類健康的重要疾病,是導致發病、殘疾和死亡的主要原因[1]。其中,缺血性腦卒中為最常見的卒中類型,占所有腦卒中的75%~80%[2]。到目前為止,重組組織型纖溶酶原激活劑(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是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準的治療急性缺血性腦卒中的唯一藥物,但其有著嚴格的溶栓時間窗限制和出血性轉化風險,臨床療效并不理想[3],因此,尋找治療缺血性腦卒中的新策略成為當前研究重點和目標。
小膠質細胞(microglia,MG)作為腦內常駐免疫細胞,占腦內膠質細胞總數的5%~20%[4],是抵御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病理損傷的首道防線[5],在監測和干預神經元水平活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6]。在腦缺血早期,MG 迅速活化并募集到損傷部位。一方面,MG 吞噬CNS 的細胞碎片,釋放抗炎因子,減輕神經毒性,發揮神經保護作用;另一方面,異常活化的MG 會吞噬應激的活性神經元,發生吞噬性凋亡,分泌促炎因子,發揮神經毒性作用,加重腦損傷[7-9]。針刺在缺血性腦卒中的治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0],其治療機制與調節MG 的極化和動態平衡密切相關[11-12]。本研究對小膠質細胞在缺血性腦卒中內的雙重功能及針刺對其調控作用進行梳理,以期為實現精準靶向小膠質細胞治療缺血性腦卒中提供新思路。
1 缺血性腦卒中后MG 激活
在生理條件下,MG 表現為“分枝形”的靜息狀態,依靠高度活躍的精細側枝(突起)持續監控腦內微環境,清理積聚的代謝產物,維持CNS 系統穩態[13-14]。而缺血性腦損傷發生后,MG 迅速活化,呈現出胞體較大、突起及分支縮短變厚的“阿米巴狀”,能夠吞噬死亡的細胞和神經元。這種病理條件下MG 形態和功能的改變被認為是MG 的激活狀態或反應狀態[15-16]。MG 的激活發生于星形膠質細胞活化之前[17],被認為是缺血性腦損傷后炎癥反應的第一步[18]。
2 MG 在缺血性腦卒中中的雙重作用
腦缺血損傷發生后,活化的MG 既可產生神經保護效應,又具有神經損害作用,這種相互矛盾的功能被描述為一把“雙刃劍”。在外界因素刺激下,MG 會釋放促炎因子和抗炎因子,極化形成M1、M2 兩種表型。這種MG 受到外源性物質的影響從而達到特定的表型,并存在一種或多種分子標記和分子分布的顯著變化結果稱為MG 的極化[19]。MG 在腦缺血后會發揮損傷神經和促進神經修復的雙重功能[20],其雙重功能作用與MG 的不同表型密切相關[21],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2.1 積極作用
2.1.1 減輕炎性反應
MG 在缺血性腦損傷炎癥反應的不同時期起不同作用,是腦內炎癥反應的重要調節器。在腦缺血損傷早期,MG 可在幾分鐘到幾小時內迅速激活并遷移到病灶區域[22],此時MG 呈現M2 表型,在缺血損傷后第3~5 天到達峰值[23];而在損傷后期,有害的M1型則占據主導地位。M2型MG 參與炎癥反應主要表達Ym-1、CD206等抗原[24],并可分泌白細胞介素-3(interleukin-1,IL-3)、白細胞介素-4(interleukin-4,IL-4)、白細胞介素-10(interleukin-10,IL-10)、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TGF-β)、胰島素樣生長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等抗炎因子,此時MG 吞噬活性增強以快速清除細胞碎片,保護組織免受炎癥損傷[25-26]。根據特異性激活物的不同,M2型又可分為M2a、M2b、M2c[27]。M2a 在炎癥期高水平表達Ym-1 等抗炎指標,發揮抑炎作用;而其他兩型則與免疫抑制和組織增殖重塑密切相關[28]。
2.1.2 促進神經修復
缺血性腦卒中發生后,梗死核心區的神經元在幾分鐘內發生退化、壞死;而缺血半暗帶毗鄰梗死核心區周圍的區域仍保持細胞代謝活性,因此挽救缺血半暗帶內的細胞功能對神經功能的恢復和預后至關重要[29],半暗帶區域的MG 反應是腦缺血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相關研究發現,在腦缺血早期,被激活的MG 主要極化為M2型,迅速向梗死灶和半暗帶遷移[30],發揮吞噬損傷神經元[16]、清理細胞碎片[2]、降低神經毒性的作用,從而挽救瀕死的神經元[31-32]。在腦卒中亞急性期和恢復期,活化的MG 被認為是愈合細胞,分泌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膠質細胞源性神經營養因子(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神經生長因子-1(nerve growth factor-1,NGF-1)等神經營養因子[33-34],使梗死周圍的肉芽纖維沿著增加的營養梯度向傷口邊緣生長[35]。研究[36]表明,MG 可消除多余的突觸連接并監測突觸的功能和狀態,在神經可塑性基礎上清除喪失功能的突觸,促進神經修復。如果造成MG功能缺失,則會導致突觸異常,從而加劇神經損傷[37]。
2.2 消極作用
2.2.1 誘導炎性反應
腦組織對缺血缺氧具有高度敏感性,在腦缺血發生后,伴隨腦血流量和供氧量的不足,可引發腦缺血級聯反應[38]。其中炎癥反應是級聯損傷過程中的關鍵病理環節,是治療缺血性腦卒中的靶點之一[39],而MG 是炎癥反應的關鍵調控者[40]。神經元損傷后,受損腦組織開始釋放損傷相關模式分子(damage associated molecular patterns,DAMPs),誘導外周免疫細胞向病灶及周邊募集,在急性期MG 被激活并極化為M2 表型,隨后逐漸并長期向M1型切換[41]。經典激活的M1型MG可分泌多種促炎因子,包括 IL-1β、腫瘤壞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干擾素-γ(interferon-γ,INF-γ)等,參與腦缺血后炎癥反應發生發展。IL-1β早期主要來源于活化的MG,可導致MG和星型膠質細胞活化并促進增殖生長,是參與炎癥反應造成腦組織損害的重要因子[42]。研究[43]表明,在小鼠大腦中動脈栓塞(middle cerebral artery occlusion,MCAO)模型的腦室中注射IL-1β,不僅會使腦梗死范圍擴大,還會加劇腦水腫程度,加重炎癥反應造成更嚴重的腦損傷。TNF-α主要由小膠質細胞分泌,是介導缺血缺氧損傷的重要因子,在腦組織炎癥反應中起關鍵作用[44]。有臨床試驗[45]證實,人體服用藥物抑制血清中TNF-α等促炎因子濃度后,腦梗死炎癥反應明顯減輕,證實了TNF-α在缺血性損傷中的關鍵促炎作用。INF-γ是T細胞中的代表促炎因子,在維持CNS穩態和功能方面起著重要作用[46]。動物實驗[47]表明,在MACO 大鼠模型中靜脈注射丹參總酚酸,可明顯降低炎癥因子INF-γ,抑制免疫炎癥反應,提示調控INF-γ為代表的T 細胞是治療腦卒中的靶點之一。
2.2.2 損傷血腦屏障
血腦屏障(blood-brain barrier,BBB)是一個處于血液和腦組織之間的動態界面,對物質的通過和交換具有嚴格選擇性,主要由血管內皮細胞、細胞間隙、緊密連接、基底膜、星形膠質細胞終足等組成[48]。腦卒中急性缺血期,MG 迅速激活并向梗死區域遷移,同時釋放活性氧簇(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過氧化氫、蛋白酶、一氧化氮等炎癥介質,這些物質的釋放在疾病病理進程中起到關鍵性影響[49]。缺血性損傷發生后,活化的MG 釋放大量IL-1β、TNF-α、IL-6等促炎細胞因子,通過介導內皮細胞壞死、下調緊密黏連蛋白1(zonula occludens-1,ZO-1)、上調細胞間黏 附 分 子 1(intercell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ICAM-1)和血管細胞黏附分子 1(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1,VCAM-1)、刺激釋放血管舒張因子加劇血小板聚集,造成緊密連接蛋白功能失調,共同誘導BBB 通透性增加[50-51]。緊密連接蛋白復合物的破壞被視為缺血性卒中下BBB 損傷的標志[52]。此外,MG 也能釋放基質金屬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主要包括MMP-3 和MMP-9,降解多種細胞外蛋白并參與細胞外基質重塑,使BBB通透性增加,導致缺血性腦損傷加重[53]。相關研究[54]發現,通過電針抑制MMP-9 可在溶栓治療中保護血腦屏障,減輕腦水腫癥狀、減少腦梗死面積。
2.2.3 誘導興奮性神經毒性
興奮性神經毒性是神經功能障礙的重要機制之一,主要是腦缺血時突觸間隙谷氨酸(glutamate,Glu)大量堆積引起的病理反應[55]。Glu 受體可分為離子型和代謝型,離子型Glu 受體根據藥理結合特性可分為α-氨基-3-羥基-5-甲基-4-異惡唑丙酸(α-amino-3-hydroxy-5-methyl-4-isoxazole-propionic acid,AMPA)受體、海人藻酸(Kainate,KA)受體、N-甲基-D-天冬氨酸(N-methyl-D-aspartate,NMDA)受體[56],目前已知MG 上可觸發AMPA 和NMDA 兩種離子型受體表達[57]。MG 活化引發NMDA 和AMPA 興奮性受體激活,降低抑制性神經遞質γ- 氨基丁酸(γ-aminobutyricacid,GABA)受體表達,致使細胞內鈣離子超載釋放過量Glu,這種興奮增加、抑制減少的比率失衡會誘導興奮性神經毒性,損害CNS[58-59]。同時,M1型MG 釋放的促炎因子如TNF-α可增加細胞突觸上AMPA受體表達,對Glu的傳播有直接影響,導致更多神經元死亡[60]。
3 針刺調控缺血性腦卒中后MG
3.1 改變MG 數量和形態結構
缺血性損傷發生后,活化的MG 胞體增大、突起變短,呈現“阿米巴狀”,形成具有吞噬功能的激活態[61],而針刺可調節MG 發生形態結構改變。鄧寒冰等[62]發現電針刺激腦卒中大鼠“陽陵泉及其配穴”“關元”“照海+申脈”等不同穴位均可使MCAO 大鼠MG 突起減少、形態逐漸向激活前恢復。馮楓[63]的研究結果也顯示,電針可以降低腦缺血后MG活化強度,控制MG的形態變化。腦卒中后,MG 迅速活化激增并向受損區域遷徙,針刺可以抑制MG 活化數量,發揮神經保護作用。有研究[64]報道,電針預處理“百會”“風府”可明顯降低MCAO大鼠腦內MG 數量,產生腦保護效應,可能是通過抑制MG 活化介導的MMP-9 實現的。
3.2 抑制炎癥級聯反應
炎癥反應是腦缺血后級聯反應的關鍵病理環節,針刺可以通過下調炎性因子釋放、上調抑炎因子表達,促進M1型MG 向M2型極化,維持M1/M2 平衡來抑制炎癥反應,從而減輕腦缺血損傷。針刺對MG 的炎癥調節已被諸多文獻證實。例如,電針“百會”“大椎”可以抑制MCAO 大鼠缺血半暗帶區MG 的變性和壞死,降低NF-κB、TNF-α、IL-1β表達,減輕神經炎癥[65]。電針腦缺血再灌注小鼠模型“承漿”“水溝”,除可減少IL-1β、TNF-α、一氧化氮合酶(inducible nitric oxide synthase,iNOS)M1型促炎因子的釋放外,還可促進MG向M2型極化,增加精氨酸酶、BDNF 抗炎因子的表達[66]。張慧宇等[67]對腦缺血再灌注大鼠“大椎”“百會”“水溝”及雙側“足三里”“風池”進行針刺,發現針刺干預后可以降低M1型MG 中TNF-α、IL-6 等炎癥細胞因子的釋放,增加M2型MG 中抗炎因子IL-10 和神經營養因子BDNF、GDNF 分泌,調節MG 極化,減輕炎癥反應。針刺抑制炎癥反應與多條通路機制有關,電針“內關”等穴位可以抑制腦缺血再灌注大鼠MG 上Toll 樣受體4(Toll-like receptor 4,TLR4)/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信號通路上炎癥因子[68]。另有研究[69]表明,電針能通過抑制p38MAPK-MyD88-NFκB信號通路來減少缺血再灌注后MG 介導的神經炎癥。金婷婷等[70]從外泌體著手,發現電針可促進腦缺血再灌注大鼠腦內M2型MG外泌體的表達,調節神經炎癥反應。此外,miRNA 參與腦缺血后MG 的激活,針刺可通過調控miRNA 平衡MG 極化作用,抑制炎癥水平[71]。
3.3 抗細胞凋亡
細胞凋亡是在腦缺血數小時后內發生的細胞“自殺”過程,主要見于缺血半暗帶區域。該部分細胞并非完全壞死,半暗帶中葡萄糖和氧氣的供應通常會導致緩慢的能量依賴性細胞死亡[72]。電針治療腦缺血再灌注小鼠后可上調其腦內ANXA1分子,引起MG表型轉換,促進細胞凋亡產物清除[73]。PI3K/Akt 信號轉導通路是一條重要的抗凋亡途徑,針刺可提升MG 活化通路關鍵蛋白如PI3K、Akt 的表達,減少神經細胞凋亡,促進神經元修復[74]。張弦[75]取“承漿”“水溝”兩穴對腦缺血再灌注小鼠予以電針治療,發現可增加小鼠大腦皮層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促進缺血性損傷修復,其機制也與激活PI3-Akt信號通路有關。鄧寒冰等[62]對腦卒中大鼠進行電針治療,發現卒中大鼠腦組織中MG 突起減少,凋亡神經元數量降低,其機制可能是通過抑制NLRP3/caspase-1 通路實現的。GUINDON J 等[76]研究發現,電針預處理可通過大麻素受體CB2R、CB1R 在腦缺血中調控MG 極化,減少細胞凋亡。
3.4 促進軸突生長與突觸重塑
腦卒中后,腦內缺乏能量供應,突觸功能受到極大損傷。MG 可以消除多余突觸連接,在促進突觸發育、維持突觸正常生理功能和突觸可塑性方面發揮作用[36]。研究[77]表明,電針“百會”“神庭”可促進局灶性腦缺血大鼠突觸重建,透射電鏡下可見突觸數量增加、神經突起中細胞骨架結構清晰,突觸間隙變寬。研究中突觸的形態學改變意味著電針可改變MG 極化失衡,促進受損神經恢復。電針腦卒中大鼠不同穴位可抑制MG 激活狀態,改善神經元活動和突觸功能[62]。勵志英[78]認為,MG 的適度激活在神經可塑性和清除壞死神經元道路上有正向作用,但其過度活化會增加腦缺血后的興奮性神經毒性,加重腦損傷程度。
3.5 激活星形膠質細胞
腦缺血后,MG 作為CNS 的第一道免疫防線首先被激活,星形膠質細胞受到MG 的影響也會發生活化[79]。MG 和星形膠質細胞在病理條件均下表達TGF-β、IL-1等相同的細胞因子,這些細胞因子互相產生刺激作用,形成相互對話的膠質細胞調節模式[80]。針刺可調節腦卒中后MG 和星形膠質細胞的表達狀態,在減輕炎癥反應、促進突觸重塑等方面發揮協同作用。在MCAO 大鼠“百會”“合谷”“太沖”上進行電針治療,可通過NF-κB信號通路增強OTULIN分子,抑制MG和星形膠質細胞的活化,減少TNF-α、IL-1β和IL-6 的分泌[81]。韓宏等[79]通過激光共聚焦顯微鏡觀察MCAO 大鼠腦梗死后的“半暗區”,鏡下可見激活的MG 和增生肥大的星形膠質細胞伸出的突起相互交錯,具有密切關聯。對MCAO 小鼠進行電針聯合多能干細胞衍生的小細胞外囊泡綜合治療可以調節星形膠質細胞的IL-33/ST2 激活,IL-33 通過與星形膠質細胞或小膠質細胞表面的ST2 受體結合,參與調節神經炎癥[82]。可見MG 與星形膠質細胞在腦損傷后發揮協同作用,共同維持CNS 穩態。
4 討論
綜上所述,MG 在缺血性腦卒中中發揮雙向調節的作用。缺血損傷發生后大腦缺乏氧和能量供應,MG 在病理刺激下被激活為經典激活型(M1型)和替代激活型(M2型)。M1型通過增加促炎細胞因子釋放、改變BBB 通透性、誘導興奮性神經毒性造成CNS 損傷,產生消極影響;而M2型則通過釋放抗炎因子和神經營養因子發揮抑制炎癥保護神經元的積極作用。針刺對MG干預效應明顯,一是通過抑制M1型生成來限制炎癥反應發展;二是促使M1型向M2型轉化發揮保護作用,促進神經修復。針刺從改變MG 數量和形態結構、下調炎癥介質分泌、抗細胞凋亡、促進突觸重塑、激活星形膠質細胞等方面多水平發揮綜合效應,誘導缺血損傷后的MG 由M1 向M2 極化,調節M1/M2 的動態平衡,修復受損神經發揮腦保護效應。
目前研究已取得一定進展,但缺血性損傷后MG 的活化和調控機制十分復雜,仍有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大量文獻中將MG 表型分為M1 和M2 兩型,此種分類方法過于簡單和理想化,已有研究發現在兩極中間可能還存在其他許多表型,提示未來對MG 的分類要更加細致。目前對缺血性腦卒中后MG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MCAO大鼠的動物實驗,但嚙齒動物模型并不能完全反映人類腦卒中后病理發展過程,基礎研究結果與臨床實際不甚貼合。目前針刺對腦卒中后MG 的調節作用主要是用電針治療,且各項研究的電針參數設置并不一致,穴位選擇上也不盡相同,實際治療效果是否受到參數設置和不同穴位治療作用的影響尚未可知,臨床手針能否達到同樣療效需要進一步驗證。電針預處理是在腦缺血前先重復刺激大鼠相關穴位再行MCAO 造模,以減輕腦卒中后神經損傷程度,但在臨床實際應用中如何實施預處理需要進一步思考。目前針刺對MG 極化調控作用的研究不多,且最新研究主要集中在限制炎癥反應方面,對其他方向作用研究還不夠深入。目前對MG的作用機制研究成為熱點話題,外泌體miRNA 與MG 關系密切也已經被證實,而針刺通過影響miRNA 來調控MG 改善腦卒中預后的相關文獻還不多,其機制研究仍需探討。MG 與星形膠質細胞雙向影響會發揮協同作用或拮抗作用。目前關于針刺調節MG 與星形膠質細胞相互作用的研究還較少,關注其相互合作的機制通路,促進MG 與星形膠質細胞發揮良性協同作用,或可為未來治療缺血性腦卒中提供更多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