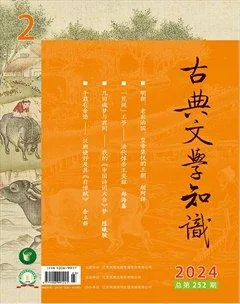千載有余情
余立新
作為一個(gè)文學(xué)大國(guó),中國(guó)歷史上又何止千千萬(wàn)萬(wàn)的文人騷客,他們像一顆顆光彩璀璨的星星,閃耀在我們的天空。而班婕妤是其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顆星星,我們的文學(xué)史也幾乎沒(méi)有班婕妤的一席之地,甚至連她的名字也失落了。可如果我們撥開(kāi)歷史的層層云霧,并用真心去接近她的話,就會(huì)感受到她所散發(fā)出的光和熱是那么的強(qiáng)烈。
一
班婕妤的生卒年不可考,《漢書(shū)·外戚傳》說(shuō)“孝成班婕妤,帝初即位,選入后宮”,又說(shuō)“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由此可以推測(cè)她大約生活于西漢元帝初年至哀帝初年。《隋書(shū)·經(jīng)籍志》記載“漢成帝班婕妤集一卷”,可見(jiàn)班婕妤的作品集至少在唐初還能見(jiàn)到。目前流傳下來(lái)的作品有賦兩篇《自悼賦》《搗素賦》,五言詩(shī)一篇《團(tuán)扇詩(shī)》。《自悼賦》在劉向的《列女傳續(xù)編》《漢書(shū)·外戚傳》等均有記載,《藝文類聚》中也有較完整的保存。《搗素賦》在《藝文類聚》《古文苑》中有記載。《團(tuán)扇詩(shī)》最早出現(xiàn)在《文選》中,題曰《怨歌行》,有人懷疑《搗素賦》與《團(tuán)扇詩(shī)》系后人偽作,但尚未成定論。另嚴(yán)可君《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guó)六朝文》還輯有《報(bào)諸侄書(shū)》一篇。
從文學(xué)史的角度來(lái)看,班婕妤當(dāng)是中國(guó)歷史上第一位女文學(xué)家。在班婕妤之前,有許多文學(xué)作品是婦女創(chuàng)作的,但嚴(yán)格地說(shuō),這些創(chuàng)作都不是文人創(chuàng)作。如《詩(shī)經(jīng)》中一些女性作者許穆夫人、共姜、壯姜等,陶秋英先生對(duì)她們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不必一定相信他是某人為了某某一件事情而做,因?yàn)椤缎⌒颉返茸髡叨济獠涣舜黠L(fēng)化的眼鏡,他所引證的事實(shí),或者也靠不住了,而所舉的人名也很難說(shuō)。”(《中國(guó)婦女與文學(xué)》)又如虞姬、漢高祖唐山夫人等,她們的創(chuàng)作均是偶做的單篇,且都并非嚴(yán)格意義上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帶有濃厚的民間歌謠色彩。
而班婕妤是中國(guó)文學(xué)史上第一位確實(shí)可考的女作家,第一位著力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有文學(xué)作品集的女作家,并且取得了相當(dāng)高的文學(xué)成就。她創(chuàng)作的《團(tuán)扇詩(shī)》在魏晉以后備受文人青睞,曹植、陸機(jī)、傅玄等眾多詩(shī)人競(jìng)相模仿,鐘嶸《詩(shī)品》稱“《團(tuán)扇》短章,詞旨清捷,怨深文綺,得匹婦之致”。茅坤稱班婕妤的《自悼賦》“賦之藻思,當(dāng)勝相如”(轉(zhuǎn)引自謝無(wú)量《中國(guó)婦女文學(xué)史》)。陶秋英先生也稱《自悼賦》“詞藻華雅,情景并臻,這種賦,不在漢代諸男名家下”(《中國(guó)婦女與文學(xué)》)。因此,我們稱班婕妤為中國(guó)第一位女文學(xué)家是不為過(guò)的。
二
班婕妤一生坎坷悲慘,據(jù)《漢書(shū)·外戚傳》,她初入宮時(shí),很受漢成帝寵幸,后受趙飛燕讒言,又連失愛(ài)子,終被成帝冷落,打發(fā)到長(zhǎng)信宮奉養(yǎng)太后,最終寂寞而死。其代表作《自悼賦》乃是班婕妤自訴自己不幸命運(yùn)的一篇自傳性質(zhì)的騷體賦。
全賦大體可分成三個(gè)段落。第一段敘述了作者初入宮時(shí)受到漢成帝寵幸的一段美好歲月: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于宮闕兮,充下陳于后庭。蒙圣皇之渥惠兮,當(dāng)日月之盛明。揚(yáng)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于增成。既過(guò)幸于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shí)。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監(jiān)兮,顧女史而問(wèn)詩(shī)。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yáng)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zāi)。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
開(kāi)頭兩句,作者說(shuō)明了自己高貴的身世和聰明賢淑的性格品性。三四句敘述了作者初入漢宮時(shí)的情況。《漢書(shū)·外戚傳》說(shuō):“帝初即位,選入后宮,始為少使。”故賦中曰“充下陳于后庭”。下四句寫(xiě)作者受寵于漢成帝時(shí)的一段時(shí)光。應(yīng)劭注“增成”曰:“后宮有八區(qū),增成第三也。”(《漢書(shū)·外戚傳》)可見(jiàn)班婕妤在后宮的地位不一般。從“既過(guò)幸于非位兮”往下十二句,描寫(xiě)了班婕妤在后宮中注重女德、嚴(yán)于律己,努力以娥皇、女英、太任、太姒等先賢為榜樣。《漢書(shū)·外戚傳》記載“婕妤誦《詩(shī)》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每進(jìn)見(jiàn)上疏,依則古禮”。顏師古注曰:“《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shū)也。”該段最后六句實(shí)際上記錄了作者一生中最令她傷心的一件事,即在她受寵于漢成帝的時(shí)候,所生的兩個(gè)兒子都莫名其妙地死去了。“陽(yáng)祿”“柘館”是后宮館名,皆在上林苑中,是班婕妤生孩子的地方。《漢書(shū)·外戚傳》記載班婕妤“再就館,有男,數(shù)月失之”。班婕妤即說(shuō)“其妾人之殃咎兮”,那么這很可能是一場(chǎng)宮廷陰謀的結(jié)果。它不僅讓班婕妤承受了失去愛(ài)子的巨大痛苦,也可能導(dǎo)致她地位下降,成為她命運(yùn)的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
第二段刻畫(huà)了班婕妤被漢成帝遺棄后供奉太后于長(zhǎng)信宮的漫長(zhǎng)孤獨(dú)的歲月: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于罪郵。奉共養(yǎng)于東宮兮,托長(zhǎng)信之末流。共灑掃于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愿歸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
從“永終死以為期”及“愿歸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來(lái)看,這篇賦當(dāng)寫(xiě)于成帝死后,很可能是在班婕妤死期前。這大概也是作者“以賦自悼”的原因吧。顏師古在《漢書(shū)·外戚傳》中注“山足”為“陵下”,當(dāng)是指成帝的陵下。《漢書(shū)· 外戚傳》記載“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第三段是全賦的結(jié)束,也是作者感情的最高潮。作者充分抒發(fā)了自己幽怨、感傷之情:
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yīng)門閉兮禁闥扃。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fēng)泠泠。感帷裳兮發(fā)紅羅,紛綷縩兮紈素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shuí)為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云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guò)兮若浮。已獨(dú)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lè),與福祿兮無(wú)期。《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從開(kāi)頭到“紛綷縩兮紈素聲”,極寫(xiě)長(zhǎng)信宮之孤寂衰頹的景色,以表達(dá)作者悲涼凄冷的心情。從“神眇眇兮密靚處”,到“酌羽觴兮銷憂”,寫(xiě)出了作者當(dāng)時(shí)對(duì)成帝的思念之情。“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顏師古注曰“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漢書(shū)·外戚傳》)。這一細(xì)節(jié)的刻畫(huà)真是動(dòng)人心魄,催人淚下。最后八句則是作者絕望的感嘆:“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guò)兮若浮”,這確是作者晚年絕望心境的寫(xiě)照。
三
從思想藝術(shù)上看,《自悼賦》深受楚辭的影響,這不僅表現(xiàn)在它在形式上是典型的騷體賦,更表現(xiàn)在它在思想感情上也是和楚辭相一致的。楚辭多言憂愁怨恨,司馬遷稱“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史記·屈平列傳》)。班婕妤一生苦難多艱,她的《自悼賦》也正是“自怨生也”。對(duì)愛(ài)子的接連無(wú)故夭折,她說(shuō)“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這實(shí)是對(duì)“天命”最憤怒的斥責(zé)。對(duì)漢成帝的絕情,她以“《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把成帝比喻成周幽王那樣的昏君。《綠衣》《白華》均是《詩(shī)經(jīng)》篇名,據(jù)《毛序》,《綠衣》乃“衛(wèi)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shī)”。《白華》乃周人刺幽王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為之作是詩(shī)也”。這可謂憤恨至極,極為大膽。
歷代都把班婕妤說(shuō)成一個(gè)溫柔敦厚、怨而不怒,完全符合封建禮教要求的賢婦義女。劉向在《古列女傳》中評(píng)班婕妤的《自悼賦》:“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不怨,《詩(shī)》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其班婕妤之謂也。”這些都不過(guò)是儒士企圖用封建的倫理道德來(lái)掩蓋班婕妤內(nèi)心深深的痛苦而已,完全是對(duì)班婕妤心靈的又一次謀殺。失子,遭讒,被逐,孤居……《自悼賦》可謂字字血淚,讀者只要稍微用心去體會(huì)班婕妤內(nèi)心的情感,就會(huì)感受到這是作者在對(duì)自己一生悲慘的命運(yùn)進(jìn)行最強(qiáng)烈的控訴。
當(dāng)然,作為一個(gè)弱女子,一個(gè)被打入冷宮的嬪妃,周圍環(huán)境對(duì)她來(lái)說(shuō)可謂危機(jī)四伏。因此,她的怨憤不可能直率地表現(xiàn)出來(lái)。她的被逐明明是趙飛燕專權(quán)讒言的結(jié)果,她卻自謂有“罪”,說(shuō)“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于罪郵”;明明是悲劇的一生,她卻說(shuō)“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guò)兮若浮。已獨(dú)享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其中蘊(yùn)含著多么大的沉重和無(wú)奈。所以說(shuō)《自悼賦》中的怨憤,實(shí)是一個(gè)封建社會(huì)中被侮辱被損害的弱女子的哽咽,即便是兩千年后的今天,我們讀這首賦,也會(huì)被其中作者的痛楚深深打動(dòng)。
就在班婕妤死后一百多年,班門又出現(xiàn)了另一位著名的女作家班昭。《后漢書(shū)·列女傳》記載班昭“博學(xué)高才”,說(shuō)她“有節(jié)行法度……帝數(shù)詔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hào)曰大家。每有貢獻(xiàn)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wù)隆薄Ec班婕妤恰恰相反,班昭生前聲名赫赫,深受統(tǒng)治者器重。她曾作《女戒》七篇,大肆宣揚(yáng)男尊女卑的封建倫理精神,受到歷代統(tǒng)治階級(jí)的歡迎。她文學(xué)上的代表作是《東征賦》,盡管作品中有淡淡的離鄉(xiāng)之愁,但通篇都是對(duì)“圣人”的緬懷和景仰,如“入匡郭而追遠(yuǎn)兮,念夫子之厄勤”,“惕覺(jué)寤而顧問(wèn)兮,想子路之威神”。又如“唯令德為不朽兮,身既沒(méi)而名存”,“唯經(jīng)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等。如果說(shuō)我們從《自悼賦》中能夠感受到班婕妤內(nèi)心深切的情感的話,那么從《東征賦》里已不能捕捉到多少女性情感的火花,后者的心靈,已完全被封建思想沙化了。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班昭是個(gè)更不幸的女性,她連自己的情感也被剝奪了。僅在此一點(diǎn)上,《自悼賦》與《東征賦》的高下便頓然分明了。
“其人雖已沒(méi),千載有余情。”夕陽(yáng)殘照下,不知那漢家陵闕,哪一片荒草下是艷骨所埋。但《自悼賦》卻始終如一支如泣如訴的悲曲,把班婕妤積郁在心中的長(zhǎng)恨悲情,流傳千載,綿綿不絕。